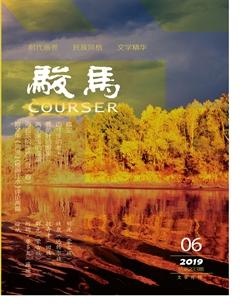第一次爬上森林瞭望塔
畢力革
那一年我爬森林瞭望塔。
好高好高的塔房矗立在崇山峻嶺之間,塔架因常年經受森林里潮濕的風,已銹蝕得不成樣子。要不是身后有幾個女孩沖我發笑,我無論如何也不會獨自一人硬著頭皮去冒這個風險了。
在密密的森林里整天整天地行走,每棵舉目不可企及的樟子松,塔林一樣佇立在我們道路上的每一處角落,早已進化的我們再也不能在每棵樹上任意攀援了,每座山峰都讓我們用同樣的困惑走進去,無論我們的腳步怎樣強壯有力,山總是不能夠離開我們。人生翻過好多個山脊之后,讓我想起童年時看見的一只甲蟲,它在一個球體上爬行著,一圈又一圈。我說它不累嗎?為什么重復著過去的腳印呢?老人們說,甲蟲們自以為在進行著很了不起的旅程,實際上它在重復過去的道路。為什么我進入而立之年后,眼前總是出現那只默默無聞的甲蟲呢?它晝夜不停地在我的眼前爬呀爬。
憋了好久,不知為什么總想出去看看。看看外面的大千世界到底會是什么樣子的。到外面久了,覺得還是乏味,于是就回來。回來后還想走出去看看,于是就又走得遠了一點,還是差不多的感覺,正如這座山與那座山,世面本沒有什么兩樣。最后,又只得掃興而歸,回到生我養我的山溝溝,回到出發的起點上。過了不久,雄心不死,還是想出外看看,到更遠的山外去,最好是國外。到國外看看,看看地球的平面到底應該是什么樣子的,我們的平足為什么在地球任意一個地方都可駐腳,都可碌碌無為地度去一生,為什么不能掉下來,在一個不平衡的球體上竟然出人意料地保持平衡的心理狀態。到外面看看去,南極、北極、赤道、海洋等等。
甲蟲在干燥光滑的球上爬上爬下。它那有滋有味的旅程一定很充實,而我卻不可理解了。那枯燥無味的上面究竟會有什么?如果甲蟲站得更高一些,甚至每一次的重復正如但丁迷失在這片林子里,只不過一個小山頭就耗盡幾輩人的腳步。腳步邁過去的地方,照樣會有人重新邁過,每棵樹都會攔劫我們的視野,不可能讓我們那一雙黑色的目光平射過去,矮小的人類又沒有超常的能力,正像小螞蟻落進草窠里,雞雛一樣驚慌失措地嘰叫著。植被的高大和遼遠的地盤,這是我們至今為之困擾而無法超越的難題。讓我們重新像樹一樣再高大起來,或者再像猴子一樣走在高大的樹上,我們早已規定好了的有尺寸的身體又沒有準備。生來貼在地皮上,長在地皮上,匍匐在地皮上,死后再仰身在地皮上望著星空,直到慢慢地被星空給火化,變成另外一種星宿,人本身在腦海里重新擺放的星宿,這是我們的本能。飛天只能作為傳說用嘴接力下去,傳說永遠在嘴里出出進進,這是飛機也解釋不了的難題。但是,在飛機上卻使我們體會到我們這個富有的地面很貧窮,未經開墾的和未經成熟的地盤,大于開墾的和成熟了的地盤,沙漠大于森林,鄉村大于城市,我們懷中沉睡的那些宏偉的玩具群過于渺小,天平的砝碼早已失去準確的衡量,而我們高高在上的思維總是不能夠平穩下來。你說我們除了把我們的城市原封不變地縮小在地圖上,除此之外,我們又能怎樣。
從飛機上走下來,我們耗盡了油水。我們的母親只是多添了幾根白發,變得更加慈祥了,我們變得更加老成了,土地還未成熟,而我們早已在這片未曾成熟的土地上成熟起來,并且像果子一樣從飛機上掉下來,落進土地里。在那里,我們除了仰望星辰之外,還要不成熟地將這種成熟一口接一口地吃掉。像飛天一樣,我們的往事在人們的嘴里出出進進。不是嗎?那種童年想飛的愿望,在一顆漸漸成熟的心中變得更加真實可笑了。笑過之后,又變得模糊不清了,直到最后消逝。這時,將會喪失整個童年。
那一年我爬森林瞭望塔。
塔架已銹蝕得弱不經風,像枯草一樣聞風而動,幾個女孩在身后笑我膽小如鼠、不敢高攀。望著高塔之上飄過的云朵,真害怕我的小命會這樣輕輕地飄走,但我還是不由自主地攀登了。
那一天整個山谷沉默不語,都為我的壯舉屏住呼吸。開始時,我的感覺還算平靜,越爬越感到塔身不斷地加寬擺動,擺動得就好像一個經不住過重分量的竹桿,隨時都會發生咔嚓的斷響。上面的風呼呼直叫,就在我剛剛接近最頂端的塔樓時,真的就咔嚓一聲,塔身加勁地搖晃起來,山如石頭大小,人們在地面上的影子就小得如同石頭縫里的泥點點,而我的身體就在與塔架同時傾斜的當兒,飛快地閉上了僅僅適合地面口味的眼睛。
在平地上,眼睛為我們明辯是非,在更高的一個階層,眼睛就會給我們帶來許許多多的膽怯和不安,甚至讓我們不能達到最佳的狀態,它有可能損害我們的生命。我緊緊地閉上這雙怯懦的眼睛,還是靠與生俱來的正常人的思維方式,就像在地面上一樣四平八穩地思考問題。這時,天空也就不再存在了。就這樣,我爬著想著,直到爬上塔樓。
塔樓在風中悠得更加厲害了,我卻緊緊地閉上眼睛,直到從上邊退下來。當時,我想起耶穌率眾弟子飄洋過海,風起云涌,世界就要到了末日,他雙臂抱合,讓眾弟子念了一種經,頓時,這個世界就風平浪靜了,一切艱險隨之化作烏有。怎么會風平浪靜呢?那是因為他們回憶起地面上的平靜,用地面上的場景,代替了這波浪的不平。忘掉眼前,用習慣的思維從塔樓上爬下來,就像從一個平面走向另外一個平面,唯獨不同的是地面上的行走是水平的,而向天空的行走卻是垂直的,兩種形式只不過是一橫一豎罷了。那么是否就可以下這樣的定義:眼睛只不過是地表的監獄,讓我們的肢體永遠不要飄出土地的鐵門。
我默不作聲地從塔樓上走下來了,那些曾笑話過我的人贊不絕口,說我很勇敢,竟能爬上危險的高度。我沒有作聲,更沒有向他們解釋我全部的勇氣和果斷。然而,多年之后,當他們再講起當時當地的往事時,竟認為我當時是那樣的幼稚。我聽后,忽然察覺到我每天行走的那種平淡無奇的小路,竟然一下子給豎了起來。
平路變成難以攀登的高空了,并且,在路的盡頭正有一個搖搖晃晃的塔樓等待我。我的成熟會像果子一樣,掉進永遠都不會成熟的土地里,也許會從土地下伸出不成熟的嫩芽。
責任編輯 冬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