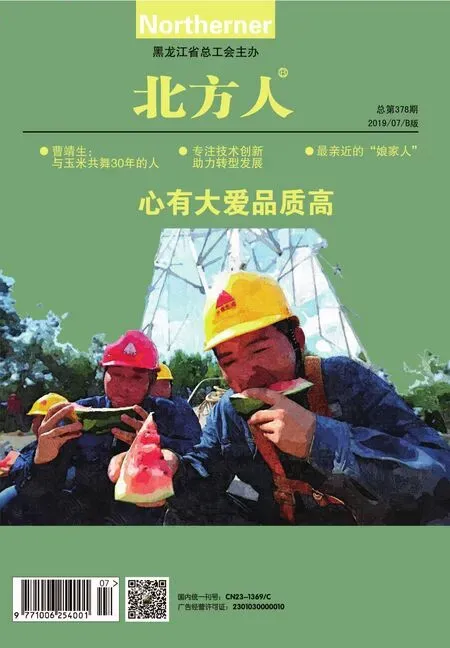家鄉的小河
文/于躍勇

從我記事起,家鄉就有一條小河。河水安靜地流淌,岸邊開著叫不出名字的花兒。盛夏時節,岸邊水草青青,空氣中彌漫著野花的芬芳。河邊的草甸子,是我們玩耍的好去處。捉蜻蜓、逮青蛙,間或用蒿子稈兒扎一頂行軍帽。匍匐在草叢中隱蔽,等待著慌不擇路的“座山雕”,每每被踱步吃草的牛兒驚擾,跳進水里乘涼。那時天空湛藍,河里魚兒曼舞。在兒時的記憶中,除了燦爛的陽光,就是天邊燃燒的晚霞,伴著我們不知疲倦的笑臉。
那時經常放映露天電影,放電影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快樂的時光。夏季的黃昏,我們經常站在小橋上眺望,那匹白色的老種馬遠遠地拉著放映機跑來,廣播喇叭里就響起了《在希望的田野上》。吃過晚飯的人就陸續來到了小河邊,大人們納涼閑聊,談論著誰家菜園長得好,誰家烀的茄子香,誰家的孩子今年高中畢業。幾位知青竊竊私語,女孩兒穿著半袖的確良襯衣,男孩兒快樂吹著口琴;角落的老爺爺打著拳,高興時他會取出那把繳獲的日本戰刀。講訴當年如何解放的四平,如何戴著狗皮帽子一直打到海南島。我們聽得津津有味,全然不顧電影已經開場,大孩子歡呼打口哨。賣冰棍、汽水的吆喝聲響了起來,那枚五分的硬幣,我捏了好幾天,這次終于沒能挺過誘惑。后來,那匹老種馬病死了,我們很傷心,一起去河邊采了幾束白花,鄭重地灑在河水里祭奠。
我經常在一顆老榆樹下垂釣。從大掃帚里抽根最長的竹梢,用火燎彎成魚竿。魚線纏上幾塊鉛皮墜,插上一節玉米秸,當做魚漂。魚鉤上滿蚯蚓,就可以守株待兔了。挖蚯蚓很有講究,要去摳柴垛根兒,或者菜園的杖子邊兒,那里蚯蚓多,尤其是紅紅的大粗蚯蚓,它是魚兒的最愛。我們人小力氣弱,常撿別人翻過的地兒,一不小心,就被主人抓個正著,每次都少不了落荒而逃。釣魚要沉住氣,鯽瓜兒逗食,鲇魚吞鉤,最狡猾的屬山泥鰍,每每咬食兇猛,卻總在魚漂上下冒泡。河邊坐膩了,把魚用柳條兒穿成串兒,拎著沉甸甸的魚串子,感受著路人驚奇的目光。下游傳來孩童的嬉戲,伴著打水仗的喧嘩,夾雜著裊裊的炊煙,一起躍入我的眼簾。晚霞悄悄映紅了河面,遲歸的奶牛悠閑地尋找主人。河水仍舊緩慢地流淌,帶走柔若無骨的榆錢兒,也帶走我波瀾不驚的記憶。
冬季的小河,白茫茫一片。放寒假的我們,在河面上清理出一片冰場,玩爬犁,滑單腿犁,在冰面上比賽打出溜滑。渴了,啃幾口凍梨,摘掉熱氣騰騰的棉帽子,追逐著打雪仗,看誰團的雪團兒大;或者堆幾座雪人,給那座一只耳朵的起個名字,一定是經常欺負我們的大孩子。不知跌了多少跤,也不記得摔了多少個仰八叉。童年的快樂時光,在小河邊靜靜流淌。直到現在,我仿佛還能聽見遠去的笑聲,卻再也追不回曾經的光陰。
80年代末,我跨過小河去讀初中。那時通往總場的是砂石路面,路邊間隔排列著整齊的沙堆。養路工人在路上忙碌,晴天卸砂石,開車刮平路面;雨天排水,墊平坑洼。那時松花江南岸還沒高速路,鄰近的幾個縣不通火車,小河邊的哈蘿路運輸繁忙。公路上車流不息,常年駛過載著原木的兩節拖車。過往司機累了,在河邊小憩,洗把臉,抽根煙,與行人搭訕幾句。談論起沿途的莊稼,再是這條小河的源頭。夸獎著當地大米,如何香甜,如何負有名氣。伴著歡快的自行車鈴聲,我們風一樣掠過安靜的小河,河水在橋下默默流淌,滋潤著這片土地,也養育著少年的我。
90年代初,我去外地讀高中了。跨過小河,就是路邊的臨時站點。那時汽車經常晚點,人多的時候,根本擠不上去。有次錯過了車,我在河邊徘徊。母親焦急地注視著遠方,擔心我趕不上火車。嚴冬時節,天空陰沉,寒風凜冽,母親的目光掠過彎曲的小河,一直眺望著公路的盡頭。雪花落在頭上,一動不動;寒風扎過面龐,她仍一動不動。弱小的身軀佇立在冰天雪地中,仿佛一尊凝視的雕像。身后的楊樹揮舞著光禿的枝杈,發出低沉的怒吼,幾只烏鴉在樹梢盤旋,再遠處是冰封的小河。河水在冰層下溫暖流動,流向遙遠的幸福,更奔向希望的春天。這一幕,許多年后,仍刻在我的記憶中,不曾忘懷。
再往后,我讀了大學,參加了工作,每天出入小橋上班。結婚時,迎親的車隊從橋面上駛過;閑暇時,一起長大的伙伴聚在河邊。小橋早變了模樣,河水還是那樣靜靜流淌,泛著波紋,打著旋兒,一路澆灌著萬畝良田,感受著香蘭的巨大變化。遠處高樓林立,車水馬龍;近處鶯歌燕舞,稻海飄香。小橋不說話,河水始終沉默,無聲地滋潤著這片土地,看著春華秋實,盼著人壽年豐,也牽掛著這塊土地上長大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