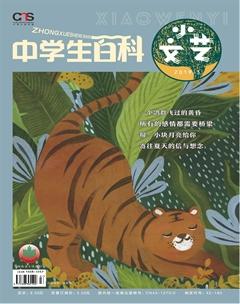我想抱住那團光
暖紀年
1
她站在那里,像高枝上的一朵百合花。
如果不是因為神經質的動作,高老師看起來就像一朵百合花。會議室頂頭的光落在她修長的脖頸上,冷光藍調襯得人很白,似乎還能看見細小的血管。她得有四十多歲了吧,五十應該沒有,不過誰說得準,天知道這種永遠優雅的精英女性能在保養上下多大功夫。
剪裁良好的白色套裝,薄殼銀灰的手表,不用刻意但就是很舒服挺拔的站姿……有某種聲音清晰地裂開,會議室里像突然綻開了一朵百合花。從縫隙開始,花瓣一絲絲分開,顏色是雪夜的白糅進了一些櫻花粉。還星星點點落著小雀斑,空氣中一下子灑滿了淡淡的清香味兒。能用百合比喻的人還真找不出幾個,當然,如果她沒有神經質的習慣,就更好了。
此刻,高老師一邊慢條斯理地訓斥,一邊下意識地剝橘子。她是策劃,在電視臺地位不低,到處都放著她的青橘子,一摞一摞地堆著。她說話的時候,總會撈過一個橘子,指甲一摁戳一個洞,一片片撕掉橘子皮,這還不夠,還要把橘子表面白白的經絡都捋干凈。
桌子上總有碗,要么就是擺著白紙,表面千千凈凈的橘子,被她連成一條直線擺在上面。剝得太干凈了,果肉瑟瑟發抖地擠在一起。她不吃,也沒人敢吃,一整排脫了衣服的橘子就光溜溜地擺在那里,有點兒像是在接受審判。
“這次活動策劃是誰想的?”
“自己好好反省錯在哪里。”
這次辦一個關愛留守兒童的公益活動。我只是帶上相機,和所有實習生一起去學校采訪,跟在高中記者站時做采訪的流程差不多。那么,到底哪里做錯了呢?
仔細想想,是我的錯。我真傻。高考完后我應該盡早考慮復不復讀,或者安安穩穩做一條咸魚,睡最長的覺,做最懶的魚。如果不是我的錯,我就不會閑得發慌,我就不會覺得無聊,就不會大老遠地跑來電視臺實習。
重新做了策劃后,下班已經很晚了,我怕黑,只能在巷子口憋一口氣,背著包一路狂奔上樓。結果一打開門,差點控制不住尖叫起來——廁所應該是堵了,滿地都是水,地上的東西基本浸濕了。謝天謝地,排插今天沒放地上。
瘋狂拖地,丟紙巾,用抹布擦干,聯系房東。找清潔工……每一步做起來我都有強烈的抵觸。社交障礙和回避型人格讓我生活在恐懼當中,極度自卑,但又有什么東西摁著我讓我往前走——我不敢接受自己是這樣的人。我堅信這也是我高考大滑坡的原因,我害怕面對,并且知道不解決絕對不能往前走,所以復讀大軍都熱火朝天地開學了,我卻逃到當地的小電視臺實習,租房子一個人生活。
想找一個沒人發現的地方,把自己拎起來,拋進去。
讓我躲一躲吧。
我坐在門檻上,瞧著月亮,有一小點兒風把我的衣服吹脹,堵得發慌的感覺終于消散了不少。我重新撈過手機打電話,想起桌子上尷尬袒露的青橘子。
一個,兩個,三個……光禿禿地排排坐,怪滑稽的,和我一樣。
2
這次是個公益活動,讓留守兒童和社會人士對接,一起過生日、做游戲,最后會做一期朗讀活動,共同讀一首詩。
內心深處。我對這個活動嗤之以鼻。換位思考一下,我愿意在這么小的時候面對電視、面對采訪嗎?曝光本身就是一種壓力。不過也許是我想多了,哪有這么多問題少年、敏感少女?
“集中注意力,下面我要出題了。”編劇兼記者陳老師也帶學生,主要教采訪和后期寫臺本。
“有一所學校,學生出了點事,我們幾個人打電話給校方想去采訪,校方態度很好,還說要安排人去酒店接我們。我當時就覺得有點兒不對,果然,校方拍下厚厚幾萬塊在桌子上,告訴我們,學校臨時翻臉不接受采訪了,我們毫無責任還可以得到很多錢。如果當時在現場的是你們,怎么辦?”
有個實習生傻樂著一拍大腿:“老師,我好像有一點點心動。”
陳老師一翻白眼,說道:“當年我帶去采訪的那個實習生也是,我感覺我看到了他眼里進發的光。”
“正確做法是,告訴對方,”陳老師清清嗓子,“把你們的錄音筆關掉。”
對方真的訕訕地取出了錄音筆。陳老師說,遇到敏感情況,提防要緊。對方可能想不報道,也可能想陰你一把,你開口說什么,都可以被剪輯,回去就被匿名舉報丟工作。
做個采訪就像演《甄嬛傳》一樣,辦公室里還是忍不住一片嘩然。
“真想接錢的,你就配不上這個行業了。”他說得漫不經心,辦公室里卻一片寂靜。
接下來的策劃討論會,高老師一邊順手剝橘子,擺成一排,一邊說了極相似的話:“這是一個公益活動,節目收視重要,但活動本身更重要。我們不是賣慘博眼球,不是標榜多么有愛心,不是施舍,不是揭他人傷疤豐富自身經歷,你要配得上‘新聞從業者這幾個字。”
聽完這段話,我猛然意識到自己錯在了哪里。
可是真的能做到嗎?
只要打開網絡,會有無數信息洶涌而來。我看過顛倒黑白,我看過低俗暖昧,我看過刻意引導……每個人都被龐大信息流裹挾著。甚至每個人都被欺騙過。
人要生活,更要生存;我們想要真相,又害怕真相。
3
考慮到也許還要回去復讀,我也偷偷問過編劇,為什么我的議論文這么差,他說我沒有真正用心。用他跳離學生多年的身份看,高考作文無非就是圍繞那幾個大方向出題,也越來越偏向家國情懷,只要我往其中糅合一些正義感和社會責任感,是很容易得高分的。問題是,我的正義感是真心的嗎?
真心不真心,旁觀者是很容易看出來的。比如說,我對這次的公益活動就不夠真心,只是把自己放在“實習玩一趟”的位置上,依然把自己當成一個學生。
如果我夠真心,我就不該和一群實習生去學校采訪,這會反復提醒那些敏感纖細的孩子一我和別人不一樣。前面的了解階段我不該帶相機,那樣無法真實交流,會讓他們看到鏡頭不自覺地開始“演”,我應該先和他們的班主任和父母聯系……
越想越心驚膽戰,我到底做錯了多少?
參加活動的孩子里有個叫姜姜的,喜歡穿一條開滿向日葵的裙子,是所有小孩里最乖巧最漂亮的。同時也是最讓人心疼的。通過班主任我知道她的父親在打工的時候遇上事故不幸去世了,母親拋下她改嫁。我想對她好一點,但不應該這么明顯,這種區別對待反而是揭他人傷疤。
開會過后領導決定重新修改活動環節,希望最后一個朗讀環節能夠順利進行。高老師怕活動出錯,也參與進來了,一個個聯系家長,有些還去了家里了解情況。辦公室里,大家心急火燎的。走路都是小跑。
高老師聯系回來,有點感慨地和我們聊天。
“這次活動有個小孩的奶奶,特別堅強。她兒子去世了,但死死瞞著不讓小孩知道,說他們都去外面打工了。她不定時把衣服拿出來曬,硬生生人前人后沒掉過一滴眼淚。”
“那過年呢?過年怎么辦?”
“過年她奶奶就假裝打電話,埋怨他們兩個為什么不回家,故意讓小孩聽見,知道工作很忙。其實兒子去世,兒媳婦改嫁了,瞞了好久。”
“等等……”我霍然抬起頭,“你說的是姜姜?”
高老師想了會兒名字,然后點點頭。
我覺得喉嚨有點干澀,不知道撞見了什么魔幻現實主義劇情,好半天才猶豫著說:“確定是姜姜?我去學校采訪的時候。姜姜早就知道父親不在了啊。”
“但她奶奶今天說……”
我倆大眼瞪小眼,然后同時愣住。
所以,每次奶奶曬衣服,把被子拍松軟的時候,她就睜著漆黑的大眼睛看著;每次打電話的時候,她就在旁邊聽著,開開,心心,乖乖巧巧;飯桌上討論著同一個人,他什么時候回來……她們守著這個美好的夢境,為了給對方一個安心。
對了,姜姜今年才九歲。
下班時間剛到,高老師就剛才的對話消化了好一會兒,然后抬起頭說:“后天的朗讀活動內容,重新修改一下吧。”
我說:“好。”
4
現場直播的地點很特別,在新華書店的頂樓。玻璃房子的直播間,往后可以看到整個城市的景觀,高樓、摩天輪,夜景尤其好看。平常圍坐讀書的人慢慢聚攏,好奇地看著攝像機。
朗讀前,主持人一般都會熱身聊聊天,消除緊張和尷尬,比如和直播連線,和“暑期父母”也就是對接的陌生人交換卡片,展示自己的愛好特長。因為節目時長,每人只能有一個小互動。
活動策劃的同事熬夜改了又改,我們砍掉別的環節,給姜姜安排了所有的互動,一共三個。
她展示了自己畫的向日葵,對接的暑期父親是個警察,真情實感地寫了一封長信給她。熱線連通了姜姜久未見面的姑姑,沒說幾句她突然掉下眼淚。高老師頓了一下。現場有些緊張,擔心連線是一個錯誤決定。還好,不一會兒她破涕為笑。
今天對于她來說,是溫柔美好的一天。
如果把“奶奶和小女孩相互隱瞞”的故事報道出去,這會是一個很吸引眼球的故事,可是沒有人這樣做。工作人員都理解姜姜的眼淚,哪怕現場的觀眾可能覺得莫名其妙,覺得這個小女孩太緊張。這個故事不會報道出來干擾她的生活,沒人拿她的眼淚賺取觀眾的眼淚。
電視臺背后藏著不少秘密,有很多這樣的姜姜,有很多背后的故事,不會被報道,也不會被揭開。這個公益活動的目的僅僅是,嘗試著在兩個本該陌生的人之間,建立長久的聯系。
朗讀的時候會全場熄燈,一片黑暗中,啪嗒一聲,僅有的一束追光打在舞臺上。
那一刻,我屏住了呼吸。全市燈火次第亮起,車流像海潮,跟著呼吸慢慢涌動著。就像詩歌里說的那樣,浪打空城寂寞回。
她……會記得我們嗎?這個小小的、精靈一樣的孩子,畫燦爛向日葵的孩子,會不會記得一群陌生人熬夜趕策劃,希望給她一點微亮的火光?會不會記得十二樓高層的玻璃間,空空蕩蕩卻不是孤身一人?會不會記得窗外,長風浩蕩。萬家燈火?
真心換真心。
這個美好瞬間,解開了我所有的恐懼和不安。
5
我剝開橘子,一個,兩個,三個……排成一排,放在白紙上,底下墊著各科高考真題。
面前突然多出了很多只手,我前后左右的同桌忙不迭把橘子拿走了。雖然復讀時周圍全變成了陌生面孔,但少年人總是一兩個月就能混得很熟。
“你為什么總是剝橘子啊?還剝得這么干凈。一定要擺成直線。”
“這是我獨家的解壓方式。”我笑瞇瞇地從抽屜里再拎出一個橘子。橘子剝開的時候,細小的霧水會灑在空中,氣味先是刺鼻的,像把檸檬所有的酸擠在一起落在鼻尖,然后舒展開酸酸甜甜的味道,再用力一吸,是雨過天睛之后的清涼。
我打開窗往外看,一直看到很遠很遠的地方。
不久以前,我一個人生活。不久以前:我看到娛樂至上,也看到顛倒黑白;我看到有人哭了,也看到有人笑了;我看到中年人背負家庭,年輕人踽踽獨行……有一群人摸爬滾打,但心中總是有一點捻不滅的光。
我想念大家,我想再往前一步,直到抱住那團光。
編輯/譚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