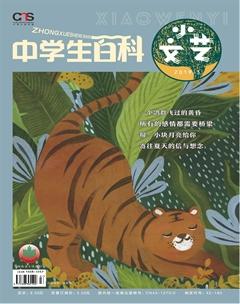他一個人的村莊
吳舒涵
劉亮程
劉亮程,作家,1962年出生于新疆古爾班通古特沙漠邊緣的一個小村莊。被譽為“20世紀中國最后一位散文家”和“鄉村哲學家”。曾獲“第六屆魯迅文學獎”散文雜文獎、“第十六屆百花文學獎”散文獎等獎項。著有詩集《曬曬黃沙梁的太陽》,散文集《虛土》《一個人的村莊》《在新疆》《一片葉子下生活》等。
第一次這么想寫一個人,他是劉亮程。
初次見到這個名字,是在高中語文練習卷上。我仍記得,那篇閱讀文章名為《今生今世的證據》。哎,這標題可文藝了吧。可里頭的內容卻沒有一點小資情調,沒有精心修飾過的浪漫詞語,也沒有引用纏綿悱側的詩句,而是樸素到了極致。劉亮程的文字太干凈了,沒有任何贅余,卻那么輕易地引起我心里翻涌的共鳴。這種共鳴是輕柔的,它一點也不激烈,可從中能夠體會到的韻味卻豐富得可怕。
“即使墻皮全脫落光,也在不經意的、風雨沖刷不到的那個墻角上,留下巴掌大的一小塊吧,留下泥皮上的煙垢和灰,留下劃痕、朽在墻中的木鑊和鐵釘,這些都是我今生今世的證據啊。”劉亮程在這篇文章里寫了這樣一段話。我把這段文字讀了一遍,忍不住又讀了一遍。作者的語氣甚至是平淡的,他在懇求,他在低訴,他同樣是在自語,企盼今生今世能在此世間留下些微他存在過的痕跡,甚至不需要哪個人記得,只要一株草,一堵土墻,一塊破瓦片的證據,就足矣。
忽然地。我想到了自己家里的粉刷墻。一年一年過去,墻角有大片擦不去的水漬,愈發暗淡灰黃,墻皮也斑駁地剝落下來,一時來不及清理,然后在時間的碾軋下,變成細碎的粉末。曾經那面墻還是潔白的,上面貼滿了三好學生的獎狀,從黃燦燦的一片慢慢陳舊發黃,再后來,因羞于展示炫耀,便一張張全揭下了,只是風干的乳膠依舊斑斑點點地殘留在墻上。
還有啊,因為小時候個子躥得快,母親便用家里的木頭梁柱當作我的身高記錄板,每隔半年,她都叫我過去在木柱前站一站,拿手比一比,再拿剪刀尖銳的一頭在上面反復刻畫出一道橫線來。那些橫線隨年歲增長愈來愈多,從梁柱的下頭蔓延到上頭,從分隔得稀疏到漸漸密集。再后來,它卻突然沒了用處。因為我已經長到頭了,長得比母親還要高了。
我很少會想起這些經年累積下來的細節,對待過去的事物,年輕的我們很少給予憐惜,未知是迷人的,新生活是值得期待的。可這一天我突然發現,原來這些,所有我不在意的這些,竟都可以成為我今生今世的證據!我曾擔心自己今后人生踽踽,無人記掛,無人想念,可那會兒讀到此處,我卻有些安心了——起碼家中的老墻會記得。刻滿橫線的粱柱也記得。
高三那年,我去書城買英語輔導書,卻在推薦展位上看到了劉亮程的散文集《一個人的村莊》,覺得挺有緣分,便買下了。坐下來開始讀,一發而不可收,整個心神也沉淪進去。
劉亮程的文字里帶有一種極為沉靜而清澈的吸引力,李陀先生評價他:“劉亮程的才能在于,他好像能把文字放到一條清亮透明的小河里淘洗一番,洗得每個字都千千凈凈,但洗凈鉛華的文字里又有一種厚重。捧在手里掂一掂,每個字都重得好像要脫手。”
這或許和他本人在鄉野成長的經歷有關。1962年,劉亮程出生于新疆沙灣縣一個叫黃沙梁的小村莊。正是那片黃沙與綠樹交織的鄉村土壤,孕育了他的文學夢想。他在黃沙梁的土地上生長了二十余年,在那兒當過農民,種過地,也在勞動之余思考和寫點文字,幾乎所有的創作靈感都與此有關。這個村莊是他的根,是他命里供養滋生的河流。于是,他為它寫詩,他為它作文,他的村莊便永遠地活在了他的文字里。
你或許會說,朝出夕歸的鄉村生活,每天都是一個模樣,有什么好寫的。可劉亮程就寫了,年年歲歲,寫了一篇又一篇,然后一篇篇摞起來,印成了一本本的書。在這個村子里,房子被風吹舊,太陽將人曬老,所有樹木都按自然的意志生葉展枝。他在不慌不忙中,努力地去接近一種自然生存的狀態。他的文字里有村莊豢養的牲畜,有野地上的麥子,也有一只蟲、一棵草、一溜炊煙和一陣風。
他會以為一只仰面朝天的蟲子正在舒服地曬太陽,也跟著扔下鐵锨,并排躺下。他曾耐心地守候過一只小蟲子的臨終時光,他說不會為一只蟲子的死去而悲傷,他最小的悲哀大于一只蟲子的悲哀,可是他也說:“別的蟲子在叫。別的鳥在飛。大地一片片明媚復蘇時,在一只小蟲子的全部感知里,大地暗淡下去。”他也曾在凜冽的冬天被寒風吹徹,掖緊羊皮大衣,節儉地想把溫暖給藏起來,又袒露出一些真心:“我的親人們說我是個很冷的人,不是的,我把僅有的溫暖全給了你們。”
很寂寞啊。讀這本書的時候,我心想。可是在這種荒蕪滋長的寂寞中,卻蘊含了劉亮程對自然對生命極為深刻的體悟。這種體悟是簡單而純粹的。它用樸實親切的語言表述出來,獨有一股博大的真理的曙光,在寂靜中從容閃爍,如甘澧,似佳釀,余味悠長。
劉亮程的比喻十分簡單和老到,他不常用,可一旦用了,必定能抓到人心。在《炊煙是村莊的根》一文中有這么一句:“這個鐮刀狀的村子冒出的煙,在空中形成一把巨大無比的鐮刀,這把鐮刀刃朝西,緩匿而有力地收割過去。幾百個秋天的莊稼齊刷刷倒了。”初讀只覺得句子極妙,妙在語言結構。妙在其浩蕩的場面與壯觀的聯想。再讀,卻能在這沉著優雅的敘述中,隱約窺探到名為哲學的微芒,愈品愈有味道,它穿透了時間和空間上的界限,將象征豐收的鐮刀與村人作息產生的炊煙,若無其事地聯系到一起,毫無突兀感。
“寫作是一件真正可怕的事情。”劉亮程曾在他的日記里寫道,“最后這段生活將隱去,我的文字留下來,包括我寫的村莊、田野、牲畜、草木,都在我的文字背后消隱。”我不知道一個被文字記住的村莊是否不幸,可我覺得,相對于那些人走村空、湮沒在時間洪流中的無名村莊,黃沙粱能以文字的方式被記住,也算是此世它存在的證據了。
黃沙梁的世界,也是劉亮程心里頭的哲學世界。它是他一個人的村莊。它一成不變。它氣象萬千。
人的一天,乃至一只狗、一只蟲的一天,都只有二十四個小時。在這二十四個小時里,我們睡覺、吃飯、工作或者學習,只恨時間過得太快,一眨眼,又是一天過去。快節奏生活帶來的心靈上的浮華和喧囂,無法在日益豐富的手機游戲里得到消弭,不如尋一個安靜的日子,不慌不忙地坐下來,讀一讀劉亮程的文章,尋一片心靈的綠洲,來撫平躁動的靈魂。
編輯/胡雅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