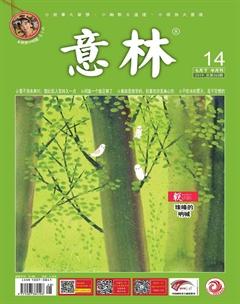兩個修鞋匠
劉荒田

在羽毛球場上揮拍時,感覺鞋子有點(diǎn)異樣,一看,鞋底前部分因黏合劑失效,多半已脫離。下了場,在回家路上,找到一個修鞋攤。由于沒有備用鞋,我聲明要“坐等可取”的服務(wù)。這攤子我去年來過,不同的運(yùn)動鞋,同樣的毛病——底部松脫。那次要把鞋子留在攤上,第二天才能取回。修鞋匠不茍言笑,對活計的質(zhì)量極為在乎,這就是上一次拒絕我當(dāng)天拿回的緣故。我對師傅說,這鞋子離報銷之期不遠(yuǎn),看能不能涂膠水把底部粘上,多對付幾個月。他拿起鞋子一看,差點(diǎn)“呸”出來。“沒法整,運(yùn)動鞋都有這毛病,我都修怕了。”“粘不緊不怪你,試試看,反正我也是湊合。”他頭也不抬,只管給擱在膝蓋的鞋子上油。“送上門的生意也不接?”“怎么接?粘好了,一穿上鞋底又掉下,羞死人嘛!”“你的意思是,我只好扔掉,買新的?”他沒說話,意思是:“還用說?”我訕訕離開。嚴(yán)詞拒絕并無風(fēng)險的生意,這樣的釘子我回國以后第一次碰到。
我不死心,找到另外一個攤子。我道明來意,他干脆地說:“行!”我問:“能不能馬上修?”他說:“可以。”師傅把磨損了后跟的高跟鞋放在小凳子旁邊,給我的鞋子涂黏合劑。我坐在他對面,和他聊天。了解到,這濃眉大眼的漢子是四川人,四十三歲,來南方修鞋十多年,日子還可以。黏合劑涂好,他用力壓緊。問我:“要不要縫線?”我說:“好是好,但鞋子快報銷了,不值得多花錢。”他說:“只要十塊。”我又開玩笑:“一只還是一雙的價?”他迷惑地看著我:“有按只收錢的嗎?”我說有:“二十多年前我在深圳一個擦鞋攤,女師傅開始時說要一塊,最后要兩塊,理由是:剛才說的是擦一只的價。”師傅笑起來,帶著職業(yè)自豪感:“我不干這下三爛。”
我付錢時,告訴這位四川漢子,我剛才去另外一家,師傅死也不肯接這活。他義正詞嚴(yán)說:“生意能這樣做嗎?客人需要,就盡力做好嘛!”
我穿上加了黏合劑又在邊沿縫了一道線的鞋子,滿意地離開。在路上想,第一個師傅,雖然為了他的拒絕而帶點(diǎn)兒芥蒂,可是,從心底欣賞他的風(fēng)骨。為了名譽(yù),為了質(zhì)量,他就是有所不為。從他冷傲的神情捕捉到早已被商品巨潮卷去的清高。我卻不能不喜歡第二位,他的善體人意,他的馴服和機(jī)靈,就是當(dāng)今正派生意人成功的訣竅。要問以后我會找哪一位修鞋,從理性上說,要找第一位,即使碰釘子;從慣性上說,我會找第二位。說得嚴(yán)重點(diǎn),這是人格分裂的表征。然而,誰不是這般,在知與行,在操守和權(quán)宜,在理想和現(xiàn)實這一類關(guān)系中,私下敬畏,由衷地贊美高尚,同時,懷著鄙夷、不屑、不甘、屈辱等復(fù)雜的負(fù)面情緒,去逢迎,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