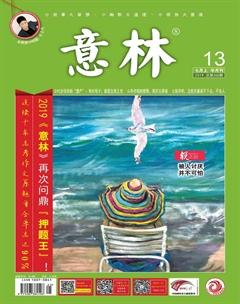被人討厭并不可怕
陳思呈

哲學家錢德勒說一切煩惱皆源于人際關系,有時候覺得這真是一件悲哀的事。世界那么大,宇宙那么無垠,黑洞的照片都出來了,但我們的眼睛卻依然總是盯著身邊這些雞毛蒜皮的事情。我們的注意力,也總是無法免俗地聚焦于別人如何看待自己。
日本詩人小林一茶寫了無數清麗絕俗的俳句,那些詩句里,竟然有這么一句:“飛雁們,咕噥咕噥地,聊我的是非嗎?”
這么詩意的一個人,依然擔心被傳是非。所以,凡夫俗子如我們,擔心被非議,擔心被孤立,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
孩子在學校遇到了對他不友善的人,問我怎么辦。我并沒有很好的辦法,卻想到了自己有過類似的經歷,是在我剛上大學的時候。那是我第一次住集體宿舍;第一次必須24小時與一群陌生的伙伴相處。完全無法確定與她們是否投緣。
我媽對此比我還焦慮。她給我準備了兩個巨大的箱子,塞滿了她所能想象到的、全部生活的必需品。甚至在我們宿舍住了一個星期,因為她要親自感受我將要遇到的所有日常。一星期后,她帶著她的焦慮回家了,我卻發現,自己被孤立了。
那一個星期是同宿舍七個陌生女生互相熟悉的黃金時光,因為我媽的在場,我錯過了與她們互相熟悉、建立情誼的過程。我成為一個局外人,不知道她們這些天關心的是什么,不知道她們如何聚在一起議論輔導員的性格、隔壁宿舍的衛生。人群中往往需要一個異類來作為話題,增加彼此的親密感,我就成了那個異類。
曾經被孤立過,使我能深刻地理解人的心理。我明白了人性的殘忍,即人們會因為一個隨機的缺點,一個偶然的機緣,就把你踢出局,讓你成為人群的對立者;人們需要這種敵意,來讓他們的友誼更有味道。
我曾經非常害怕被孤立,但后來我回想,被孤立的時候,是我讀書最多、工作最有效率的時候。人群是溫暖的,但同時也是拖累。被孤立并沒有那么可怕,有的人之所以恐懼,原因在一本叫《被討厭的勇氣》的書中寫得很清楚:“不想被別人討厭,這對人而言非常自然的欲望和沖動,哲學家康德把這種欲望稱之為傾向性。對于很多人來說,僅僅是被討厭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可怕的印章,它意味著一種終極失敗。你的一切價值很可能因此而歸之為零。”
這本書對此提出一個明確的說法:當你被某人或者某些人討厭,這是你行使自由以及活得自由的證據,也是你按照自我方針生活的表現。如果有人討厭你,那不是你的問題。
被他人討厭的人,客觀上也得到了很多自由:時間上的自由、行動上的自由。我前面說到自己在被孤立時的高效閱讀正是這個證明,在高效和高密度的閱讀中,有一些抽象的人陪伴了我,他們是書上的人,比身邊的人更智慧,他們與我交換著能量,并緩慢地讓我意識到,我更大的舞臺不在這里。
要在更廣闊的天地里尋找自己的位置。實際上,我們每個人都屬于多個共同體。如果你在一個集體里被孤立,說明你不屬于這個集體,你可能屬于更廣大的集體。如果在這個共同體里面沒有歸屬感,那么此時,我們需要做的就是置身事外,尋找更大的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