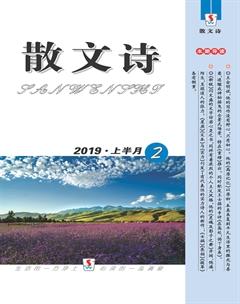文藝性調查初探
龍彼德
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1918~2008),1970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他的生世可以用“勞改”“驅逐”“流亡”“榮譽”“回歸”五個詞來概括,而連接它們的關鍵詞是“創作”,這是他視之為超過生命的工作。無論是在國內勞改,還是在國外流亡,他都沒有停止創作。前是打腹稿,反復背誦;后是寫下來,再發表。他的長篇小說《古拉格群島》,對前蘇聯勞改營作了全面的描述和分析,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他自稱乃是“文藝性調查初探”,這也是他寫作的基本方法。散文詩《破桶》,就是運用這種方法寫出來的。全文由八節組成。第一節點出了調查初探的時間與地點:“是的,卡頓森林,讓一位往日的士兵去重訪,是令人悲惋的地方。”因為“森林一處,還留著十八年前的遺跡”。第二節與第三節寫“破桶”的發現、形狀與用途,表面上是狀物,實質上是寫人:“在這個掩體里,在漫漫的長冬里,九十天乃至一百五十天,在戰況膠著的拖延中”。他們將廢物利用,“取暖”“點煙”“烘面包”,度過那寒冷、漫長、危險的日子。“當煙火不盡地吐出時,吐不出的是圈在爐邊的人的思緒,要說而無法說出的話,要寫而寫不成的信——而后來,他們就這樣沉默以終。”作者的感情色彩相當鮮明!
第四節至第七節,交代“情況突變,掩體要被放棄”。盡管日久生情,勤務兵想把破桶帶走,卻受到上士的斥責,只好扔掉。“只有這個忠實服務過的破桶還留在掩體的門外。”是對人情寒薄的揭示?或是對歷史吊詭的見證?兩者皆有,文字的含量讓人驚訝。第八節是作者的緬懷與感嘆。緬懷“戰時的那些朋友他們是多么美好”;感嘆“那支持著我們的精神,我們的希望,還有無私的友誼”。雖然“這一切都像煙一般,消失了;如今,再也用不著它,這個銹爛的破桶便被完全遺忘了”,時代的復雜導致了情感的復雜,有褒有貶,但“精神”“希望”“友誼”仍讓作者牽掛,仍在他的心中,正能量還是突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