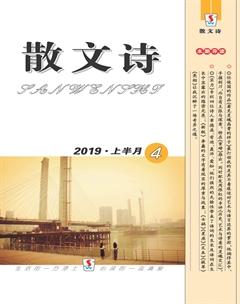歷史、藝術與詩意的靈魂交匯
周根紅
對歷史的詩意書寫,對藝術作品的詩意發掘,是散文詩(詩歌)寫作中最難把握、也最難突破的題材。曾幾何時,這類題材卻大量泛濫于散文詩(詩歌)作品之中。其問題也較為普遍。它們往往容易流于對歷史事件的“情景再現”,或對原文本的“語言翻譯”,因此,很多類似的作品大多是一次寫作的旅游觀光和文
本導讀。
任俊國的這組散文詩,迎難而上地選擇了這樣一種具有較高難度和寫作風險的題材,著實表現出詩人的勇氣和信心。讓人感到驚喜的是,他的這組散文詩雖然寫到了歷史,寫到了藝術,卻又真切地超越了歷史和藝術。它不是對藝術作品的簡單描摹,也不是對歷史賬本的現實檢閱,而是通過對意象系統的重建和深刻的思想創新著原文本的呈現方式,并加強了歷史的深度,從而把我們帶入到一個歷史、藝術、詩歌交織的多元體系里。詩人通過對《搶掠薩賓婦女》《搶掠波呂克塞娜》《圣十字架傳說》《大衛》《帕修斯》等作品的詩意再造,對戰爭與和平、搶掠者與被搶掠者、放逐與堅守、高貴與謙卑等內涵進行了多向度的書寫。
這組散文詩也表現出詩人對不同藝術形式的文本轉譯過程中寫作技巧的純熟、敏感和獨特的把握。如在寫作《大衛》雕塑時,詩人選取了觀看大衛雕塑時“45度的最佳仰角”:在寫作赫刺克勒斯雕塑時,聚焦于藝術家“如何表達一支離弦的箭”;在寫作六尊圖拉真時代雕像時,側重于人物的安靜和凝思;在寫作帕修斯雕塑時,著重于銅和錫的比例……這些角度和細節的選擇,較好地避開了對藝術作品進行詩意轉換時“全面解讀”的寫作范式,而是通過選取關鍵性的一點深入挖掘,既節約了筆墨,避免落人類似題材寫作的俗套,更為重要的是,詩人所選擇的這些切人點,正是詩人所要表達的“思想內核”,是詩人進一步追問和提升的入口。因此,藝術作品不過是詩人寫作的一個突破口,歷史背景也只是為
進一步提升詩歌思想的底色,詩人所要表達的其實是一種精神的追尋和靈魂的堅守。詩人試圖在藝術作品的文本表達和造型審美中,尋找到遺落在時代歷史中的精神印記。
詩人北島曾經說:“詩人應該通過作品建立一個自己的世界。”蘇格拉底在回答別人的詰問時說,盡管地球上并不存在一個理想的“城市”,但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很多人,仍將按照這座城市的準則行事。說到底,這個“世界”和“城市”,只是一種存在于詩人內心的空間,是一種具有高度精神化的空間。正是基于對自身精神世界的建構和靈魂的安放,詩人從藝術和歷史中不斷走向“高貴的靈魂”和“高處的精神”:從《搶掠薩賓婦女》雕塑中詩人發現了“那個看不見的旋轉中心,叫和平”;從《搶掠波呂克塞娜》的雕塑中反思雕刻家對歷史的搶掠,對觀看者靈魂的搶掠和對作者的心理搶掠;從一座卓立的塔和但丁的藝術中,表達出“高處”的追求:從“阿諾河水的聲音”里,燭照出圣十字教堂流淌的信仰;從《大衛》雕塑中看到“靈魂從天堂回來,人性開始覺醒”;從帕修斯雕塑中的銅和錫的比例,傳遞出思想和技藝的爐火純青……從這組散文詩的字里行間,我們能夠深刻地領悟到作者所追求的靈魂和情懷。
用厚重的歷史背景,提升時光沉積后的藝術品質;用詩歌的語言,實現藝術與詩歌的交相輝映。歷史和藝術所傳遞出的思想,是阿諾河;每一位藝術家和其作品,其實就是一座橋。詩人對歷史和藝術的寫作,其實正如他所說的,是一次致敬:“向老橋致敬,陽光一直陪我站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