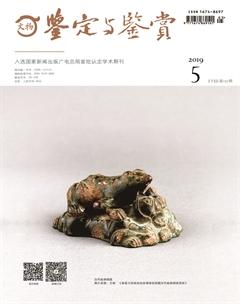融中西繪畫為一冶的藝術家
侯韶鵬



摘 要:潘玉良是民國時期杰出的女畫家,其藝術創作涉及領域較多,但彩墨畫是最能體現其“合中西于一冶”的藝術主張。文章分析了潘玉良所處的時代背景和求學經歷對其繪畫風格的影響,并從其后期成熟的彩墨畫作品中挑選幾幅人物畫和靜物畫,通過對具體作品的剖釋,探討她是如何把西方繪畫手法和中國傳統藝術的審美進行融合的。
關鍵詞:潘玉良;時代背景;求學經歷;彩墨畫
1 時代背景
20世紀初,西方現代藝術思潮涌入中國,中國藝壇上掀起了改良美術教育的熱潮,中國傳統文人畫藝術也遭到沖擊。如新文化領軍人物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演講中就提出“舍宗教而易以純粹之美育”說,堅定美術教育改革重要性。陳獨秀在《新青年》雜志上率先高呼美術革命,提倡“采用洋畫的寫實精神,以改良中國畫”,對西方的寫實畫法大力推崇。可見“借鑒西方,中西融合”已經成為當時繪畫藝術教育的時代主題,推行新的美術教育已經成為當時社會的一個趨勢。“五四運動”以后,各種新式美術學校、西畫社團在中國蓬勃發展,中外美術交流活動也趨于頻繁,大量青年藝術家在這種開放、自由、多元化的環境下選擇出國深造,積極探索國畫新出路。潘玉良不僅受益于這個時代,還成為中國美術改革運動的重要實踐者之一。
2 主要求學經歷
1917年,潘玉良在潘贊化的幫助下考上了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因為對浴室洗澡人群以及自己的裸體進行素描習作,而備受非議。為了尋求繪畫技術上的進一步發展,在校長劉海粟的建議下,1921年潘玉良取得留學津貼赴法留學。求學期間,先后在里昂國立美術學校和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校就讀,主攻素描和油畫,學習了西方古典寫實主義、印象派、后印象派、野獸派等眾多流派的風格與繪畫技巧,為日后的作品創作打下了扎實的功底。1928年學成回國,當時的中國藝術界中西文化碰撞、爭鳴的學術氣氛濃烈,潘玉良積極參與國內畫展,受劉海粟、徐悲鴻等諸多名流指導,開始臨摹和研習中國傳統繪畫。在回國的十年時間里,積累了一定的中國傳統繪畫基礎,影響了后來的創作路線。1937年,潘玉良借參加“萬國博覽會”和舉辦畫展的機會,經過蘇聯和德國,再次赴法。此時的潘玉良已經接受了中西藝術的共同熏陶,開始探索自己的繪畫風格,尋求藝術突破。
3 “合中西于一冶”——彩墨畫
潘玉良在白描、油畫、彩墨畫、雕塑、版畫等諸多領域都有所涉獵,從她大量的作品傾向能看出來,她是一個追求進步和改變的藝術家。而且她一直在積極探索如何從西方的“油畫系統”逐步轉換到一種東方式的表達,其中留下來的彩墨畫最能體現她個人特色和“合中西于一冶”的藝術主張。二次赴法后,潘玉良致力于研究和創作彩墨畫作,她的彩墨作品是以毛筆、宣紙、國畫顏料作畫,在作品中融入西畫的繪畫技巧和構圖方式。尤其20世紀50年代后的彩墨作品,已經能熟練地運用野獸派的色彩表達、后印象派的點彩諸法,將西方畫中光影處理手法施于中國畫,作品整體風格和處理上都符合中國繪畫審美特征,中西合璧的藝術風格已經趨于成熟。
如1954年創作的《讀書女》(圖1),畫中是一個身著紅衣、半裸坐在蒲團上的東方女性。女子一只手撫在脖頸上,另一只搭在膝蓋處,腰部微側,低頭看向手中的書籍,營造一種愜意舒適的感覺。受西方古典藝術審美影響,潘玉良作品中的女性多為圓潤豐滿的體型,如圖中的女子柳葉眉、丹鳳眼,具有典型的東方女性面部特征,但一反傳統國畫中塑造人物單薄、纖細身形的方式,而采用富有變化和流暢的線條,刻畫了一個身材飽滿豐腴的東方女子。身體輪廓簡練精確,充滿質感,下半身格外肥厚的腿部和坐著的姿勢,使得整個畫面看起來穩定而平衡。人物的肌膚用大面積暖色平涂,畫面顯得堅實飽滿,中國畫的平面效果躍然紙上。背景處理上,則打破了國畫中傳統的留白手法,通過擦染的方式暈染背景,畫面的四角格外加深墨色,畫面中心人物服飾和蒲團采用紅色搭配,顏色明亮,和暗沉的背景色對比強烈,試圖創造油畫中光和色給人帶來的感官效果。1963年創作的《撫頭女人體》(圖2),背景上更是采用了西方油畫的點彩技法,用大小不一的色點和交錯重疊的短線進行處理,試圖制造油畫那般的多層次,在畫面中營造較為明顯的明暗關系。
潘玉良“合中西于一冶”的主張不僅在人體彩墨作品中能體現出來,在靜物作品上也有所體現。如1966年創作的《捕捉之前》(圖3),近處的麻雀線條清晰細膩,給人以真實緊繃的質感;而遠處的貓筆觸灑脫自然,線條簡單虛化,通過若有若無的細線勾勒輪廓,給人一種蓬松自然的感覺,這種近實遠虛的處理使畫面看起來十分有空間感。另一個處理就是畫面的中心位置,瓶中紅白相間的花束用大塊的紅白色塊填涂,最靠前的白色花朵輪廓線自然地隱藏于暗部的枝葉之中,通過這種明暗處理體現物體的遠近。潘玉良通過使用西洋畫的處理手法,彌補中國畫因為材料工具限制而光影效果和空間感差的缺陷,成功地將中國畫的筆墨精神和西畫的實體質感融入到彩墨畫中。
還值得一提的是,潘玉良創作的彩墨作品中有強烈的民族色彩,如繪畫對象多為東方女性,題材也多以中國民族風情的活動為主(圖4);在以花卉為主題的系列作品中,具有中國特色的元素的陶瓷花瓶和其他中國元素出鏡率也極高(圖5)。這些都體現了潘玉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愛與中國人身份的認同感。潘玉良二次赴法期間,一直拒絕加入法國國籍,并多次在家書中提及想要回到祖國大地。但由于赴法期間國內形勢復雜,其到去世都沒能回到祖國。病逝前囑咐友人,自己要穿旗袍入殮,并且一定把她的作品設法運回祖國。其生前的最后幾幅作品之一的《臨窗窺視女人體》(圖6),表達了潘玉良對回歸祖國深深的渴望。
潘玉良的一生都沒有停止過對藝術的追求,她的繪畫藝術是在中西方文化不斷碰撞、融合中萌生發展的。她通過自己的實際行動,不斷嘗試突破已有的繪畫風格,去探索傳統文化如何與時俱進,在中國美術史上留下了燦爛的一筆。無論是在當時還是現在,如何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有揚棄地發展與傳承中華民族文化都是一個永不過時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