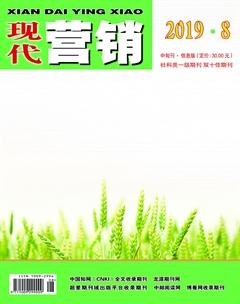商譽減值的文獻綜述與研究展望
胡群
摘 ?要:隨著市場化改革進程不斷加快,上市公司并購重組業務呈現爆發式增加,商譽總額急速飆升,背后積聚的潛在減值風險不容小覷。本文希望通過梳理國內外學者的文獻,總結有關商譽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一些研究展望,希冀對商譽的后續計量模式的改革有所幫助。
關鍵詞:商譽本質;商譽減值;經濟后果;減值測試攤銷
根據國泰安數據庫資料,2016-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商譽凈額分別為:1.049萬億、1.307萬億、1.299萬億。隨著商譽總額急速飆升,A股上市公司巨額計提商譽減值的做法也接踵而至。2019年1月4日,財政部發布的《企業會計準則動態》中提及,有不少人贊同采用商譽隨合并利益的消耗進行攤銷,以取代現行的商譽減值規定,這一舉措又將商譽問題置于會計處理的輿論中心。為此,本文希望通過梳理國內外學者的文獻,厘清商譽的本質,把握商譽的形成原因、影響因素、商譽減值的經濟后果及后續計量的研究成果,希冀對商譽的后續計量模式的改革有所幫助。
一、商譽的本質
商譽作為極具爭議的問題之一,其本質一直都是學術界和實務界關注的熱點,國內外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了闡述。
關于商譽本質的“三元理論”在會計領域引起了廣泛共鳴,即好感價值論、超額收益價值論和總計價賬戶論。好感價值論將商譽界定在融洽的商業關系、企業與雇員的良好關系、顧客對企業的好感上。超額收益價值論將商譽定義為企業所能賺取的超額收益的資本化價值。總計價賬戶論將商譽定義為企業總體價值與賬面凈資產公允價值的差額。
崔靜(2010)認為商譽本質就是一種協同效應。
張乃軍(2018)認為商譽本質上應該是并購資產未來獲取超額收益的能力,不能讓商譽成為損害投資者利益的“皇帝的新衣”。
綜合以上觀點,本文認為,商譽應該是一種因協同效應而產生超額收益的特殊資產,它并不具有可辨認性,因此它不同于無形資產。
二、巨額商譽產生的原因
(一) 并購方轉型升級的迫切性導致高溢價收購
吳輝(2018)指出,*ST三泰以7.5億元的高價收購了凈資產賬面價值僅為0.4529億元的煙臺偉岸,評估增值率高達1555.87%,產生6.7755億元的商譽,在收購完成后的第二年就對原商譽的96%(6.5272億元)計提了減值。*ST三泰高溢價并購的原因是煙臺偉岸的互聯網特性恰好符合其轉型升級的需要,但這正是由于這種迫切性導致了巨額商譽的形成。
(二) 被并購方做出不切實際的業績承諾
方重等(2016)從業績承諾的角度出發,認為標的公司的業績承諾對高估值溢價并購起到明顯的支撐作用。
毛心怡、賓幕容(2019)指出,一些中小企業為了通過被上市公司收購的方式帶來利益,夸大業績以獲得高業績與高估值,收購方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接受這種高溢價并購。
從上述文獻可看出,高溢價并購是由于收購方和被收購方雙方面原因造成的,高溢價并購、價值高估必然直接導致巨額商譽的形成。
三、 商譽減值的影響因素
現有文獻表明,企業計提商譽減值受內、外兩方面因素的影響,內部因素主要以盈余管理為主,外部因素主要以宏觀經濟環境為主。
(一) 內部因素——盈余管理
Masters-Stout(2008)、Majid(2015)等認為管理層將計提商譽減值作為調節利潤的手段。
王秀麗(2015)通過對影響商譽減值計提的因素進行實證檢驗,她發現上市公司商譽減值不是由于經濟因素所導致的,而是受管理層盈余管理動機影響的。
(二) 外部因素——宏觀經濟環境
Francis(1996)發現商譽減值的計提會受到經濟變化的影響。
SapkauskieneAetal(2016)指出企業計提商譽減值的行為受到經濟危機的影響,為了在經濟復蘇時期獲得更高的經濟效益,企業更傾向于在經濟危機時期多計提減值,為將來預留盈利空間。
四、 商譽減值的經濟后果
(一) 企業價值
市場投資者將商譽資產減值視為公司負面消息,解讀為公司未來盈利能力下降,繼而做出賣出公司股票的投資決策(Lietal.,2011)。
韓宏穩等(2019)通過實證分析發現商譽信息中商譽增加并不顯著提升公司股價崩盤風險,只有商譽減值對股價崩盤風險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且這種影響作用在公司并購年度股價泡沫較高的情境下更加顯著。
(二) 債務融資
徐經長等(2017)指出當上市公司計提商譽減值準備的數額越大,其債務融資成本越高。
杜春明等(2019)研究發現商譽減值與企業債務期限結構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即債權人視商譽減值信息為負面信號,商譽減值金額越大,債權人更傾向于向企業發放短期貸款。
(三) 審計費用
葉建芳等(2016)發現,與沒有商譽的公司相比,有商譽的公司審計費用明顯更多,尤其是那些確實計提了不可核實的商譽減值的公司,其審計費用增加的更多。
鄭春美等(2018)發現審計師對并購商譽風險保持了應有的職業謹慎,增加審計收費以確保審計質量。
五、 商譽的初始計量
蔣芊如等(2015)指出,現行準則對企業自創商譽不予計量,僅以合并成本與合并企業的凈資產衡量商譽,這種做法是不符合商譽本質的,他們認為應對自創商譽進行顯性化處理。
陳樹民等(2018)認為企業會計準則僅對母公司對應部分的商譽加以確認,而少數股東部分對應商譽價值并未在報表中反映,這種做法極易造成個別公司人為操作影響商譽確認的情況。
張浩進(2019)指出當購買成本小于凈資產時計入營業外收入,而不確認負商譽,會虛增一定的收益,這種做法欠妥,他還提出應采用間接方法對自創商譽予以確認。
六、 商譽后續計量
對于商譽會計處理應當攤銷還是進行減值測試計提減值準備,學者們的爭論一直比較激烈。
2006年之前,我國會計準則規定以攤銷法進行商譽的后續計量,但該計量方式與商譽的實際情況不符。為此,財政部于2006年頒布新的會計準則,明確規定以減值測試法取代攤銷法,自此商譽會計處理模式在我國企業中開始全面轉變。
(一) 主張采用減值測試法
張信遠等(2019)指出通過簡單的“商譽減值改為攤銷”并不能克服減值測試法的缺陷,他們認為仍采用減值測試法,但在并購時企業要擠出多余泡沫以避免商譽過大,與此同時政府應該采取手段以遏制企業盲目的高溢價并購。
(二) 主張采用攤銷和減值相結合的方法
張乃軍(2018)指出目前我國對商譽只進行減值測試不進行攤銷的做法不符合會計謹慎性原則,他主張應適時調整商譽后續計量規則,采用攤銷和減值相結合的方式。
王仁平等(2019)指出應以權責發生制原則為基礎,將商譽這一特殊資產按照合并利益的消耗而合理攤銷分配,當其出現明顯減值跡象時,計提相應的減值準備,即攤銷和減值相結合。
(三) 從商譽本質出發采用不同的后續計量模式
蔣芊如等(2015)認為應將商譽區分為減值部分和沖銷資本公積部分,對商譽僅進行減值測試無法客觀真實反映商譽的價值。
王靜(2015)通過對比,認為應根據商譽的經濟內涵將商譽分為“應該確認的商譽”和“不應該確認的商譽”。對前者采用逐年減值測試法,對后者采用沖減資本公積的做法或僅在財務報表中予以披露即可。
本文認為,商譽的后續計量模式不應該是“一刀切”的做法—只減值不攤銷亦或是只攤銷不減值,應該對并購過程中的商譽進行細致分析,首先應將可辨認的資產確認為無形資產,擠出多余泡沫以避免商譽過大,其次對于確認為商譽的部分,應從商譽的本質出發,區分為應該確認和不應該確認的商譽,對于前者采用減值加攤銷的后續計量模式,對于后者采取沖減資本公積的做法。
七、 簡評與展望
本文對目前國內外有關商譽減值的文獻進行了全面梳理,總的來說,關于上市公司商譽減值的研究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成果。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有三條主線:其一,通過分析商譽的本質、形成原因、減值影響因素等三方面的內容,聚焦于探析為什么會出現商譽減值;其二,從不同的角度出發,通過實證和案例分析深入探討商譽減值的經濟后果;其三,從會計的初始計量和后續計量來探討目前商譽會計存在的問題。為此,本文審慎的對商譽減值的研究方向做出展望。
(一) 自創商譽和負商譽的確認研究
很多學者認為目前商譽的初始確認存在一些問題,他們主張應該確認自創商譽,但是對于何時確認、如何確認的研究尚少。現行會計準則下,對于并購中合并對價小于享有凈資產公允價值份額的差額部分計入營業外收入,并不確認為負商譽,對這種做法應進行進一步研究。
(二) 商譽后續計量方法的改進研究
目前商譽減值受人為操縱的影響較大,上市公司“洗大澡”、“業績大變臉”的頻繁發生,商譽巨額減值似乎成為了資本市場的一顆“地雷”,因此對商譽的后續計量方法是否要適時調整以及如何調整應該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參考文獻:
[1]張乃軍.莫讓商譽成為“皇帝的新衣”——關于商譽處理的理性分析.會計之友, 2018:(18).
[2]王仁平,張旻逸.我國商譽會計面臨的挑戰及對策[J].中國注冊會計師,2019,(4):4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