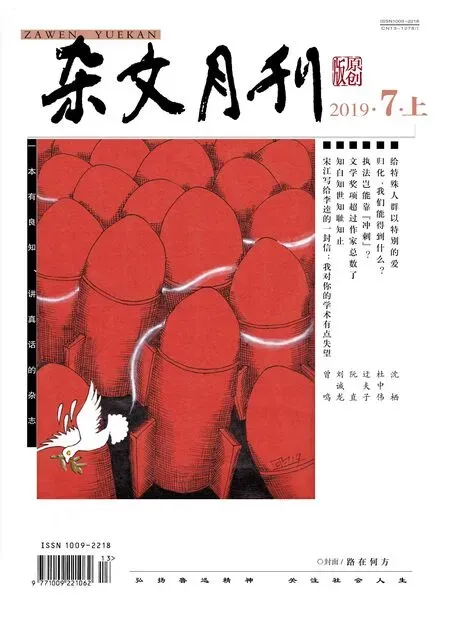我新發現
——寫在與雜文結緣十年的日子
●齊世明

創作就是發現!寫詩是發現詩意,散文發現情境,小說發現新的人物和珍珠一樣閃光的細節,寫雜文就在于發現新的思路與觀點、新的呈現方式。
無法否認,今日之世界,正是文化貶值,物質與技術主義泛濫的年代,相伴著電子產品及副產品光怪陸離地涌現,我們的文化與思想巨人在哪里潛藏?我們的人文精神與文化傳統又在何方抑郁?
于是乎,觸目可見,金錢決定著尊卑,快感決定著幸福,物質決定著存在,娛樂決定著時尚……
慢道雜文過氣,此際更須雜文——因為雜文的“初心”與使命。
我新發現,雜文的“初心”就是“砸”文,亦稱“扎”(針)文。雜文是最具中國特色的文種,迅翁們創下的特色名牌洋洋乎而成大觀,概因其“砸”丑“砸”惡,“砸”兇“砸”害,“砸”假冒偽劣,這正乃雜文二性:現實性與批判性。今日,雜文家作為療治社會沉疴的“心科大夫”“精神醫生”,怎么能“下崗”?“啄木鳥”前無病樹了么?“銀針”面前少“病灶”了么?
而今朝之雜文仍是真文。怎么真,真誠之文。今朝,所謂有痛點、有筋骨、有溫度之上乘雜文,恐怕要皺著眉頭寫甚或含著熱淚寫,才是雜文家起碼的真誠吧。
我新發現,雜文真正是一門藝術,是講求說“不”的文藝學品類,在藝術精神上是“我不茍同”,在藝術技巧上是“我不趨附”。
這個“不趨附”,不但是不按常規“出牌”,對行文傳統說“不”,對流行(敘述)語言也說“不”。唯重創新,絕不重復他人,也不重復自己。
這樣,我新發現,蘸著心血敢為人先的雜文家身高、容貌各異,但擁有共同的“血型”“體溫”與共同的稟性(也是雜文的使命):
心天容不下陰影,眼前見不得污穢;
與蒼生同頻,與時代共振;
心思激濁揚清,筆馳喻世明言。
而雜文的“形象”標幟也自顯:春蠶與紅燭。那敢于用我筆寫我心的雜文作者,都是春蠶,吐絲不斷,全不顧自己的“壽命”;都是紅燭,一遇陰霾,便閃動思想的火苗,盡管自己也有痛苦的眼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