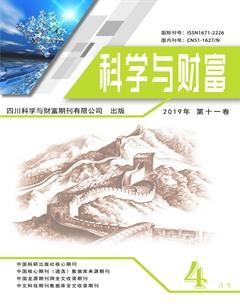聞一多的詩歌創作
陳強
一.中西文化共通滋潤下塑造的獨特人格
聞一多原名聞家驊。清光緒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1899年-1946年)生于湖北浠水縣(今湖北省黃岡市浠水縣)巴河鎮聞家鋪的一個書香家庭。聞一多于1912年考入清華大學,他喜歡讀中國古代詩集、詩話、史書、筆記等,具有著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學底蘊,10年的清華學習使他對西方文學也有了自身獨到的理解,“中西合璧”和“多元并蓄”的教育培養了他對自由思想與獨立精神,22歲(1922年)去美,學畫三年,卻找到了他的詩人之筆。可以說,在聞一多的身上,有著中國五千多年的文化積淀,承載著西方浪漫主義和理性思想的新潮,受到了美學藝術的感染,懷揣著深深的愛國情感,他所處的時代,他個人的經歷奠定了其國學和西學的文學基礎。聞一多首先是學者,是美學家,是藝術工作者,是新舊思想交替中承上啟下的青年,在這個基礎之上他成為了詩人,因而在他的詩中帶有著屬于學者的理性,屬于畫家對于美的敏感,屬于新青年的熾熱與深情。在中西文化共同滋潤下塑造的獨特人格是他在后來的學術生涯中能夠成為新詩理論的開創者的重要原因。
二.聞一多自身對詩歌創作的理解
對于新學和舊學,聞一多先生內心是具有矛盾性的,一方面他欣賞西方的人文主義文學,美學原理,文學批評等文學藝術,但對西學的有些方面不能茍同甚至反感,另一方面,在當時,中國社會遭受列強欺壓的事實以及他在美國留學時感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刺激了他強烈的愛國情懷,尤其清華的西方熱風氣讓他寫下《美國化的清華》一文,直指美國的文化不值得我們學習吸收,相比之下,他認為東方文化的生活方式是最理想的,我想,這與他長期受到中華古典文化的浸染又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因而,在他的詩作中,雖然有西方文學的影響,但從骨子里滲透出的感受,我以為,中華古典文學的筆觸更加深刻。但這并不是說聞一多是保守主義者。1920年,聞一多在《征求藝術專門的同業者的呼聲》一文中,就提出了富有時代意義的新觀點,他說:
我們談到藝術的時候,應該把腦筋里原有的一個舊藝術底印象掃去,換上一個新的,理想的藝術底想象。這個藝術不是西方現有的藝術,更不是中國的偏枯腐朽的藝術底僵尸,乃是融合兩派底精華底結晶體。
在1923年,他發表的《<女神>之地方色彩》進一步強調了這一觀點:
我總以為新詩徑直是“新”的,不但新于中國固有的詩,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詩,換言之,它不要做純粹的本地詩,但還要保存本地的色彩,它不要做純粹的外洋詩,但又盡量的吸收外洋詩的長處,它要做中西藝術結婚后產生的寧馨兒。
從聞一多的這兩段論述之中,我們可以讀到他對于新詩的獨特看法,既新于東方,也新于西方,表現了新時期下的一場詩歌的重新創造,在這之中,我們可以很深刻的感受到聞一多對于社會發展潮流的把握,對于中國文化的自信,對于西學的不盲從,在新文化運動充斥在對于中西方的絕對肯定或否定的狂熱中時,聞一多先生能夠以其學者的素養,理性的分析,提出對于中西方文化的辯證認知與創新,我認為這是極具前瞻性和預見性的。與此同時我們也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聞一多在當時對于新詩的定位是具有重要歷史價值的。而這也為其提出新詩“格律”的理論打下了思想基礎。
三.戴著鐐銬跳舞
在《詩的格律》一文中,聞一多這樣寫道:
假定“游戲本能說”能夠充分的解釋藝術的起源,我們盡可以拿下棋來比作詩;棋不能廢除規矩,詩也就不能廢除格,假如你拿起棋子來亂擺布一氣,完全不依據下棋的規矩進行,看你能不能得到什么趣味?游戲的趣味是要在一種規定的格律之內出奇制勝。作詩的趣味也是一樣。假如詩可以不要格律,做詩豈不比下棋、打球、打麻將還容易些嗎?難怪這年頭兒的新詩“比雨后的春筍多些”。
這是一個非常生動的比喻,其實,無論是下棋還是其他,都有自身的章法,而不是亂搞一氣,在“規矩”的束縛之下才能創作出更符合自身價值的作品,只有不會下棋的人才會亂下一通,而精通棋藝之人往往深諳棋的內在法則,同樣,只有不會作詩的人才會不講格律,懂得作詩,能作好詩的人是樂于而且善于“戴著鐐銬跳舞”的。他強調詩歌要重視格律,詩歌首先是詩,具有詩的格律,才能傳遞藝術的美。我們清楚的知道,聞一多先生并不反對白話,他反對的是以胡適為主體當代詩人的對于詩的無格律式改造,片面的追求詩的通俗易懂性而忽視詩作為一種文學的藝術價值的做法。誠然,胡適先生開創了白話的詩歌時代,賦予其自由的內涵,帶動了一大批新青年的新詩創作,但在這個過程中,詩歌的文學價值是被削弱了的,而聞一多先生在這里重新強調了形式之美的正面意義,使得大家能夠了解詩歌的創作是不容易的,是嚴肅的,它“戴著鐐銬”,它有著自身的使命。如果說胡適先生開創了一個詩歌的新時代,那么聞一多則是將詩歌的創作拉上了藝術的正軌。
四.聞一多在今天
作為青年時代的聞一多,身于社會變革的風口浪尖之上,處在新舊文化交替之時,卻能夠以時代的眼光,理性的態度來看待新詩的創作與發展,并運用自身的文化素養,投入以熾烈的情感,推動新詩格律化的進程,寫出耐人尋味的詩篇,將新詩的發展推入正軌,我以為這是很了不起的。在他的身上,有著畫家的明睿,書法家的深沉,詩人的才情。最難能可貴的是他的那一份理性,為他的詩作染上了一層厚重之氣,使其無論在哪個時代,讀來都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當然,在經歷戰爭波折和黑暗統治之后,他由學者變成了民主戰士,可能這一身份也更為人們所銘記,但我總認為,他在青年時期無論是在學術上,思想上還是詩作上都要比40年代后的他更有學習和研究價值,而他作為學者,詩人,知識分子的身份更應當被銘記。在今天這樣一個浮躁的社會轉型時期,我們需要的,應當是像聞一多這樣潛心研究,人格獨立,具有真實才學的知識分子,需要的是像《死水》一般振聾發聵的詩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