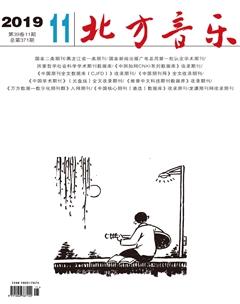淺析音樂中的三部性原則
成歌


【摘要】三部性原則是曲式發(fā)展的基本結(jié)構(gòu)原則,在音樂作品中具有普遍性。無論是在中國還是西方,三部性原則都是在音樂作品中被廣泛運用的。本文通過中西方音樂的對比,來闡釋中西方音樂思維中三部性原則的差異;通過對古二段式、三段式以及古奏鳴曲式發(fā)展的梳理,來窺測三部性原則的發(fā)展歷程;通過對三段曲式、三部曲式的詳細(xì)論述,了解三部性原則在具體曲式結(jié)構(gòu)中的運用;通過其它結(jié)構(gòu)與三部性原則的結(jié)合,論證三部性原則在音樂作品中的普遍性。
【關(guān)鍵詞】三部性原則;三段曲式;三部曲式;奏鳴曲式
【中圖分類號】J61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一、三部性原則的基本結(jié)構(gòu)
在傳統(tǒng)的曲式與作品分析中,三部性原則是曲式發(fā)展的一種基本結(jié)構(gòu)原則。一般來說,常用的曲式發(fā)展的結(jié)構(gòu)原則,包括呼應(yīng)原則、三部性原則、起承轉(zhuǎn)合原則、變奏原則和回旋原則等,除此之外,還有不常用的原則存在,如并列原則、拱形結(jié)構(gòu)原則等。三部性原則屬于常用的曲式發(fā)展結(jié)構(gòu)原則,是在呼應(yīng)原則基礎(chǔ)上發(fā)展起來的。
三部性原則就是在遙相呼應(yīng)的兩部分之間,插入一個中間部分。在具體音樂創(chuàng)作中體現(xiàn)為A-B-A,即主題(呈示)-離題(對比或引申展開)-返題(主題的再現(xiàn))。其中再現(xiàn)原則是三部性原則的核心。
(一)主題的陳述
在主題的初次陳述時,多為結(jié)構(gòu)和調(diào)性都比較穩(wěn)定的呈示性陳述,音樂的主題材料多比較統(tǒng)一,有相對比較完整的結(jié)構(gòu)。一般來說,調(diào)性與和聲較單純、明確(尤其是小型曲式),雖然也可能包含離調(diào)或轉(zhuǎn)調(diào)(如奏鳴曲式的呈示部),但通常總是以一個主要調(diào)性的確立為中心,而且常常是方整性的結(jié)構(gòu)規(guī)模,尤其是在小型曲式中,就連樂句也多為方整性樂句。這種方整性結(jié)構(gòu)有助于建立對稱感和平衡感。但是在大型曲式中,由于要求有比較大而廣泛的發(fā)展,動力性越來越要求突破這種穩(wěn)定、均衡的結(jié)構(gòu),從總體上看,更多的有不穩(wěn)定和開放性的特點。
(二)展開的中部
三部性的中部即發(fā)展部或?qū)Ρ炔浚蛘哒f是離題部分或破題部分,是和呈示部的主題和再現(xiàn)部形成對比的部分,是對呈示部的“否定”“突破”。這一部分總的特點是不穩(wěn)定陳述或動力性陳述,結(jié)構(gòu)和調(diào)性相對比較的不穩(wěn)定;樂思相對比較的零碎化和片段化;調(diào)性和和聲呈不穩(wěn)定狀態(tài),在大型曲式中這種不穩(wěn)定最基本的體現(xiàn)就是避免出現(xiàn)或強(qiáng)調(diào)全曲的主要調(diào)。當(dāng)然,不穩(wěn)定的程度要依樂曲內(nèi)容的不同和樂曲結(jié)構(gòu)的大小而定。結(jié)構(gòu)越長大,內(nèi)容越復(fù)雜深刻,一般來說,不穩(wěn)定或?qū)Ρ鹊囊蛩鼐驮蕉啵粗嗳弧P⌒颓接捎谄南拗疲恼归_部不可能進(jìn)行大的對比;但是在大型曲式中,如奏鳴曲的展開部一般都有比較強(qiáng)烈的對比,轉(zhuǎn)調(diào)頻繁,和聲的動力性強(qiáng),樂思的發(fā)展充分,內(nèi)部的結(jié)構(gòu)也較為細(xì)碎。
(三)再現(xiàn)原則
三部性原則包含了對立統(tǒng)一的辨證因素,“三”不是簡單的數(shù)量關(guān)系,而是具有概括事物矛盾運動規(guī)律的質(zhì)的意義,是“否定之否定”的矛盾運動規(guī)律,主要體現(xiàn)在再現(xiàn)部,也叫再現(xiàn)原則。
再現(xiàn)部對全曲的統(tǒng)一和均衡至關(guān)重要,通過中間部分與主題的對比,作為音樂發(fā)展結(jié)果的再現(xiàn)部往往不能再原封不動的重復(fù)第一部分,因而產(chǎn)生了各種不同性質(zhì)、不同程度的變化。如裝飾變奏(如肖邦的《第一、第四夜曲》)、改變力度速度(如柴可夫斯基的《遺忘的真快》中加快速度)、改變音區(qū)、改變音色(交響樂作品中常用)、改變織體(如肖邦的《c小調(diào)夜曲》見譜例3-4,再現(xiàn)部的結(jié)構(gòu)和旋律幾乎不變,但因速度加快一倍,織體變化很大——和弦加厚、三連音的音型,使得原來樂曲情緒由原來的深沉悲痛變成熱情激動)、改變和聲、改變調(diào)性(如比才的歌劇《卡門》第四幕末尾霍塞的小詠嘆調(diào)從原來的小調(diào)變成大調(diào))、改變結(jié)構(gòu)(擴(kuò)大或縮小)等手法。它的變化程度與作曲家的構(gòu)思和樂思的發(fā)展等多方面的因素有關(guān)。這一部分是對前面音樂矛盾發(fā)展結(jié)局的總結(jié),音樂矛盾得到了解決,是全曲的“否定之否定”部分。
二、中西音樂中三部性思想的對比
古希臘戲劇大師亞里斯多德在他的《論詩的藝術(shù)》一書中說“所謂‘完整,指事之有頭、有身、有尾……所以結(jié)構(gòu)完美的布局不能隨便起訖,而必須遵照此處所說的方式。”這是歐洲早期文藝作品的三部性思想。陶宗儀在他的《南村輟耕錄》中說“喬夢符(我國元代作雜劇家)博學(xué)多能,以樂府稱。嘗云作樂府亦有法,鳳頭、豬肚、豹尾是也。”這些都是一種“頭、腹、尾”形式的三部性章法,可見三部性原則是中外音樂作品的共有結(jié)構(gòu)原則。但由于文化傳統(tǒng)不同,這個普遍性中有極大的差異性。
(一)西方音樂的三部性思想
西方音樂有它傳統(tǒng)的曲式模式的:“呈現(xiàn)一個樂思,再呈現(xiàn)一個對比性的材料離開它,然后又回到原先的樂思——這樣的構(gòu)思是貫串西方音樂史的基礎(chǔ)。”“三段式,其三段必須重現(xiàn)第一段。”由此可見,西方音樂基本原則結(jié)構(gòu)就是A-B-A的三部曲式。西方音樂曲式思維偏重于采用在對比的基礎(chǔ)上完成統(tǒng)一,從古希臘哲人的“對立造成和諧”“互相排斥的東西結(jié)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調(diào)造成最美的和諧;一切都是斗爭所產(chǎn)生的。”到古典主義音樂貝多芬氣勢磅礴、具有橫掃千軍的英雄氣概的交響樂以及后來瓦格納的樂劇,都體現(xiàn)出這樣一種思維方式和審美趣味。常采用突變的方式來表現(xiàn)對比,追求強(qiáng)烈而鮮明的對比,三部性原則恰恰十分符合這一審美趣味,自然成為歐洲音樂作品曲式的代表性結(jié)構(gòu)原則——無論是小型的單三、復(fù)三或大型的奏鳴曲等——強(qiáng)調(diào)對比,同時又在對比的基礎(chǔ)上完成統(tǒng)一的布局,A與B之間往往對比鮮明(哥特式建筑的拱型結(jié)構(gòu)也是這一審美觀在另一藝術(shù)領(lǐng)域的恰當(dāng)體現(xiàn))。當(dāng)這樣的音樂傳入中國,被習(xí)慣于淡雅之聲的國人接觸時,他們說“西歐之樂,其聲壯厲,其狀促遽。”
(二)中國音樂三部性思想
中國的音樂則不同,傳統(tǒng)漢族音樂在曲式方面以變奏曲、聯(lián)曲體為代表;在以三部性原則為基礎(chǔ)構(gòu)成的三部曲式中,它常常表現(xiàn)為A-B-C形式,這就是中國音樂三部性原則“頭、腹、尾”的典型結(jié)構(gòu)特征。如我國古代最龐大的音樂結(jié)構(gòu)唐代大曲,從文獻(xiàn)的記載看,都是由三個大的部分組成:散曲;中序、排序和歌頭;破。
若采用A-B-A1形式,B與A1之間的對比也往往較為模糊,這就是再現(xiàn)的模糊性特征。
這里A1的開頭,使人覺得它是中間的一個部分,而感覺不到它已經(jīng)再現(xiàn)了,這是用“換頭”或“尾蓋頭”的民族傳統(tǒng)手法模糊了所謂的“再現(xiàn)性”的典型例證。它之所以能模糊人們的聽覺,把“再現(xiàn)”的開頭仍聽成中間段落的尾部,其巧妙之處,在與B與A1之間在樂句劃分上的交錯感。
再如《江河水》的“再現(xiàn)”是比較明顯的,但它在再現(xiàn)時也用了傳統(tǒng)的“換頭”的手法,把第一段的首句去掉,而從第二句開始再現(xiàn),也多少模糊了再現(xiàn)性,這是民族審美習(xí)慣的一種表現(xiàn)。
中國音樂小的段落甚至到一個樂句,也可以找到三部性的特征。
這是一個八板,每一小節(jié)為一板,一氣呵成,把它看成一段式。開始兩小節(jié)是一個教為完整的“樂逗”,在結(jié)構(gòu)上是一段式的頭;中間四小節(jié)連綿不斷,基本上是開始樂逗的發(fā)展和衍生;最后兩小節(jié)緊連中間曲調(diào),是開頭樂逗的再現(xiàn)。由此看來,這樣小的一段式,仍有三個有機(jī)的部分。
參考文獻(xiàn)
[1]錢仁康,錢亦平.音樂作品分析教程[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02.
[2]吳祖強(qiáng).曲式與作品分析[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