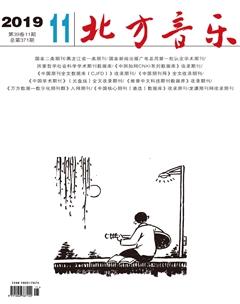布索尼對記譜法和音樂性的詮釋
【摘要】費魯奇奧·布索尼(Ferruccio Busoni,1866-1924)意大利鋼琴家、作曲家、理論家,是20世紀初盛行的新古典主義音樂的先驅(qū)。布索尼代表性的理論著作是《新音樂美學(xué)綱要》①,書中記錄了他對音樂本質(zhì)、純音樂、記譜法、改編以及音樂性的理解,完美呈現(xiàn)了布索尼的美學(xué)觀念,這本美學(xué)著作被稱為20世紀三大經(jīng)典美學(xué)著作②之一。
【關(guān)鍵詞】布索尼;記譜法;改編;音樂性
【中圖分類號】J613 【文獻標識碼】A
一部音樂作品,通過聲音展現(xiàn)出來,是作曲家情緒的詮釋,體現(xiàn)了作曲家創(chuàng)作理念的自由高度。在藝術(shù)作品受到世俗眼光的質(zhì)疑時,表達的情感和作品內(nèi)在的精神會澄清自己。
記譜法,即作曲家創(chuàng)作的樂譜,作曲家運用自己獨特的手段去捕捉靈感,使靈感融入到樂譜中并記錄下來。但是,樂譜之于即興演奏猶如雕像之于人的生活,作曲家用樂譜這種符號去表達和保存最內(nèi)在的情感。
然而作曲家們想要演奏者對樂譜進行詮釋,他們認為演奏會使創(chuàng)作更趨于完美,更接近創(chuàng)作本身。
通過記譜法,作曲家的靈感必然有所損失③,他要表達的理念還需靠他本人去還原。
對作曲家來說,記譜法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并且變得越來越重要。新的音樂創(chuàng)作手法也是源于古老的記譜法,并且作曲家們?nèi)匀粚爬系挠涀V法愛不釋手。
如果作曲家有方法,他們會希望演奏者無論何時、無論是誰、無論在什么條件下都能以相同節(jié)奏精準再現(xiàn)任何給定的作品。
但這是不可能的;這圣潔的孩子活潑、爽朗的本性使它反抗——它需要反抗。每一天的開始都與以前不同,卻總是沐浴在曙光之中。優(yōu)秀的藝術(shù)家在每次重復(fù)演奏自己的作品時也有不同,一時興起便會稍加修改,節(jié)奏會跟隨情緒的起伏而變化,但他們不會把這種即興的演奏方法標記在樂譜中,而是會一直遵循“永恒與和諧”這一給定的條件。
“改編”是記譜法的一種,這種創(chuàng)作形式時至今日還常被人們誤解。世人對于“改編”頻繁明顯的敵意,反對派對“改編”的非理性批判,促使我去尋求對“改編”這一創(chuàng)作形式更清晰的理解和詮釋,也激勵著我的”改編“事業(yè)繼續(xù)前行。我最終的結(jié)論是,本質(zhì)上,每一種記譜法是一種抽象觀念的改編,在筆捕捉它的瞬間,作曲家的意圖便已經(jīng)失去了本來的面貌。作曲家必須選擇一種風(fēng)格和調(diào)性,去記錄和展示自己的創(chuàng)作理念,用獨有的音樂形式和結(jié)構(gòu)去定義自己音樂的發(fā)展方向和范域。
這和人本身是一樣的,人是不會在出生時就有明確的志向,他覺得現(xiàn)在就是其職業(yè)生涯作出決定的最好時機。從決定的那一刻起,無論在人們以往的生活中有多少深根固柢的觀念,或是這種創(chuàng)作形式的發(fā)展不容樂觀,這些都不會成為我改編創(chuàng)作的阻力。一個人的音樂觀念能決定他的創(chuàng)作風(fēng)格;就像一個人能成為士兵或是牧師,這是一種原始的安排,由人內(nèi)在的本質(zhì)決定的。人們往往會忽略一個事實——改編并不破壞原作,因此,原作不會通過改編而遺失。
而且,每一次演奏也是對作品的改編,無論演奏者自由發(fā)揮與否,原作也不會被湮沒。一部音樂作品在其音響開始之前和逐漸平息消逝之后都是完整存在的,音樂作品既存在于時間之內(nèi)又存在于時間之外,這就是音樂作品的本質(zhì),可以把它放到原本無形的時間概念里去重新定義它。
至于其他,貝多芬許多鋼琴作品聽起來像管弦樂作品的改編;舒曼許多管弦樂作品像鋼琴片段的組合——在某種程度上,他們都是這樣。
說來也奇怪,變奏曲只是建立在一個借來的主題上進行一系列的變化組合,它卻受到崇拜者的高度尊重。相比之下,在改編曲中,改編的越巧妙、越有獨創(chuàng)性反而越不受歡迎。
因此,改編并不受推崇,因為它改變了原作;而變奏曲是好的,盡管它“改編”了原作。
德國人使用的術(shù)語“Musikalisch”(音樂性)在某種意義上與其他語言使用這一術(shù)語的涵義不同④“這是一個屬于德國人的概念,而不屬于普通大眾”,我認為這種表達是不準確的。“音樂性”源于音樂,就像“詩意性”源于詩歌或“物理性”源于物理(學(xué))。當(dāng)我說“舒伯特是最有音樂性的作曲家”時,同我說“亥姆霍茲是最具物理性的物理學(xué)家”是一樣的。那就是音樂性,游走在節(jié)奏和音程之間的音響。如果說“音樂作品”被封閉在一個櫥柜里面,這個櫥柜就有了“音樂性”⑤。相比較而言,“音樂性”比“悅耳”有更深層的意義。一位著名詩人曾評價我說:“我作品中的音樂性太強,以至于很難設(shè)計音樂的結(jié)構(gòu)布局”。埃德加·艾倫·坡(Edgar Allan Poe,19世紀美國女詩人、小說家和文學(xué)家)評論我的音樂時說“靈魂隨著魯特琴和諧的樂律起舞”。最后,如果有人說“笑聲的音樂性”,也許他說的很恰當(dāng),因為笑的聲音聽起來像音樂。
僅限在德國來看,在音樂演奏技術(shù)方面有很強的辨別力和敏感性的人,才可以被稱作是有“音樂性”的人,這才是這一術(shù)語應(yīng)用的意義所在。這里的“技術(shù)”,是指節(jié)奏、和聲、調(diào)性、結(jié)構(gòu)以及主題動機的處理。他把這些技術(shù)處理的越微妙,他的演奏就具有更多的“音樂性”。
正是由于對這些音樂元素的高度重視,“音樂性”自然而然地成為一個音樂家最重要的氣質(zhì)所在。因此,擁有完美演奏技術(shù)的音樂家可以被視為最有音樂性的演奏家。但人們所說的“技巧”不只是機械地演奏樂器,所以“技術(shù)性”是包涵在“音樂性”的涵義之內(nèi)的。
事情發(fā)展到現(xiàn)在,甚至可以說一個作品本身具有“音樂性”⑥,或甚至斷言像柏遼茲這樣偉大的作曲家缺乏音樂性⑦。“無音樂性”傳達著最強的責(zé)備,因此,被責(zé)備的音樂家便似乎被放逐一般⑧。
像在意大利這樣的國家,所有人都參與到音樂的樂趣中,這種對音樂家有無音樂性評價的分化就變得多余,因而在意大利語中找不到相應(yīng)的詞匯。在法國,充滿活力的音樂并沒有滲透到人們的生活中,因此這里有音樂家和非音樂家之分;其余的,有些人“非常喜歡音樂”,而有些人則“完全不關(guān)心音樂”。只有在德國,“音樂性”天賦才能成為一種榮譽,也就是說,人們不僅僅要熱愛音樂,更要理解它在技術(shù)上的表達,這樣才能真正理解音樂。
無數(shù)人在支持這個活潑的孩子,熱心地加入他的行列,他在嚴重跌落后可能不會馬上重振旗鼓,然而音樂這孩子畢竟年少,他不朽的本性一定會展現(xiàn)出來;當(dāng)他不再一味地追求“音樂性”時,自由地日子就會來臨。
注釋:
① Busoni,Sketch of a New Esthetic of Music,布索尼,《新音樂美學(xué)綱要》,1907年以德文首次出版,1911年英文譯本出版,translated by Dr.TH.Baker。這本美學(xué)著作共十一節(jié),前三節(jié)由姜丹先生于1988年翻譯完成并發(fā)表于《音樂藝術(shù)》。此譯文是《新音樂美學(xué)綱要》的第四、五節(jié)。
②20世紀三大經(jīng)典美學(xué)著作:德彪西《克羅什先生——一個反對音樂行家的人》、布索尼《新音樂美學(xué)綱要》、艾夫斯《奏鳴曲前的隨筆》。
③在音樂中,記譜法對于音樂風(fēng)格的影響如此強烈,并且束縛了人們的想象,記譜“形式”從作品中呈現(xiàn)出來,并且表現(xiàn)出一成不變的風(fēng)格。作曲家E.T.A霍夫曼就是典型的例子去證明這一點,因為在他的作品中凝結(jié)了他悲劇性的智慧。這位卓越音樂家的精神觀念迷失在幻想情緒中,陶醉在先驗主義的自由精神中,正如他在作品中常以獨特的方式去闡釋自己,要自然地流露——這樣人們才會推斷出——在他作品中,夢幻般的先驗藝術(shù)音調(diào)語言和表達方式的高度契合性。事實上,他以精準的音樂語言非常有效地描繪這一切——神秘主義的面紗、自然的和聲、超自然的快感、夢境邊緣的朦朧微光——所有這些讓人們覺得,他可以用音樂符號詮釋他的思想。然而,將霍夫曼較好的音樂作品和他較差的文學(xué)作品相比較,你會悲傷的發(fā)現(xiàn)他在戲劇盛行的時代去追求傳統(tǒng)形式和音調(diào),這讓他從詩人變?yōu)樗兹恕5牵瑥幕舴蚵珢刍孟氲囊魳防砟钪形覀円矊W(xué)到很多,而且其文學(xué)洞察力常常令人感到欽佩。
④布索尼或許考慮到“音樂性”這一術(shù)語在南歐語境下會有不同理解的問題。該術(shù)語在英語和斯堪的納維亞語匯中,都能精確地同德語保持相同的意義。(譯者注)是不是阿諾爾德·勛伯格的手寫注釋?
⑤唯一一種能被稱作有音樂性的人是歌手,因為他們自己能夠唱出曲調(diào)。相同的,當(dāng)被觸摸時通過某些技術(shù)發(fā)出聲音的小丑,亦可稱作偽音樂人。
⑥ “但是這些作品充滿音樂性”,一位小提琴家這樣評價一部在我看來十分平淡的四手聯(lián)彈。
⑦我曾聽到過有人非常嚴肅地說“我的狗音樂性很強”,難道這只狗比柏遼茲的音樂性更強嗎?
⑧ 這是我自己的命運。
作者簡介:王曉娜(1981—),女,黑龍江省勃利縣,哈爾濱師范大學(xué)音樂學(xué)院音樂教育系教師,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dǎo)師,博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音樂與舞蹈學(xué)—音樂表演理論。
([意]布索尼,著;王曉娜,譯)
基金項目:黑龍江省藝術(shù)科學(xué)規(guī)劃重點項目 “布索尼鋼琴作品及音樂觀念研究”在研(項目編號:2017A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