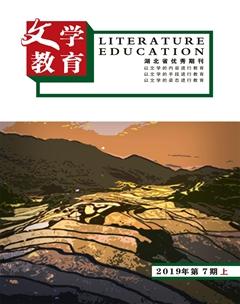改革開放四十年與深圳文學(xué)的再生產(chǎn)
黃海靜
內(nèi)容摘要:本文從新馬克思主義的視角研究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深圳文學(xué),發(fā)現(xiàn)“文學(xué)深圳”的身份認(rèn)同感是未來深圳城市空間生產(chǎn)的主體性期待,深圳文學(xué)文本空間的形象嬗變體現(xiàn)出城市空間塑造的隱秩序向同質(zhì)化的轉(zhuǎn)向。深圳文學(xué)生產(chǎn)無論外部環(huán)境還是內(nèi)部運(yùn)動(dòng)規(guī)律,均體現(xiàn)出文化追隨空間流動(dòng),在時(shí)空壓縮中被創(chuàng)新、變化和替換的特點(diǎn)。深圳正處于城市化高速發(fā)展的迅猛階段,城市的空間擴(kuò)張更新與文學(xué)的空前發(fā)展構(gòu)成一種復(fù)雜互動(dòng)的辯證關(guān)系。
關(guān)鍵詞:新馬克思主義 深圳文學(xué) 空間生產(chǎn)
? 一.引言
深圳,是改革開放建立的第一個(gè)經(jīng)濟(jì)特區(qū),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城市,被譽(yù)為“創(chuàng)客之城”、“設(shè)計(jì)之都”和“志愿之城”。彈指四十年間,深圳作為中國南方大地一夜崛起的傳奇城市,激蕩著不計(jì)其數(shù)的象征這座城市名片的文學(xué)作品:有底層打工,述說都市生存;有校園青春,書寫白衣飛揚(yáng);還有“深圳速度”,宣揚(yáng)敢為天下先的創(chuàng)新深圳。城市與文學(xué),究竟存在一種怎樣的關(guān)系?從馬克思主義到新馬克思主義,以亨利·列斐伏爾、戴維·哈維、愛德華·W·索亞和曼紐爾·卡斯特爾等為主要代表的新馬克主義將空間意識和空間秩序植入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構(gòu)成了新馬克思主義[1]的空間批判理論,使得空間理論涉及社會學(xué)、經(jīng)濟(jì)學(xué)、政治學(xué)、哲學(xué)和文學(xué)等諸多領(lǐng)域,掀起了一股空間轉(zhuǎn)向之風(fēng)。文學(xué)創(chuàng)作離不開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和社會的巨大場域,城市的空間生產(chǎn)也必然會根深蒂固于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土壤之上。
? 二.新馬克思主義的空間生產(chǎn)理論
20世紀(jì)6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國家出現(xiàn)普遍的城市危機(jī),伴隨著全球化時(shí)代的到來,工業(yè)化、城市化以及資本積累動(dòng)態(tài)的變遷,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及其統(tǒng)治不僅在空間普遍化了,而且使空間本身成為資本積累及其統(tǒng)治的手段[2]。在這一背景下,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紛紛試圖從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汲取精華,尋求解決城市問題的答案。他們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與城市空間分析結(jié)合起來,誕生了以戴維·哈維、亨利·列斐伏爾、愛德華·索亞、曼紐·卡斯特等為代表的新馬克思主義的“空間生產(chǎn)”理論。[3]
列斐伏爾首先意識到空間問題對資本主義發(fā)展的重要性,他巧妙地將視角轉(zhuǎn)移到空間生產(chǎn)本身,將空間看作是社會巨大的資源——生產(chǎn)力和生產(chǎn)資料,和其他生產(chǎn)過程一樣,“空間是社會的產(chǎn)物”。“城市”作為一種空間形式,實(shí)質(zhì)也是資本生產(chǎn)下的產(chǎn)物。在此基礎(chǔ)上,列斐伏爾將空間的社會、精神和物質(zhì)三者結(jié)合起來,建立了社會性、歷史性和空間性的“三元辯證法”[4]作用于城市空間與資本主義的生產(chǎn),初步實(shí)現(xiàn)空間轉(zhuǎn)向來進(jìn)一步闡釋后現(xiàn)代城市的本質(zhì)。
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chǎn)理論給后來的哈維、卡斯特和索亞帶來了巨大的啟示和深遠(yuǎn)的影響。哈維從生產(chǎn)的角度將地理學(xué)知識融入空間生產(chǎn)理論,認(rèn)為資本(資本積累和資本循環(huán))在城市的興衰中起到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具體而言,他的空間生產(chǎn)理論緊密圍繞城市化過程。一方面,時(shí)空格局直接影響并主導(dǎo)城市化進(jìn)程;另一方面,城市化進(jìn)程也反作用于城市時(shí)空的改造。在此基礎(chǔ)上,他給出“城市化是資本積累的重要形式和資本主義再生產(chǎn)的重要條件”的重大結(jié)論和“資本的三種循環(huán)說”。
如果說哈維是從生產(chǎn)角度來研究當(dāng)代城市社會,那么卡斯特則從消費(fèi)領(lǐng)域出發(fā)研究空間問題。卡斯特的城市空間理論深受阿爾都塞的結(jié)構(gòu)理論影響。他認(rèn)為,城市不能脫離整個(gè)社會系統(tǒng),城市作為整體系統(tǒng)的一個(gè)子系統(tǒng),在整體中發(fā)揮著巨大的消費(fèi)功能,而這種集體消費(fèi)也逐漸成為主導(dǎo)城市化進(jìn)程的核心力量。
緊接著,索亞在前人的基礎(chǔ)上提出“第三空間”的概念。“第三空間”并不是一個(gè)具體存在的真實(shí)空間,而是通過意識和思維的加工想象,重新建構(gòu)多重文化沖突下的身份、城市空間和都市文化景觀。索亞極力反對空間生產(chǎn)理論中的“二元空間論”:非此即彼的絕對性,以移民文化在空間中的體現(xiàn),揭示“第三空間”中不停轉(zhuǎn)換和改變的觀念、事件、現(xiàn)象和意義的社會環(huán)境。[5]
新馬克思主義并不是與馬克思主義思想斷裂開來的一種新觀點(diǎn),而是對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繼承和深化。戴維就曾指出:“馬恩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英國工人階級狀況》、《論住宅問題》、《1857-1858年經(jīng)濟(jì)學(xué)手稿》以及《資本論》中將‘城市空間納入到歷史唯物主義的整體視野中,‘城市空間由此具有了社會歷史性,并成為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主義進(jìn)行批判的一個(gè)重要視角”。[6]此外,空間生產(chǎn)理論已走進(jìn)地理學(xué)、文學(xué)、社會學(xué)、哲學(xué)、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等學(xué)科領(lǐng)域的學(xué)術(shù)視野,尤其是近年來空間生產(chǎn)理論延伸至后現(xiàn)代社會的文化批判,在文學(xué)、文化學(xué)領(lǐng)域掀起了一股“空間轉(zhuǎn)向”研究的熱潮,也逐漸形成跨學(xué)科、跨文化的綜合發(fā)展態(tài)勢。
? 三.全球化下的深圳文學(xué)建構(gòu)
在全球化資本積累高度集中和巨大擴(kuò)張的背景下,一方面,深圳文學(xué)在城市空間創(chuàng)造中渴望尋求一種象征身份的“共同體”;另一方面,深圳文學(xué)本體性在歷史長河中的形象嬗變,使得文學(xué)植入空間成為空間擴(kuò)張的強(qiáng)大動(dòng)力。
1.身份認(rèn)同:“文學(xué)深圳”的期待
深圳文學(xué)紛繁蕪雜,在短暫的歷史交匯中,似乎很難定義“文學(xué)深圳”。有人說,這是因?yàn)樯钲谕鈦眈g雜,在各種異質(zhì)文化沖突中很難找尋同一性和認(rèn)同感。英國學(xué)者斯圖爾特·霍爾認(rèn)為,“認(rèn)同感”是在話語實(shí)踐的動(dòng)態(tài)發(fā)展過程中形成的,因此“文化身份”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在社會環(huán)境中由文化塑造和建構(gòu)得來。班納迪克·安德森提出的“想象的共同體”,他認(rèn)為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認(rèn)同感”依賴于“想象共同體”的催生,小說報(bào)紙等印刷媒介與“共同體”休戚與共,并在之形成過程中起到重要功用。[7]“文學(xué)深圳”的身份含混曖昧,它不像穆時(shí)英、劉吶鷗、張愛玲和王安憶筆下頗具西方摩登現(xiàn)代性的“文學(xué)上海”,也不似老舍、茅盾筆下頗有京城翹楚得天獨(dú)厚的“文學(xué)北京”,這些地域文學(xué)都有自己鮮明的文化身份和深刻烙印。因此,才有了吳予敏《渴望“文學(xué)深圳”的誕生》[8]和趙改燕《“文學(xué)深圳”的呼喚——深圳文學(xué)參與城市文化身份建構(gòu)的探討》[9]等深圳學(xué)者對文學(xué)深圳的冀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