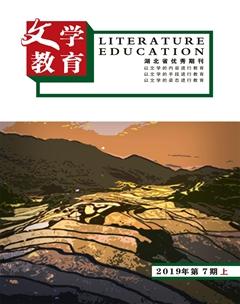作家聲音
●莫言再談《紅高粱》:依然看到年輕時的創作激情
“電影《紅高粱》已經拍了32年了,回頭再看這部電影,依然能夠感覺到當時一幫年輕人的創作激情。”莫言日前在山西舉辦的呂梁文學季上如是說。當晚,莫言現身賈樟柯發起創立的首屆呂梁文學季,并在由西安電影制片廠修復的4K版本《紅高粱》放映前夕,與觀眾互動交流。此番修復后的電影《紅高粱》,也是首次在中國內地放映。有段時間,互聯網上的一張32年前《紅高粱》拍攝花絮的照片廣為流傳,照片中的莫言、姜文、張藝謀光著膀子和鞏俐站在一起。“那是1987年我們在我的家鄉拍《紅高粱》的場景,那時候我們都還很年輕,我32歲,姜文不到30,張藝謀37歲,那時候我們也沒想過能獲得國際大獎,沒想到張藝謀成了國際大導演,鞏俐成了國際影壇上熠熠奪目的明星,姜文后來拍出了廣受歡迎的電影。”莫言說。回望32年前的那段場景,莫言說,“現在依然能感受到當初年輕人創作的激情。”“這個電影反映了上世紀80年代中期,剛剛獲得思想和藝術解放的這批年輕的創作者,要求沖破一切思想禁錮的精神。”莫言認為,很多藝術作品之所以能在一時間被眾口相傳,就是因為它契合了當時民眾內心深處的深切需求。《紅高粱》是一個歷史的產物,一個歷史的巧合。“大家看這個電影,應該用反觀歷史的心態,來了解上世紀80年代年輕一代思想深處的強烈要求,也希望給年輕觀眾以啟迪,我想這也是老電影的作用。”
●蘇童稱好電影是給原著作家的珍貴禮物
蘇童日前現身正在山西汾陽賈家莊村舉辦的首屆呂梁文學季,談及改編電影與原著作家之間的關系,蘇童坦言,“好電影是給原著作家的一份珍貴的禮物。”蘇童當日在賈樟柯藝術中心廣場作題為《我的鄉村,我的街道》的演講。他認為,故鄉是世界的縮影,是人們最初認知世界的一個輪廓,寫小說利用的就是這個輪廓,再把這個世界的縮影去放大,告訴別人自己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樣。30多年來,作家蘇童的原著小說頻頻被搬上大銀幕,改編自《妻妾成群》的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曾獲第48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銀獅獎。改編自《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的同名電影也入圍了第69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地平線單元”單元。蘇童說,“作家寫自己的東西,然后被影視化改編,我覺得都是一個禮物。對我來說,我是收到了一個珍貴的禮物,它(電影)讓我擁有了更多的讀者,更好的閱讀市場,這部電影對我是有幫助的。”蘇童認為,作家與導演的關系,實際上是食材供貨商與廚師的關系。“至于廚師做成什么菜,那就跟食材供應商沒什么關系了。”獲得第九屆茅盾文學獎的作品《黃雀記》早年傳出被影視化改編,對于影片的進度,蘇童坦言并不知曉。
●葉兆言認為作文和文學是兩回事
葉兆言日前在山西省汾陽市與學生暢談“怎么寫作文”。葉兆言認為,“作文和文學是兩回事,文學屬于創作,作文屬于最基本的一種能力,是做為有文化的人最基本的東西。”葉兆言稱自己并不贊成過多在小學里談文學,因為這樣小朋友會覺得寫作與作家有關。“但為什么我們要教作文課,強調的還是寫作能力,想什么寫什么其實很難,從想到寫還是有一段距離。有困惑非常正常,作文課就是解決這些問題的,對于同學們來說,要像鍛煉身體一樣提高寫作能力。第一,我希望大家快樂地去寫作文,第二,讀一些好的范文。”葉兆言坦言:“大多數時候我是不喜歡寫作文的,但我在想,能不能提供給同學們一個讓他們喜歡寫作文的理由,能不能向老師、同學、家長提供一個體會你小小的聰明和壞的一個機會。寫作文寫一個很好玩的故事就行了,不用最后一句都寫‘這是有意義的一天。”
●笛安稱和筆下的人物“像室友一樣”相處
匈牙利作家佐娜·烏格龍日前與中國作家笛安共聚北京老書蟲書店,與讀者分享如何塑造小說中引人入勝的角色。在羅馬尼亞出生的匈牙利作家佐娜·烏格龍專注于歷史題材小說,描繪十五十六世紀的歐洲畫卷。對于需要書寫真實歷史人物的佐娜來說,研究是第一步:搜集資料、確認真偽。佐娜常常去那些或保存完好或已經毀掉的遺跡,感受遺跡,再寫進書里。有時候,比起寫作,佐娜發現自己甚至更喜歡研究的過程。寫虛構小說的笛安則看重“和小說人物相處的過程”。笛安一直相信,她筆下的人物真實存在于世界上,“不知道為什么,但就是相信他們存在”;在每篇小說的初始階段,她和筆下的人物“像室友一樣”相處、磨合,觀察人物,了解人物身上隱藏的特點,這個過程大概占據整本小說的前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了解到主角的弱點之后,笛安對整個小說就有了把握。但與人物相處的經驗似乎不適合短篇小說。笛安常常覺得,短篇小說似乎“還沒開始就已經要結束了”,寫完了,她也不太了解人物。因此她自認不擅長寫短篇小說。笛安2012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嫵媚航班》里,她認為只有講一個一百多歲的老頭一直在等死的《胡不歸》這一篇算得上“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