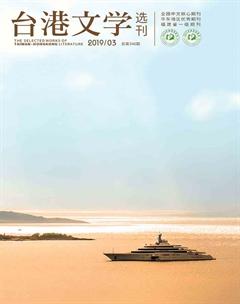表 達
徐東
表 達
我看到一個人在下雨的夜里游泳,那雨落在游泳池中,燈光清晰地照見了雨落下來時微斜的痕跡。那人自顧自地游著,我卻感到那是另一個我在游。
小時候我曾在落雨的天氣里游泳,在一條寬大的河里。后來我再次回到家鄉,看到那條河時,河已不像小時候感覺到的那樣寬大了。我看到在河中游泳的孩子,也許他們仍會像我小時候那樣感到那條河是寬大的。看著他們,我像看到了自己小的時候。
時光流逝了,記憶卻停留在過去的時空中,不時被喚醒。那被喚醒的,是什么呢?當一個人活過,消失后,那消失了的又是什么呢?我們活在當下,也活在記憶與感受中——我想,那記憶與感受便是精神的綠地了吧。
傾 聽
他說,你聽!
于是我停下匆匆腳步,聽林中的鳥鳴。
我們愿意停留在某一處,感受那些不會發出聲音的事物,它們存在的聲音。它們也會發出聲音,只是我們沒有聽見。
許多無聲無息地活著的人也并非沒有發出聲音,只是我們沒有聽見,沒有留意,沒有與他們交談。
靜下來的心使人間的喧嘩變得有了些純粹。
靜下來的你會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聽見一條小溪的淙淙流淌。
傾聽,使人漸見自我。
我是誰?我是輕風,是微塵,是花開花落,是白云悠悠。
我是東方的日出遙望著高樓林立,車水馬龍。
我是我,也是你。

不惟是相互愛戀的人才形同一個人,陌生人的一個眼神也會讓你生出似曾相識之感。而我們不強化那感受,因我們面臨著更多的人生的內容與風景。
我們總想著,要向前去。
我們走出人群,去爬山。
我們望著一棵樹,金黃色的陽光從樹葉的空隙穿過來,似乎“嘩”的一聲,落在了我的心里。
我說,你聽,鳥鳴不遠不近。
他說,讓近的再近些,遠的再遠一些?
失 蹤
看到穿得又破又臟的流浪漢,我想象自己有一天無法自控地失蹤了,離開了熟悉的城市,熟悉的生活,熟悉的朋友,放下了一切走向遠方。我在眾人的遠方,在山川草木間,在陌生的地方,在風雨中,在日月輪回中,不斷向前走去……
有時我渴望那樣真正的孤獨與決絕。可當我想起深愛的人,深愛我的人,他們有可能會走遍千山萬水,用盡一切辦法去尋找我,便冷靜下來,繼續現在的生活,日復一日。我感受自己存在的一切可能,卻漸漸活成為別人的樣子,并如一股小風撲向時代。我無法穿越,惟有活著既定的命運一般的自己,活在當下。
每個人都是龐大整體的部分,在整體之中很多人漸漸失蹤,原因在于他們為了總是撲面而來的現實,為了獲得物質的滿足,漸漸放棄了對自我的追問,已然不知身在何處。
窗 外
窗外有持續不斷的喧囂聲,是人們制造出的各種聲音交合在一處。
窗外有綠樹在微風中搖晃著枝葉,鳥兒們在遠處,在公園里的一角,在野外的樹林子里。我想去看看它們,聽聽它們在唱著什么歌。
窗外的風景朝著四面八方延伸,形成一個被情緒與思想籠罩的抽象的世界。
窗外的一切也在我的內部,使我想要停止呼吸,感受到時代的心跳。時常我聽不到什么,外部的噪音太大。
窗外突然有人大喊了一聲。
——我擔心有誰從高處跳了下來。
——我擔心跳下來的那個人是自己。
喊 山
在房中坐久了,去爬爬山很有必要。
沉默得太久了,去山中喊幾聲很有必要。
我聽見別人在喊,想走過去看看,和那個人聊上一會。
我只想和那個人聊上一會,并不期待和他成為朋友。我甚至想看看那個人是不是另一個我。通常,我只是那么想一想。
有時我見著那個喊山的,會對他笑一笑。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已經替我喊過了。如果我再喊一聲的話,就是重復。不過,我想喊的時候還是喊了。
山有回聲,我聽見了,感到聲音穿過時空時遇到了諸神的耳朵。
我需要愛,愛無處不在——只不過我沒有讓人聽見我的心聲。
看 天
我曾是那個躺在山坡上看天的人。
那時我十八歲,十九歲,二十歲。那三年我經常躺在山坡上看西藏藍藍的天空,天空上潔白的,一團一團的云彩。
多年后我回憶起那樣的時刻。
我生命中的西藏:太陽很亮,照著群山,天空很藍,云淡風輕。
當我再次抬頭看天時,我已經看不到那時的天空。
放 松
閱讀使人放松,聽音樂使人放松,和好朋友聊天使人放松,暫時放下手頭的工作去別處走走看看使人放松。
喜歡唱歌的人唱上一首歌是放松,喜歡運動的出出汗是種放松。
我喜歡喝點紅酒,紅酒也使我放松。
有時我深呼一口氣,輕輕呼出來也是一種放松。
寫作的時候使我全神貫注,寫作意味著表達,表達也是一種放松。
娛樂活動的必要性就在于可以使人放松,放松使人的內心漸生喜悅之情。
想事想得太多使人沉重,因此不想事兒也是一種放松。
看到神情放松的人我會覺得順眼、舒服,仿佛他在代替我輕輕松松地在活著,活得自由自在。
不要總是低頭走路,有時也要抬起頭來看天空。
藍天白云讓我放松。
接 近
有時我會想起那些離我很遠,甚至與我無關的石頭、樹林、河流、村莊,卻想不起一個可以想起的人——在那樣的時候,是孤獨的。
孤獨的時候不忍心睡去,就像那樣睡去是在消失,無法醒來。
我是留戀這人世的,我想要通過一生去愛更多的事物,去創造些什么,去證明我的存在。有時我又對生又有著莫明的厭煩,因為我會感到生命的時空被層層劃分、隔開,我成了面包店陳列的點心,一塊一塊的被莫名的嘴巴吃掉,而不再有我。
渴望愛,渴望付出,渴望獲得,而愛仿佛總在別處。如何否定精神的虛無,緊緊握住早已握住的現實?我渴望的一切有何意義?
一切都是陌生的,終會陌生。
有時,我并不需要任何人的理解——因為有時我并不想理解任何一個人——仿佛誰都那么無辜,在被動地生活著。
有時我看到自己在不遠處張望著我,像是從更遠處走來,卻無法再靠近。
我試圖用寫作去接近千千萬萬個我,接近他們——我愿意向遠處的我靠近,我與我相互對視,彼此憐憫,彼此原諒,彼此相愛,卻又相互輕聲責備,顯得親切而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