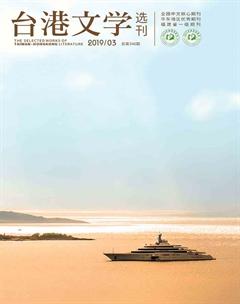父形
雷驤

有許多次,當我在陌生的旅邸,面對盥洗間鏡臺的時候,不期然從映出的我的影像上,重疊出一個衰竭的頭顏,光頭和上髭頭須,一切都是銀白色的——那即是我父親殘年時的頭像。雖則我與父親在外貌上并不形似(毋寧更像母親罷),但那頭顏,常常在我獨自一人的時刻浮現起來,仿佛隱藏在我體內的另一種面貌,倘若不加壓抑,它就悄然地替代了我刻下的面容一般。
人們回索過往,常會追想到上一輩去,因為生命體是連續的呢。具體說:父親、祖父的生物生命,不正在我身體內延續著嗎?個我確定是家族生命的一支。那幻象的浮現,也許就是這種溯往情緒的具象化。
父親頭顏所意含的獨裁與固執,只是表象如此,實際上父親晚年十分仁慈,常處于脆弱與不安之中。為什么選擇那樣沖突的發須形式,的確讓人不解。
“學你的樣呀……”父親撫了撫唇上的短髭,向我笑著說。同時,我也發現他理去了頂上的頭發。從那時到辭世,變成這副不相稱的形貌固定下來。
如果周遭足夠安靜,不致影響老人的專注的話,我總促請他回述過往。老人尋思著,每每顯出對自己的一生,猶有許多困惑的樣子。我感覺那困惑,來自現刻的清明之故,所以難以理解彼時他自己的舉措。每在此時,他便不時找些事由來寬慰自己了。
我特別記得那一天,坐在我家庭園的那次。父親包裹在松厚衣物下的身軀,仍在看不見地顫抖著。和煦的冬日陽光,也徒使父親的面肌益形蒼白。
那次他向我陳述了家鄉淹水的夢。
據知,那個我從不曾踏臨的故鄉,因為傍河的關系,水患總不可免,是父親在年少的時候印象極深的。水漲起來淹沒自家的院墻和田園,毗鄰的縣衙中,有囚人們的喊叫,一片汪洋,極其渾濁,糞便浮游在水面上。但在父親的那個夢中,那大水清澈無比,像翠綠的湖面一樣,而他自己竟毫無阻難地在水域上恣意行走,到處觀看和拜訪著。
“那是什么意思呢?大水出奇的透明干凈……嗯?”老人撫摸已經剃光的頭殼,反復向我詢問。
自年輕時代負笈都會,且從此與故鄉切斷臍帶的父親,差不多從不對子女提及故鄉的事。因此這種種景象的描寫,無論真實或夢境,對我皆都奇幻。記憶之于他,如同層層疊疊陳年掩蓋的落葉,忽然被揭露,直到那最底層——原以為腐爛無形的枯葉,竟回復那清麗明晰的葉形,分明地呈現在早經埋葬的位層。以是,我忽然感到父親實際已預見他的死亡了。
九歲的某日,我從尾部甲板上看到,輪船終于搖晃著駛進像盛滿一盆水的基隆港,神志才清明起來。前此,在越過海峽時候的翻騰,忽被拋擲腦后,迎面是像圖畫里那樣美的山巒,綠色的呈波弧的樹叢。輪艙上倏忽嘈雜起來,原來他們把錨落在海底,船身也就此止住了。說是要泊在港里候辦檢疫等等事務,恐怕要耽誤兩個時辰呢……就在這時候,我從高高的船舷看到一個小木船上,穿著夏衫白色短褲長線襪,而頭上戴著像狩獵家的那種圓盤帽的男人,向我激動地揮舞雙手。那就是雇了小船劃到港里來歡迎我們的父親呀,我看到小舟的尖頭里,還裝載滾圓的幾顆西瓜,好像帶給我們一家人飄洋過海以后,隨即有一種旅游的心情。
接下來在臺北的幾天之后,父親委托年輕人馬君,帶著我們兄弟三人坐火車南下——已安排好一處日式的宅院。嗜吃的我們,一路都坐在鋪著白桌巾的餐車上,一面望向窗外引人的風景;一面不斷向侍者點著餐食,直到目的地。——后來,我卻看到馬君向父親報賬時的愧怍表情,因為他自始至終都沒有約束我們的緣故吧。不過那也是我們享用豪奢的尾聲了,此后,因為投資回償的斷絕,以及父親未作任何保值的計劃。一年后,生活即陷入苦境。
日后,兄弟間總有機會檢示雙親理財方面的諸種不當。但據我所見,那已是上輩人的習常,殊無改變的可能。兄弟之一,因為前車之鑒而戮力置產,積累財富。而我的日后行事,竟循了父親的法則。
那個狩獵家打扮的精力充沛的父親,仿佛不久前的印象呢,轉眼看,已經老邁,呆坐起居間沉默著了。他似乎對衰竭突然攫住了自己也難以置信。
“于是有一天,跌坐在馬路上了……”父親說:“在下午的大太陽底下,我心里還想:這樣脫了力,從此就爬不起來了嗎?這不可能是真的。屁股底下的柏油路面,柔軟燙人,我該勉力站起來,但是被吸住了似的,一點也不能動彈,而午后路上靜悄悄的,一個路過伸援的人也沒有……”
父親終而無可挽回地衰老了,八十年來的困乏,使他隨時可以入眠。實際上是進入另一種精神活動——回憶或想象的綜合世界。在夢中,他足登年輕時夏天喜愛穿的白皮鞋,匆促上下辦公室樓梯,一點兒不費力氣。我完全可以想象他情狀愉悅的模樣。事實上,那時他已經甚難走動,必須依賴輪椅、四腳手杖以及傭人的扶持,才能緩慢移步,膝蓋以下的骨節銹蝕麻木了。去世前的若干年,幾乎就只茫然坐著,或竟小睡過去,發出無忌憚的鼾聲。有一回他的長孫女,悄悄用微音器輯錄下來,SAMPLE進她的合成樂器,當祖父醒來的時候,即用那鼾聲彈奏一曲給他聽。 父親半信半疑地微笑,人們告訴他這個科學發明的事實,他微笑對待——反正目下這個已經是自己不能也不想追趕的世界啦。
(選自臺灣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爾雅散文選·第一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