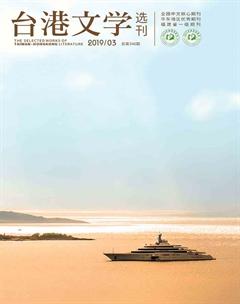淡淡春暉
“一、二、三、四、五、六、七。”每次帶我們出門,母親總要數(shù)上好幾遍。“好奇怪呀!為什么老是數(shù)來數(shù)去,我們又不是牛。”妹妹說。她剛上過《怎么少了一頭牛》那一課。
如果問母親,她一定會說上一大串:“你們要知道,你們一共有七個,七個哦!只要眼睛那么一閃,很可能就丟掉一個。像上次搭火車到高雄,我把你們一個個拉上車,最后發(fā)現(xiàn)老四不見了,這可怎么辦?找來找去,才看到她上了另一輛車,正在對我招手呢!還有一次,睡覺前點來點去,就是少了老大,天啊!那已經(jīng)是深夜了,我跑到街上找、戲院找、夜市找,一邊喊一邊哭,回到家,天都快亮了,正急得不知怎么辦?忽然靈機一動,彎腰到床邊的梳妝臺下一看,果然,她睡著睡著滾到里面去了,呵!嚇死我了。”
母親常說她好像在對付“一軍營的兵”。不要看我們一個個長得斯文秀氣,站出去好像很害羞很有禮貌,在家里可是兇悍無比,雖說是女孩子可也好打架,而且專喜歡用腳互踢,踢得我們一個個都是蘿卜腿,不但如此,我們偏好打群架,一個推一個,然后扭成一團。母親說我們簡直是一團橄欖球隊員。
孩子打架的主要原因是“分配不均”。誰多了一個玩具,少了一塊糖,就會吵得天翻地覆。為此,母親很早就立下一個規(guī)則:買東西一定同樣的買七份,做衣服一定是同一塊布料,同一個樣式,誰也別想多個蝴蝶結(jié),少個扣子。結(jié)果我們在家也得穿制服,誰也別想占誰的便宜。
我有一張小時候的照片,一排小女生,一式的花洋裝,每個人頭上都有一個別針,我那時才上幼稚園,可也知道為自己爭,我的別針是小黑人掛著一副大耳環(huán)。記得母親為了讓我們每人都有一個別針,幾乎找遍了鎮(zhèn)上所有的百貨行。
吃飯也是麻煩時間,尤其是大家庭里,大鍋飯大鍋菜,菜老是不夠吃,母親每每在吃飯前先把菜分配好,肉切成幾塊,菜分成幾份,每個人吃多少,皆嚴格執(zhí)行,使得我們有口也難辯。她從不要我們誰讓誰,因為根本做不到,她只是公正嚴明,讓我們找不到漏洞。
也許是小時候爭多了吵煩了,不好意思,我們現(xiàn)在特別禮讓,每有好東西,一定推來推去,彼此互相取笑:“好虛偽哦!”
那時,家里做生意,老房子狹而長,爸媽在店里忙,中間隔著天井,叫人老叫不到。媽媽于是發(fā)明一種叫人的方法:她在店里安裝一個電鈴, 并列出一張表,每個人都有一個固定的訊號,譬如大姐是“三長兩短”,我的“兩短三長”,小妹的“三長”,如此,只要鈴聲大作,被點到名的趕忙奔赴,母親之講求紀律可見一斑。
為了訓(xùn)練我們整潔的習慣,從上小學之后每個人都分配工作,星期日全家上下總動員,由父親擔任清潔隊長,帶我們打掃庭園。我們常常一面唱歌一面工作,不但發(fā)現(xiàn)勞動的樂趣,而且發(fā)現(xiàn)各自的長處。譬如大姐對插花最有一套,她才十來歲便喜歡種花買花,插花也能自創(chuàng)一流,可以稱之為“意識亂流”;三妹最有設(shè)計的美感,舉凡挑選布料家具,裁剪窗簾,她都能一手包辦,家里的陳設(shè)經(jīng)過她的布置總是特別漂亮;至于我,因為常唱歌也練成一副不好不壞的歌喉。我們常自比為《小婦人》中的四姐妹,老大“梅格”漂亮賢慧,老二“喬”最有性格,老三最愛美,老四多才多藝又最善良。
在母親嚴明的紀律下,我們享有公平的待遇,可也常感到被疏忽被冷落,尤其在少年時代,種種的苦悶與寂寞,常歸咎于母親。后來年歲漸長,才了解要公平且仁慈地對待別人,是一件困難的事。我們?nèi)菀灼珢勰鐞蹫E愛,感情更需要嚴明的尺度,否則容易迷失自我。更何況我們只有一個母親,當然會把一百分的期望放在她身上;而母親卻有七個子女,她只能平分她的愛,縱使我得到的愛只有七分之一,也遠比我給母親的愛多得太多。
四妹與我同時結(jié)婚,母親硬是辦兩份同等的嫁妝,不管是一針一線,一雙鞋一條項鏈,總要做到公平,還頻頻問我們:“這樣可以嗎?還喜歡嗎?”我們真的已經(jīng)不在乎不計較了,我們已經(jīng)長得好大好大,可是,她還是堅持著。
日復(fù)一日,她的容顏變老,原則卻越來越少,她似乎很少再堅持些什么,就連生氣也喜歡保持沉默,尤其是當她抱著孫子時,面團團,發(fā)蒼蒼,笑嘻嘻,簡直就是一個沒有脾氣的老祖母。現(xiàn)在,我們七個孩子,分散在各地,她可是一頭牛也不用找,更找不到。有時候打電話回家,她老是摸不著頭腦地問:“你是芬伶還是芬青呀?怎么聲音聽起來都一樣。”
我想她是老了,老得分不清我們的聲音,可是,她的兒女可記得,她公正又仁慈地愛著她們,讓她們健康地成長。她們?nèi)绻麤]有變得自私,那是因她曾要求她們寬大;她們?nèi)绻麤]有變得怠惰,那是因為她曾要求她們勤奮。她們也會永遠記得,母親出門時,張皇地找尋自己的孩子,心里老是默數(shù):“一、二、三、四、五、六、七。”不管年去歲來,這幅影像永遠不會淡去。
母親有一雙嬰兒般的手掌,皮肉柔細肥軟,手指頭又粗又短,五指合攏時,掌心便凹進一個洼,母親說那是“金窟”,這種手是會裝錢的,一輩子吃用不盡。
可是,這樣的手還沒摸過多少錢,母親便吃過許多苦。小時候家境雖不錯,她的母親卻被父親趕走,接著繼母進門,把所有的家事全部推到年紀過小的母親身上,她的手被炊飯的煙熏過,被養(yǎng)豬的餿水泡過,被刮傷,被鞭打,卻依然細白柔嫩,像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蓮。
她生過七個孩子,又要經(jīng)營一家藥店,大家庭里有數(shù)不清的家務(wù),她的手洗過尿布,數(shù)過鈔票,搬過貨物,卻依然細白柔嫩。只是中年以后發(fā)胖,手背上多了好幾個肉洼,更像胖娃娃的手了。
她喜歡各式各樣的戒指,戴上戒指的手更顯得華貴,就像是貴婦人的手。生活的磨難并沒有在這雙手上留下痕跡,只留下甜美。
在記憶中,我們并不常牽手,就算現(xiàn)在我們親昵如朋友,出門時我也只喜歡挽著她的手臂。以前我常想,也許母親不喜歡拉我的手。后來,我做了母親,才了解什么是“生我鞠我,長我育我,顧我復(fù)我,出入腹我”,這種緊密的相依之情,誰又沒有過呢?
從小我便為自己的手感到自卑。我的手雖最像母親,可是皮膚較黃,指甲又被啃得支離破碎。就掌形來說,它看起來粗魯拙稚;就掌相來說,它代表著懶惰與意志薄弱。我也有個“金窟”,只是比較平淺,淺得一個銅板便能將它填滿,它可從未帶來任何財運,卻將我的弱點暴露無遺。多么盼望有一雙纖細修長屬于藝術(shù)家的手掌,因為如此,我總是小心翼翼地不讓人看到我那令人傷心的手掌。
曾有幾次我與母親核對彼此的手掌,多奇妙!它們的形狀大小幾乎完全一致,只是我的比較枯黃粗糙而已。我遺傳了父親的長相,卻遺傳了母親的手。我們有著相似的手掌,卻有著全然不同的命運;我們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但是我們的心是如此靠近。
如今,我的孩子也有一雙與我相似的手掌。我很喜歡用自己的手包住他小小的手掌,奇怪的,他并不掙脫,他也喜歡讓我握著。他的掌心也有個迷你“金窟”,剛好可以裝下一顆健素糖。
也許有一天,我的手再也包不住他的手,他必定會找到一些情緣的線索,在我們相似的手掌里;他也許也會忘掉我怎么生他鞠他,長他育他,顧他復(fù)他,出入腹他,但他必定會再找回一些愛的記憶,也許是在他孩子的掌心里。
從此,我的手便有一種嶄新且神圣的意義。我還是那么羞于展示自己的手,也羞于去握母親的手,可是,有許許多多生命的奧秘在指間,在手心里。
(選自臺灣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新世紀散文家:周芬伶精選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