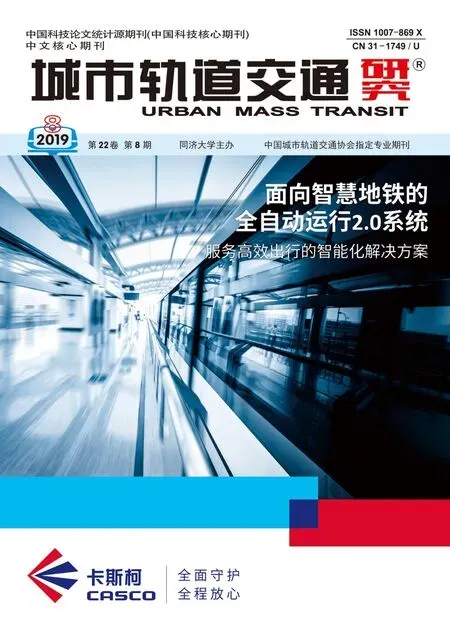超長地鐵聯絡通道水平凍結溫度場變化規律分析*
崔 灝
(北京中煤礦山工程有限公司,100013,北京//高級工程師)
聯絡通道是地鐵隧道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安全疏散和排水功能,一般位于各區間隧道的中部,其斷面多為矩形、圓形或直墻拱形。聯絡通道的施工是地鐵建設的關鍵。當聯絡通道處于軟弱、破碎、富含水地層或斷層破碎帶時,可采用MJS(全方位高壓噴射)法、管棚法、人工凍結法對通道周圍土體進行預加固后再開挖。其中,凍結法由于具有安全可靠、適用面廣、污染性小等優勢,已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地鐵工程中得到了廣泛運用[1-2]。文獻[3]以北京中細砂層地鐵聯絡通道凍結工程為背景,基于理論分析,得出該地層條件下凍結壁厚度計算公式;文獻[4]基于上海雙層越江隧道的實測數據,得出管片散熱是影響凍結壁形成的重要因素;文獻[5]以蘇州地鐵2號線某軟弱地層聯絡通道凍結工程為背景,基于實測數據,得出凍結壁形成及解凍的基本規律。綜上所述,目前常規聯絡通道凍結設計與施工已較為成熟,但對于復雜地層條件下的超長、超埋深聯絡通道凍結溫度場變化規律還缺乏研究,而凍結溫度場的預測分析可提前判斷凍結壁發展狀況,因此必須掌握超長聯絡通道凍結溫度場的變化規律。
本文以福州地鐵2號線某區間超長聯絡通道凍結工程為背景,對凍結方案進行分析,并結合數值分析數據和實測數據對凍結溫度場的發展與分布規律進行研究,重點分析了初始地溫、導熱系數、比熱容對該溫度場的影響規律。研究結果可為今后類似工程設計提供參考。
1 工程概況
1.1 地質條件
福州地鐵2號線上洋—鼓山1#聯絡通道及泵房位于右線里程YDK35+898.179(左線里程ZDK35+939.022),主要穿越地層分布情況自上而下為:雜填土<1-2>、淤泥<2-4-1>、黏土<3-1>、淤泥質土夾薄層砂<3-5>、(泥質)中砂<3-3>、黏土<3-1>、強風化花崗巖<7-1>。聯絡通道主要位于淤泥質土夾薄層砂、(泥質)中砂層中,地下水豐富。聯絡通道頂部埋深20 m,左、右線地鐵隧道中心線間距42.68 m,聯絡通道凈長36.48 m。
1.2 工程特點
1) 周邊環境復雜。聯絡通道左線位置上方有多棟建筑物,右線位置為福州西三環輔道邊部,通行車輛較多,且右線上方上有一條DN800的雨水管線,埋深約2.5 m;因此在施工過程中對變形控制要求高,若產生較大變形,將會引起房屋傾斜開裂、道路破壞或地下管線破損,造成嚴重的負面社會影響。
2) 地質條件差。聯絡通道主要處于淤泥質夾薄砂層、泥質中砂層中,埋深大。淤泥質夾薄砂層屬于高壓縮性土層,泥質中砂層承壓水頭較高,水量較大,開挖時易出現坑底突涌。
3) 通道過長,凍結體量大。常規聯絡通道中心距一般為11~13 m,而此聯絡通道中心距達42.68 m。采用單側隧道打孔時,凍結管偏斜較難控制,跟管鉆進難。該聯絡通道凍結體量是常規聯絡通道的3倍,在施工過程中需要嚴格控制凍脹對地層的擾動。
2 聯絡通道凍結加固方案
2.1 凍結加固方案
根據地層資料及聯絡通道特點,聯絡通道施工擬采用“隧道內水平凍結加固土體,隧道內暗挖構筑”的全隧道內施工方案。由于聯絡通道中心距長達42.68 m,因此采用左、右線兩端打孔,共布置178個φ89×8 mm(φ108×8 mm)無縫鋼管作為凍結管,其中,左線90個,右線88個,如圖1所示。聯絡通道正常段凍結壁厚度不小于2.1 m,喇叭口處凍結壁厚度不小于1.8 m,積極凍結期45 d,積極凍結期內鹽水溫度維持在-27~30 ℃,采取低溫快速凍結的方式,以減小凍脹。凍結壁平均溫度不低于-10 ℃。

a) 左線隧道
2.2 測溫孔布置
為準確掌握凍結溫度場的變化情況,共布置24個測溫孔,如圖1所示。其中,左線隧道布置13個(C1—C13)測溫孔,右線隧道布置11個(J1—J11)測溫孔。C3、C4測溫孔較短,入土深度為2 m,采用φ45×5 mm無縫鋼管,其余測溫孔采用φ108×8 mm無縫鋼管;每個測溫孔布設3~4個測溫點,分別位于入土0.5 m、5.0 m、12.0 m、19.0 m深度處。
3 凍結溫度場數值分析
3.1 凍結溫度場數學模型
地鐵聯絡通道凍結溫度場是含相變、內熱源、邊界條件復雜且與空間和時間相關的瞬態導熱問題,結合多孔介質傳熱學和凍土學理論可知,三維凍結溫度場的控制微分方程可表示為:
(1)
式中:
Cep——等效體積熱容;
T——土體溫度;
τ——時間;
λep——等效導熱系數;
q——相變潛熱;
Qm——熱源匯。
式1的初始條件為:
T|τ=0=T0;T|(xp,yp,zp)=Ty;
T|(x=∞,or y=∞,or z=∞)=T0
(2)
式中:
T0——土體的初始溫度;
xp、yp、zp——凍結管上各點的坐標數值;
Ty——鹽水溫度;
x=∞、y=∞、z=∞——距離地鐵聯絡通道凍結區無限遠處。
隧道與空氣交界面處的對流換熱邊界條件為:
(3)
式中:
Ta——隧道內空氣溫度;
n1——隧道管片的法線方向矢量;
hf——空氣與隧道管片之間的對流換熱系數。
3.2 計算模型與邊界條件
采用ANSYS軟件進行有限元分析,單元類型選取具有20節點的SOLID 90單元,假設工程所處位置計算范圍內土體材質均勻且各向同性。考慮到凍結溫度場影響區域為凍結管外側凍結壁厚度的3~5倍,計算模型縱向長度(Z軸)取值為40 m、縱向寬度(X軸)取值為80 m、高度(Y軸)取值為50 m,隧道及凍結管幾何模型如圖2所示,土體參數取值如表1所示。為提高計算精度,對凍結管布置周圍的土體進行網格加密。溫度場計算邊界條件為:土體初始溫度為20~25 ℃,因此假定初始地溫為23 ℃ ;模型上部及兩側為絕熱邊界,底部為20 ℃的恒溫邊界;凍結管壁溫度為鹽水溫度;隧道土體與空氣接觸面對流換熱系數取值為732.2 KJ/(m2·s·℃),空氣溫度取值為23 ℃,在此條件下積極凍結取值為45 d。

圖2 隧道及凍結管幾何模型截圖

體積質量/(kg/m3)導熱系數/(W/(m·K))未凍土凍土比熱容/(kJ/(m3 ·℃))未凍土凍土潛熱/(105 kJ/m3)1 8001.582.022.011.641.53
3.3 結果分析
C8、J11測溫孔0.5 m處數值模擬計算結果與實測數據對比如圖4、圖5所示。由圖4、圖5可見,數值模擬計算結果與實測數據的降溫規律基本一致,都表現為先快后慢;兩者的變化速率也基本相同。土體溫度變化速率大致可分為3個階段:第一階段,土體溫度從初始地溫降至0 ℃,各測點的溫度初期下降速度較快。以C8測溫點實測數據為例,凍結7 d時,土體溫度由初始地溫23 ℃下降到5 ℃,每天下降約2.6 ℃,這是由于凍結管與周圍土體溫差大,熱交換明顯;在這階段后期土體溫度下降速率短暫變緩,這是由于受土體相變過程潛熱影響所致。第二階段,水冰相變階段后,土體降溫速率又逐漸增快,但溫度下降速率小于第一階段。以C8測溫點實測數據為例,凍結12 d到30 d時,土體溫度由0 ℃下降到-10 ℃,每天下降約為0.55 ℃,這是由于水冰相變后,冰的導熱系數大于水的導熱系數,所以降溫速度加快;但隨著凍結時間增長,地層溫度與凍結管壁間溫差減小,地層溫度下降速度小于第一階段。第三階段,土體降溫速率基本保持不變,這是由于熱交換已達到平衡,推測凍結壁已基本形成。

圖3 C8測溫點0.5 m處模擬計算溫度與實測溫度曲線對比圖

圖4 J11測溫點0.5 m處模擬計算溫度與實測溫度曲線對比圖
數值模擬計算結果與實測數據之間存在誤差的原因是,在數值模擬計算中將土體視為均質各向同性材料,且忽略了水分遷移的影響。而在實際工程中,土體為多孔介質,為非均勻連續體,且水分遷移會影響土體物理參數指標,因此,數值模擬計算結果與實測數據有一定差異,模擬計算溫度值高于實測溫度值1~2 ℃。綜上所述,基于該數值模擬計算模型進行超長聯絡通道凍結溫度場計算時,可以較好地模擬實際工況。因此利用數值模擬計算方法分析研究凍結法施工凍結溫度場是合理可行的。
凍結45 d時地鐵超長聯絡通道凍結溫度場的擴展分布情況如圖5所示。凍結45 d時,聯絡通道正常段形成的凍結壁厚度達2.45 m,大于設計值2.10 m;喇叭口處凍結壁厚度達2.10 m,大于設計值1.80 m;凍結壁整體平均溫度達到-13.6 ℃,小于設計值-10.0 ℃,有較大富余。符合設計要求。

圖5 凍結45 d時地鐵超長聯絡通道凍結溫度場云圖截圖
4 溫度場影響因素敏感性分析
結合地鐵聯絡通道凍結溫度場方程,選取初始地溫、導熱系數和比熱容這3個因素進行單因素分析,基于所建立的三維數值計算模型,選取測溫點C8在0.5 m處的降溫曲線來分析不同因素對凍結溫度場影響的規律。
1) 初始地溫的影響。土體初始溫度分別取15 ℃、20 ℃、23 ℃(未變)、30 ℃進行計算,計算結果如圖6所示。由圖6可以看出,相同條件下,C8測溫點土體溫度降至0 ℃所需的時間與土體初始地溫呈正相關,初始地溫越高,測溫點處土體溫度降至0 ℃所需時間越長。如:初始地溫15 ℃時,C8測溫點土體溫度降至0 ℃所需時間僅為10.5 d;當初始地溫升高到30 ℃時,C8測溫點土體溫度降至0 ℃所需時間達到18 d,但土體溫度的最終降溫趨勢趨于一致。這是由于土體初始溫度越高,土體降溫所需的冷量越大,因此土體溫度降至0 ℃所需的時間越長;但當土體溫度降至0 ℃后,隨凍結時間增長,降溫趨勢趨于一致。

圖6 不同初始地溫下C8測溫點土體溫度降溫曲線
2) 導熱系數的影響。按土體導熱系數在原有基礎上分別增大10%、20%、30%進行計算,計算結果如圖7所示。由圖7可以看出,相同條件下,C8測溫點土體溫度降至0 ℃所需的時間與導熱系數呈負相關,導熱系數越大,測溫點處土體溫度降至0 ℃所需時間越短。如:導熱系數增大30%時,C8測溫點土體溫度降至0 ℃所需時間僅為11 d,該點降至0 ℃所需時間較初始導熱系數時縮短了3 d。

圖7 不同導熱系數下C8測溫點土體溫度降溫曲線
3) 比熱容的影響。按土體比熱容在原有基礎上分別增大10%、20%、30%進行計算,計算結果如圖8所示。由圖8可以看出,相同條件下,C8測溫點土體溫度降至0 ℃所需的時間與比熱容呈正相關,比熱容越大,測溫點處土體溫度降至0 ℃所需時間越長。如:比熱容增大30%時,C8測溫點土體溫度降至0 ℃所需時間為17 d,該點降至0 ℃所需時間較初始比熱容時延長了3 d。

圖8 不同比熱容下C8測溫點土體溫度降溫曲線
原始地溫主要受氣溫環境影響,以及水泥加固過程中水泥水化熱釋放出的熱量影響。導熱系數、比熱容與土體性質有關,而采用水泥加固土體后可有效增加土體導熱系數、減小比熱容[6]。因此,在遇到大體量凍結工程時,可采用水泥、MJS等技術對土體進行預加固后再進行凍結,避免兩者同時施工時因水泥水化熱量釋放而導致凍結壁交圈時間的增加。
5 結語
超長地鐵聯絡通道采用雙側打孔凍結時,凍結溫度場變化規律主要分為溫度快速下降與水冰相變階段、溫度下降、土體溫度穩定等3個階段,積極凍結期內各測點的溫度變化趨勢基本一致。數值模擬計算結果與實測數據驗證了地鐵聯絡通道三維凍結溫度場有限元分析的可靠性。初始地溫、導熱系數、比熱容對凍結溫度場影響較為明顯,凍結壁交圈時間與初始地溫、比熱容近似呈線性遞增關系,初始地溫每升高5 ℃,交圈時間延長2 d,交圈時間隨比熱容增加而延長;凍結壁交圈時間與導熱系數呈負相關,導熱系數每增高10%,交圈時間縮短1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