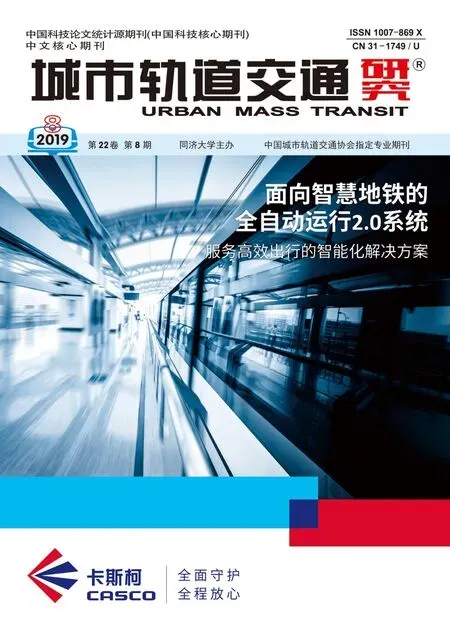盾構(gòu)施工對(duì)歷史保護(hù)建筑的影響及控制研究*
黃 杉 王尉行 李谷陽(yáng) 李曉亮 王海飛 徐前衛(wèi) 孫梓栗
(1. 中鐵五局電務(wù)城通公司,410205,長(zhǎng)沙;2.同濟(jì)大學(xué)道路與交通工程教育部重點(diǎn)實(shí)驗(yàn)室,201804,上海//第一作者,工程師)
0 引 言
隨著城市軌道交通系統(tǒng)的快速發(fā)展,越來越多的盾構(gòu)隧道不可避免地穿越或鄰近已有建筑物。盾構(gòu)施工會(huì)在地層中產(chǎn)生卸荷效應(yīng),使周圍土體產(chǎn)生變形,當(dāng)變形傳遞到建筑物下方時(shí)會(huì)引起地基變形。盾構(gòu)隧道對(duì)鄰近建筑物主要有三個(gè)方面的影響,即沉降、傾斜以及開裂[1]。國(guó)內(nèi)外學(xué)者主要從理論分析、數(shù)值模擬和監(jiān)測(cè)數(shù)據(jù)分析三個(gè)方面研究盾構(gòu)施工對(duì)相鄰建筑物的影響。例如,文獻(xiàn)[2]分析了實(shí)測(cè)隧道下穿建筑物變形規(guī)律,提出了采用單線隧道已有的Peck修正公式疊加得到雙線隧道的地基基礎(chǔ)沉降規(guī)律。文獻(xiàn)[3]將土體損失簡(jiǎn)化為擾動(dòng)荷載,對(duì)鄰近建筑物的盾構(gòu)施工引起的地面沉降進(jìn)行了理論分析和數(shù)值模擬,提出了盾構(gòu)臨近建筑物施工的控制措施。文獻(xiàn)[4]結(jié)合工程實(shí)際,基于建筑物與隧道中心的距離和建筑物不同基礎(chǔ)類型兩個(gè)因素,用數(shù)值模擬的方法研究了隧道開挖對(duì)上覆建筑物基礎(chǔ)變形的影響。
在北京地鐵8號(hào)線天橋站—永定門外站區(qū)間隧道施工過程中,盾構(gòu)需要從重點(diǎn)保護(hù)文物燕墩下方穿過。燕墩屬磚砌結(jié)構(gòu),且年代較為久遠(yuǎn),盾構(gòu)掘進(jìn)勢(shì)必對(duì)其結(jié)構(gòu)安全造成影響。有鑒于此,借助數(shù)值分析軟件對(duì)盾構(gòu)側(cè)穿燕墩的施工過程進(jìn)行模擬,研究了盾構(gòu)近接施工引起的地層變形及對(duì)燕墩的受力和變形的影響,提出了地層加固方案和施工控制措施,相關(guān)成果可為今后類似工程提供借鑒和參考。
1 工程概況
天橋站—永定門外站區(qū)間于K34+802.400處側(cè)穿北京市保護(hù)文物建筑——燕墩。燕墩是一座磚臺(tái),其上豎有清乾隆皇帝御制碑一座,是北京著名碑刻之一。燕墩外形下寬上狹,平面呈正方形,臺(tái)底各邊長(zhǎng)14.8 m,臺(tái)面長(zhǎng)13.9 m,臺(tái)底至臺(tái)面高約8 m。燕墩位于區(qū)間西側(cè),距離右線最小距離為7.915 m,此處盾構(gòu)線間距為16.8 m,覆土22.3 m。地鐵線路與燕墩的空間位置關(guān)系如圖1所示。
圖2給出了盾構(gòu)穿越施工區(qū)段的地質(zhì)剖面。該處隧道埋深約為22.3 m,地下水距離隧道頂部約為3.94 m。

圖2 區(qū)間地質(zhì)剖面示意圖
2 盾構(gòu)側(cè)穿燕墩施工模擬
2.1 計(jì)算模型
圖3給出了盾構(gòu)側(cè)穿燕墩的數(shù)值計(jì)算模型,土體橫向邊界長(zhǎng)68.0 m,豎向邊界長(zhǎng)48.3 m,縱向邊界長(zhǎng)度60.0 m,左、右線隧道模擬的是從777環(huán)到827環(huán)的襯砌結(jié)構(gòu)。
為考慮地下水滲流與土體因開挖造成的應(yīng)力狀態(tài)改變之間的相互影響,采用流-固耦合分析模式進(jìn)行計(jì)算。地基土、燕墩、管片和注漿層均采用實(shí)體單元模擬,地基土采用Mohr-Coulomb彈塑性模型,燕墩、管片和注漿層采用各向同性彈性模型。土層、管片、注漿層及燕墩的計(jì)算參數(shù)如表1~表2所示。

圖3 隧道側(cè)穿燕墩計(jì)算模型圖

地層重度/(kN/m3)黏聚力/kPa摩擦角/(°)體積模量/MPa剪切模量/MPa孔隙率滲透系數(shù)/(m/d)①1 65008.004.462.060.732.30③1 57023.258.644.572.110.720.23③31 629030.0036.6716.920.6569.00④1 60021.6711.927.833.610.820.23④32 000030.0018.949.760.620.71⑤1 670040.0039.5818.270.501 400.00⑥1 49722.508.809.924.580.810.23⑦21 647030.0027.0812.500.6081.00⑦1 694045.0039.5818.270.452 300.00

表2 彈性實(shí)體單元計(jì)算參數(shù)
2.2 施工過程模擬
按照實(shí)際施工工況進(jìn)行開挖模擬,即左線隧道先開挖24 m,左、右線隧道隨后一同開挖36 m,右線隧道再開挖24 m。左、右線隧道每次開挖長(zhǎng)度為5環(huán)6 m,隧道襯砌施作和注漿施工應(yīng)滯后開挖面6 m。開挖面支護(hù)壓力按照太沙基松動(dòng)土壓力計(jì)算,隧道頂部側(cè)壓力為140 kPa,中心處側(cè)壓力為215 kPa,變化梯度為25 kPa。
3 計(jì)算結(jié)果分析
3.1 地層豎向變形
左、右線盾構(gòu)掘進(jìn)完后的總體豎向位移如圖4所示。最大沉降值約為10.07 mm,發(fā)生在左線隧道827環(huán)拱頂和777環(huán)地表位置;最大隆起值約為11.37 mm,發(fā)生在左線隧道827環(huán)拱底附近。
圖5為數(shù)值模擬得到的盾構(gòu)刀盤到達(dá)不同管片環(huán)位置時(shí)的地表豎向位移監(jiān)測(cè)斷面的變形曲線。該監(jiān)測(cè)斷面位于燕墩中心處的第800環(huán)管片位置。地表變形曲線有一個(gè)沉降峰值,最大沉降值為5.91 mm,出現(xiàn)在刀盤距離燕墩20 m左右的位置。分析盾構(gòu)通過前后的地表豎向位移曲線可知,該斷面處的地表豎向變形表現(xiàn)為隨著盾構(gòu)的接近而逐步發(fā)生沉降,而當(dāng)盾構(gòu)遠(yuǎn)離該監(jiān)測(cè)斷面后,則沉降值趨于穩(wěn)定。

圖4 左、右線盾構(gòu)掘進(jìn)完成后豎向位移云圖

圖5 數(shù)值模擬第800環(huán)監(jiān)測(cè)斷面處地表豎向位移曲線
3.2 孔隙水壓力分析
圖6為盾構(gòu)通過后的土體孔隙水壓力分布圖。由于施工擾動(dòng)引起開挖面附近土體膨脹,在開挖面附近形成負(fù)的超孔隙水壓力,孔隙水向開挖面附近流動(dòng),后期由于超孔隙水壓力的消散會(huì)使土體發(fā)生固結(jié)沉降,這可能會(huì)對(duì)地表的燕墩產(chǎn)生不利影響。

圖6 左、右線隧道開挖完后的孔隙水壓力
3.3 燕墩結(jié)構(gòu)變形分析
圖7是計(jì)算得到盾構(gòu)開挖完成后的燕墩豎向位移云圖,圖8分別給出了燕墩各角點(diǎn)的變形曲線圖。左線隧道開挖20環(huán)后,此時(shí)盾構(gòu)并沒有通過燕墩,燕墩整體有一個(gè)微小的隆起變形;左線隧道開挖50環(huán)后,燕墩除J-15-04角點(diǎn)所在區(qū)域外,均發(fā)生沉降變形,且距離盾構(gòu)開挖區(qū)域最近的J-15-01附近區(qū)域沉降值最大為1.85 mm;左、右線隧道開挖完后,燕墩J(rèn)-15-04附近區(qū)域發(fā)生微小的隆起變形,其余區(qū)域均發(fā)生沉降變形,且J-15-01附近區(qū)域沉降值最大為2.22 mm。

圖8 燕墩各角點(diǎn)豎向位移圖
3.4 燕墩結(jié)構(gòu)應(yīng)力分析
圖9、圖10是左、右線盾構(gòu)開挖后燕墩的最大主應(yīng)力和最小主應(yīng)力云圖,燕墩最大拉應(yīng)力為0.139 MPa,最大壓應(yīng)力為0.461 MPa。最大主應(yīng)力對(duì)應(yīng)最大拉應(yīng)力,最小主應(yīng)力對(duì)應(yīng)最大壓應(yīng)力,對(duì)于磚砌結(jié)構(gòu)的燕墩來說,盾構(gòu)施工引起的拉應(yīng)力在其允許范圍內(nèi)。

圖9 燕墩最大主應(yīng)力云圖

圖10 燕墩最小主應(yīng)力云圖
4 施工控制措施及實(shí)測(cè)數(shù)據(jù)分析
4.1 盾構(gòu)穿越燕墩的保護(hù)措施
1)由于燕墩基座位于右線盾構(gòu)施工的影響范圍內(nèi),故右線盾構(gòu)施工時(shí),除嚴(yán)格按照盾構(gòu)施工工藝控制和監(jiān)測(cè)外,采取加大同步注漿及二次注漿量、二次深孔加強(qiáng)注漿及在左線隧道采用加強(qiáng)型襯砌環(huán)的保護(hù)方案。同步注漿量不小于建筑空隙的220%,二次注漿量不小于同步注漿量的25%。盾構(gòu)過燕墩的加強(qiáng)型襯砌環(huán)設(shè)置范圍如圖11所示。

圖11 盾構(gòu)側(cè)穿燕墩加強(qiáng)襯砌環(huán)設(shè)置平面圖
2)如圖12所示,二次深孔注漿即通過加強(qiáng)襯砌環(huán)管片(管片主筋由φ20 mm增強(qiáng)至φ22 mm)吊裝孔及新增注漿孔打設(shè)鋼花管進(jìn)行管片壁后注漿,每環(huán)加強(qiáng)襯砌環(huán)管片的吊裝孔及新增注漿孔共有16個(gè),沿圓周均勻布置。

圖12 盾構(gòu)側(cè)穿燕墩段二次深孔注漿斷面示意圖
二次深孔注漿工藝流程及注漿設(shè)備同二次補(bǔ)漿,漿液采用水泥-水玻璃雙液漿,漿液配比同二次補(bǔ)漿漿液配比,注漿壓力為0.5~0.8 MPa,注漿應(yīng)控制在距離開挖面20 m左右。
4.2 盾構(gòu)掘進(jìn)參數(shù)管理
4.2.1 上部土倉(cāng)壓力
圖13為789~815環(huán)推進(jìn)時(shí)實(shí)測(cè)土倉(cāng)上部土壓力與理論計(jì)算值的比較。此段隧道平均埋深22.3 m,根據(jù)太沙基松動(dòng)土壓力公式可得土倉(cāng)壓力理論計(jì)算值為0.100~0.127 MPa。由圖13可知,大部分實(shí)際土倉(cāng)壓力在理論計(jì)算值的范圍內(nèi)。

圖13 土倉(cāng)壓力實(shí)測(cè)值與理論計(jì)算值
4.2.2 推力管理
對(duì)于土壓平衡盾構(gòu)來說,盾構(gòu)千斤頂?shù)耐屏褪峭七M(jìn)過程中盾構(gòu)遇到的全部阻力之和,盾構(gòu)總推力理論計(jì)算值是20 794~29 706 kN。實(shí)測(cè)盾構(gòu)總推力約為14 000~20 000 kN,比理論計(jì)算值小,因?qū)嶋H施工采取欠壓推進(jìn)模式,以免引起過大變形。
4.2.3 扭矩管理
根據(jù)理論計(jì)算公式可得刀盤扭矩值為2 326~5 815 kN·m,實(shí)測(cè)789~815環(huán)扭矩值在1 800~2 500 kN·m范圍內(nèi),靠近經(jīng)驗(yàn)估算值下限,比理論計(jì)算值略小。
4.2.4 盾構(gòu)掘進(jìn)參數(shù)管理
盾構(gòu)實(shí)測(cè)的推進(jìn)速度在60~70 mm/min間波動(dòng),螺旋輸送機(jī)轉(zhuǎn)速在5.5~6.5 r/min間波動(dòng),刀盤轉(zhuǎn)速在0.9~0.94 r/min間波動(dòng)。結(jié)合土倉(cāng)壓力實(shí)測(cè)值可以看出,此種盾構(gòu)掘進(jìn)參數(shù)組合基本能夠保證盾構(gòu)掘進(jìn)面的壓力與支護(hù)力相等,有效控制了地表的沉降變形。
4.3 實(shí)測(cè)地表變形分析
圖14為實(shí)際施工中地表監(jiān)測(cè)斷面所反映的地表沉降變化曲線。與圖5中數(shù)值計(jì)算結(jié)果相比可以發(fā)現(xiàn),二者所反映的地表變形隨盾構(gòu)推進(jìn)的變化規(guī)律基本一致,且最大沉降值均出現(xiàn)在距離燕墩20 m左右的位置。數(shù)值計(jì)算得出最大沉降量5.91 mm,略高于實(shí)測(cè)最大沉降量3.6 mm,這說明實(shí)際施工時(shí)實(shí)施的二次注漿有效控制了地表的沉降量。

圖14 實(shí)測(cè)第800環(huán)監(jiān)測(cè)斷面處地表變形歷時(shí)曲線
4.4 實(shí)測(cè)燕墩變形分析
圖15分別給出了實(shí)測(cè)得到燕墩各角點(diǎn)的沉降變形圖。對(duì)比圖8和圖15可知,隨著盾構(gòu)推進(jìn),燕墩整體產(chǎn)生沉降變形,且沉降值小于2.5 mm,在控制范圍內(nèi),這與數(shù)值模擬一致。但在實(shí)測(cè)結(jié)果中,J-15-04并未產(chǎn)生隆起變形,這是由于盾構(gòu)采取欠壓推進(jìn)所致。

圖15 施工監(jiān)測(cè)燕墩各角點(diǎn)沉降變形圖
5 結(jié)語(yǔ)
結(jié)合北京地鐵8號(hào)線側(cè)穿燕墩的工程實(shí)例,通過數(shù)值分析軟件對(duì)盾構(gòu)施工過程進(jìn)行動(dòng)態(tài)模擬,結(jié)合現(xiàn)場(chǎng)監(jiān)測(cè)數(shù)據(jù)和盾構(gòu)掘進(jìn)參數(shù),得到以下結(jié)論:
1)地表豎向變形整體表現(xiàn)為隨著盾構(gòu)推進(jìn)而逐步發(fā)生沉降,盾構(gòu)遠(yuǎn)離監(jiān)測(cè)斷面后,沉降值趨于穩(wěn)定。
2)隨著盾構(gòu)推進(jìn),燕墩整體產(chǎn)生沉降變形,且沉降值小于2.5 mm,在控制范圍內(nèi)。
3)采取合理的盾構(gòu)掘進(jìn)參數(shù)和二次深孔注漿工藝能夠有效減少盾構(gòu)開挖對(duì)上方建筑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