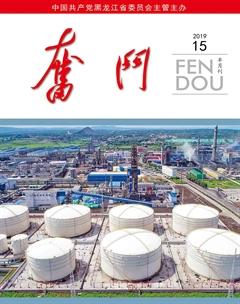永遠赤誠的心
任紅禧 張佳蕊 佟堃
2019年6月29日上午,在木蘭縣境內的松花江大橋上,一位老人手扶橋欄望著江面哽咽著說:“松花江啊,你的女兒回來了!”
越過2400公里的距離,跨過72載的光陰,自1947年參軍離鄉后,馬旭終于踏上了魂牽夢繞的故土。
去時豆蔻芳華,歸來滿頭華發。雖然遠在他鄉,但她的心從未離開過這片故土。正是這份對桑梓的深深眷戀,才有了“為家鄉教育捐資千萬元”的驚人之舉。而在這一壯舉的背后,展示給世人的則是一顆始終赤誠如初的心。
一位龍江女兒的家園情懷
——“如果不是當初家鄉人送我去當兵,就沒有我的今天。”
2018年3月,木蘭縣委副書記徐向峰接到一個陌生來電,電話那頭是一位名叫金長福的空降部隊老兵:“我有個叫馬旭的老首長,想給家鄉木蘭捐一筆錢,用作教育事業。”

馬旭是誰?捐款數額是多少?起初,這些信息均不清楚。為了搞清這些問題,木蘭縣委責成縣教育局負責人進行對接。經過與金長福以及馬旭本人的多次溝通,關于馬旭的情況逐漸清晰起來。
1933年3月,馬旭出生于木蘭縣建國鄉李國寶屯的一個貧苦家庭,父親去世得早,馬旭和弟弟與母親相依為命,吃了上頓沒下頓。每到秋收,母親就去別人家的田里撿拾收割后遺下的玉米、土豆。
“母親會說大鼓書,一家人就靠她說書養活。”在馬旭的記憶中,母親李成珍是一個“落魄的大家閨秀”,因家道中落流落東北,被外祖父許配給木蘭的一個農民,也就是馬旭的父親。
因為李成珍識文斷字,很多村民拿著《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小說找她“說古”。當時大家都很窮,聽書的人用破碗抓一點兒小米,或者用小碟盛幾滴煤油,就算是聽書的費用了。
李成珍十分重視孩子的教育,說書之余,她還教馬旭姐弟倆識字、打算盤,這也為他們日后參軍并考軍校打下了基礎。
1946年2月,木蘭縣成立了民主政府。1947年,村里的農會主任建議馬旭的母親送一個孩子去當兵,因為當時弟弟年紀太小,母親就讓馬旭去了。
臨行前一夜,母親為馬旭縫補衣服,邊補邊哭,馬旭則躲在被窩里抽泣。第二天送行時,母親跟著隊伍一直送到松花江邊,不停地呼喊著女兒的名字……
就在馬旭入伍的第二年,母親因病去世了。
入伍后,馬旭先后參加了遼沈戰役、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戰爭,后被保送至第一軍醫大學,畢業后一直從事軍事臨床醫學工作。直到上世紀80年代,馬旭以大校軍銜從空降兵某部離休。馬旭的弟弟后來也參軍,并考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即著名的“哈軍工”),畢業后一直從事國防事業。
樹高千尺忘不了根。馬旭常說:“如果不是當初家鄉人送我去當兵,就沒有我的今天。”少小離家的她,始終念念不忘的就是家鄉。“在軍醫大學讀書時,我就想節約一滴水、節省一粒米、節攢一分錢,回報家鄉,為家鄉建設做貢獻。”
馬旭將積蓄捐給家鄉的想法由來已久,但不知道該如何聯系當地政府。直到2017年,空降兵部隊邀請退伍老戰士參加紀念黃繼光的活動,馬旭碰到了多年未見的傘降教員金長福,當時,他剛從遼寧撫順的民政部門退休。考慮到金長福身在東北,離自己的家鄉更近,馬旭便請他幫助聯系木蘭縣委,以完成捐資心愿。
在多方努力下,馬旭最終得償所愿:2018年9月13日,馬旭的300萬元第一筆捐款匯到木蘭;2019年4月8日,馬旭購買的理財產品到期后,將余下的700萬元也如數匯出。
2019年6月28日,受家鄉人民盛邀,馬旭終于踏上歸途,并于次日乘車回到木蘭。
看著靜靜流淌的松花江水,馬旭想起當年媽媽站在江邊喊她名字時的場景,不禁感慨萬千。如今,媽媽不在了,她把松花江當作了母親。
一個軍人的使命擔當
——“如果不能和他們一起跳傘,我這個軍醫就是廢物!”
這幾年,馬旭的一只腳幾乎失去了著地的力量,走路越發吃力,那是因為戰爭年代留下的舊傷開始反噬。
當年,馬旭入伍不久便考入東北軍政大學吉林分校。學習半年后,她成為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的一名衛生員。
1948年10月,馬旭跟隨部隊參加遼沈戰役,冒著槍林彈雨搶救傷員。在黑虎山地區的一次戰斗中,馬旭緊跟戰士進行搶救,不幸被一塊炮彈皮擊中大腿,她掙扎著站起來,可沒跑幾步又倒下了,最后被戰友用擔架抬了下去。在后方醫院沒待多久,馬旭就想方設法回到前線。“前線的傷員需要我。”馬旭說。
1951年,馬旭隨部隊跨過鴨綠江,參加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戰爭,救死扶傷,多次立功受獎,被授予抗美援朝紀念章、保衛和平紀念章和朝鮮人民政府三等功勛章。
今天,馬旭對過去的軍功很少提及,更不居功自傲,她說:“和那些犧牲的戰友相比,我能活著就感到無比的幸福。”
從朝鮮回國后,作為優秀戰地衛生員,又有一定的文化基礎,馬旭被保送到第一軍醫大學深造。1956年,馬旭以全優的成績畢業,被分配到武漢軍區總醫院,當上了一名外科軍醫。憑著精湛的醫技,剛剛20歲出頭的她就獲得了“軍中一把刀”的美譽。
1958年,思想、業務全面過硬的馬旭光榮入黨。
在武漢軍區總醫院工作不到三年,馬旭主動要求調往前線野戰部隊醫院,到步兵某師衛生營手術繃帶所任軍醫。
1961年,中央軍委命令由參加過上甘嶺戰役、黃繼光烈士生前所在的英雄部隊某軍為主體,組建中國人民解放軍空降兵部隊。馬旭受命參與新部隊的衛勤保障工作。
“如果僅僅在后方做衛勤保障工作,怎么能了解傘兵的需求呢?”馬旭在心里打了一個問號,于是她決定:“我一定要和傘兵一起跳傘!”可馬旭的身高只有一米五三,體重僅有三十五公斤,不能達到空降兵訓練大綱對跳傘的身體要求,更何況當時沒有女兵傘降的先例。為此馬旭多次找到部隊首長:“部隊同志都跳傘下去了,如果不能和他們一起跳傘,我這個軍醫就是廢物!”

馬旭沒有氣餒,不能參加跳傘訓練,就站在一旁觀察揣摩。到了晚上,等傘兵們訓練完了,她就偷偷跑到訓練場,借著月光練習。為了熟練掌握動作要領,她還在宿舍挖了一個坑,墊上細沙,把椅子疊到桌子上,自制了一個簡易跳臺,每天晚上練習幾百次。
練了半年多,馬旭感覺“差不多了”,于是,咬破指頭寫了一封血書:“身在空降師,如果不跳傘,怎么能叫傘兵?我懇求組織批準,并保證成為合格的傘兵!”
師首長無奈地說:“如果你跳得比其他戰士好,就讓你上!比他們差,以后就別再提了!”
馬旭二話沒說,跳上平臺,連跳3次,動作標準利索,贏得了在場戰士們的陣陣掌聲,師首長這才不得不同意馬旭跳傘的請求。
從1962年秋初次跳傘,此后20多年間,馬旭先后跳傘140多次,雖然她的體重過輕,跳傘落地時總是飄到比其他戰士更遠的地方,但整個跳傘生涯沒有出過其他差錯。從她的安全角度考慮,1984年起,部隊不再允許她上天。
在人民共和國空降兵的歷史里,馬旭創造了三項之最——第一位女空降兵、跳傘次數最多的女兵、實施空降年齡最大的女兵。
一對科技工作者的探索攀登
——“我感覺從來沒有離休過,總覺得時間不夠用。”
馬旭除了軍醫的身份外,還是一個勤奮的科技工作者。
在部隊的日常工作中,馬旭和丈夫顏學庸一起從事科研工作,他們始終圍繞著部隊的實戰需要,開發研制了許多實用性很強的發明。
比如,馬旭夫婦在做手術時發現,一針一針地縫合創口速度太慢,不符合戰地需要,于是,他們研發了一款拾針器,一次性能縫合3針。
充氣護踝則是馬旭夫婦獲得的第一個發明專利。在隨軍空降時,馬旭發現,在著陸的瞬間,強大的沖擊力容易造成戰士的腰部、踝部骨折。在當時,因為跳傘骨折造成的非戰斗減員高達30%。如何才能有效避免這種情況,也就成了他們攻關的課題。
馬旭和顏學庸經過反復試驗,最終設計出了套在腳上的充氣護踝。為了讓官兵放心用,馬旭夫婦先在自己身上進行試驗。為了驗證效果,他們20多次從天而降,在花甲之年還前往高原跳傘。
1995年,他們又研制出“單兵高原供氧背心”。當時,空降兵在高原跳傘,因為氧氣稀薄,需要背負氧氣瓶。但是,氧氣瓶的分量太重,且攜帶不便,馬旭夫婦便一起研究,是否可以發明一款穿在身上的輕便供氧裝備。于是,他們用航天材料制作成背心狀的供氧袋,既穿戴方便、行動靈活,又解決了高原供氧問題。這款發明于1996年獲得國家發明專利。當年,《解放軍報》的一篇報道稱贊這項發明“填補了空降兵高原跳傘供氧上的一項空白”。
在馬旭夫婦發明的多項專利中,應用最為廣泛的一項就是治療萎縮性胃炎的藥劑。
早些年,空降部隊的一些新戰士因為在跳傘前高度緊張,睡不著覺、吃不下飯,常常餓著肚子進行跳傘,等安全著陸后又猛吃一頓。一來二去,不少戰士患上了萎縮性胃炎。
為了治療這個疑難病癥,馬旭夫婦從祖國傳統醫藥學和民間偏方中尋找治療方法,又利用西醫提取技術,萃取有效藥物成分,最終研制出一種治療萎縮性胃炎的藥劑。當年,馬旭也因為這項發明引起媒體的廣泛關注。
一些制藥廠商和醫藥研究單位先后和馬旭建立合作關系,陸續生產了一些藥劑成品。這些專利轉讓費也成了日后馬旭為家鄉捐款1000萬元中的一部分。直到今天,還經常有患者上門求醫問藥。
“活到老,學到老。我感覺從來沒有離休過,總覺得時間不夠用。”隨著科研的不斷深入、拓展,馬旭越發感覺知識不夠用,78歲那年,在顏學庸的支持下,馬旭做出一個驚人的決定——考研。
最終,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基礎醫學院被馬旭的精神所打動,破格錄取了她。盡管困難重重,但馬旭很是珍惜這次學習機會。經過3年的刻苦學習,馬旭大多學科都順利通過考試,只有外語沒有過關。于是,在家中的飯桌、床頭,貼滿了寫有密密麻麻的外語小字條——那是馬旭學外語的土辦法。
幾十年間,馬旭夫婦筆耕不輟,在軍內外報刊發表了100多篇學術論文和科研體會,還出版了《空降兵生理病理學》《空降兵體能心理訓練依據》等專著,填補了我國在這些領域的空白。
一名共產黨員的初心本色
——“心里裝著黨和人民利益的人,是最美的!”
馬旭平時愛唱歌,從武漢回木蘭,她一路走一路唱,其實只唱了一首歌——《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是從她心底流出的歌。
在武漢市黃陂區木蘭山下的軍營大院旁,有一處被樹木、雜草圍攏的小院,院里有兩間平房,這便是馬旭的家。擁擠的小房子里堆滿了書,他們睡的是一張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硬板床,兩只沙發早已破舊不堪,沙發面上墊了好幾層麻袋片。
“這就是那個捐出1000萬元積蓄的馬旭家?”凡是來過這里的人,都會心生劇烈的反差,難以將這樣清貧的生活與1000萬元的捐款人聯系到一起。
“這筆錢是我們一分一角攢起來的。”馬旭說,“我們倆舍不得花錢,也從不買衣服,一輩子始終穿軍裝。70多年來,大部分工資都存入銀行,再把利息算入本金,錢越存越多。加上專利轉讓費和專著版權費、稿費,日積月累,便攢下了1000萬元的積蓄。”
與馬旭“一擲千金”的大氣相比,生活中的馬旭卻“小氣”得令人心酸。
這些年,老兩口一直共用一部過時的翻蓋手機,身上穿的迷彩作訓服早已洗得褪色,腳上最貴的鞋是一雙僅15元的“人造革”紅皮鞋,掉了皮、開了線,用膠粘上還在穿。
走在馬路上,只要看到被人丟棄的塑料瓶,馬旭都會撿起來,攢到一起賣廢品。
有些村民非常不理解:“倆人的工資這么高,日子卻過這么苦,劃不來。”
可馬旭說:“人和人的情況不一樣。我十幾歲就受黨的恩惠,在部隊的大熔爐里成長,要知恩圖報。我常想,如果我心里裝著黨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那我可能是最美的;如果我心里有私心雜念,那我可能是最丑的。”
有些人不理解馬旭,但馬旭也有不理解的人。每當看到有領導干部腐化墮落的通報新聞,馬旭既痛恨又痛心:“真不明白,他們要那么多錢干嘛?”
有人覺得,馬旭夫婦過得太清苦,可馬旭并不這么認為:“我不追求物質生活,物質生活的追求是沒止境的。”
馬旭和顏學庸雖然節儉,但他們并不以此為苦。相反,身為醫生的他們更重視飲食健康:很少吃煎、炒、炸的食物,早餐是蒸土豆、咸鴨蛋和酸奶,中午和晚上則是將西紅柿、時令蔬菜、牛肉、大米放在一起煮成的粥。
顏學庸自豪地說:“我們沒有糖尿病,沒有‘三高,我們很知足。”
事實上,馬旭夫婦并非“苦行僧”,只是他們認為“不該花錢的地方絕不亂花”,他們在求知求學方面就很大方。
2012年開始,為了學好外語,也為了親眼看看國內外的差距,經組織批準,馬旭和顏學庸先后自費去過日本、俄羅斯、法國、美國等十幾個國家,“走出去看看世界”。而每次回來,“對祖國的感情就更深一步”。
如今,馬旭覺得此前捐款1000萬“捐少了”,“我倆的工資花不完,只要我還活著,就會繼續捐錢給家鄉。”
“為人類奉獻一切,為革命萬古長青。”這是馬旭當年囑咐侄子在馬旭父母墓碑上刻下的兩行字。這,既是她對父母的深情告慰,也是她的初心誓言,更是對她一生無私奉獻的最好詮釋。
軍中伉儷的大愛情深
——“她一直都是最美的。”
在馬旭身邊,始終站著一位了不起的男人——顏學庸。從矢志奮斗的同志、生死相依的戰友,到志同道合的伙伴、相濡以沫的伴侶,顏學庸始終與馬旭并肩前行。
盡管媒體對顏學庸的報道并不多,但細心的人依然能品味出他的人格魅力。
出生于重慶市江津區的顏學庸與馬旭同歲,經歷相仿,他于1950年入伍后參加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戰爭,1959年進入第三軍醫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空降兵部隊任軍醫。
在30歲之前,馬旭并沒有談婚論嫁的念頭,直到顏學庸走進她的生活。
當時,顏學庸已是馬旭工作上的好伙伴。一次,他們聽說蘇聯的一名駐島戰士突發闌尾炎,必須馬上手術,但島上只有一名醫生,沒有助手幫忙打開腹部,導致無法實施手術。
“如果遇到類似情況,我們該怎么辦?”馬旭和顏學庸幾乎同時發問。“能否發明一種自動開腹器,在手術過程中幫助醫生拉開腹部?”兩人的想法一拍即合。他們一起設計、反復修改,又把圖紙送到上海的醫療器械廠家生產。最終,自動開腹器在臨床上得到應用。
1963年,兩個志同道合的年輕人走到了一起。
夫妻情深,相守56載,即便年至耄耋、滿頭白發的今天,他們無論走到哪兒都手牽著手,穿著與眾不同的“情侶衣”——一身褪色的迷彩服,胸前佩戴著黨員徽章。他們一起跳交際舞,一起騎自行車鍛煉,一起看書學習,一個輕聲唱歌、一個打著節拍,還有著說不完的悄悄話……
盡管年過八旬,但馬旭依然喜歡扎著兩個羊角辮,由顏學庸寸步不離地牽著她的手。
而在家里時,馬旭卻儼然是顏學庸的“領導”。馬旭只需坐著動動嘴“支使”,顏學庸便會很快收拾好一切。
對馬旭來說,丈夫是最愛她、寵她的人,也是最懂她的人。對于馬旭捐款的想法,顏學庸早在結婚之初就已知曉——馬旭對他說:“以后要攢點兒錢,支援家鄉建設。”對于妻子的想法,顏學庸的態度是“完全支持”。
這對相濡以沫的夫妻,年輕時卻做過一個令人難以理解的決定——不要孩子。一方面,馬旭參加跳傘時已屬“大齡女兵”了,能跳傘的時間本就不多,她不希望因懷孕生子而耽誤訓練,甚至提前退役;另一方面,由于馬旭體質瘦弱的問題,懷孕本身也極具風險。經過反復考慮,最終,夫妻倆放棄了做父母的機會。
在回木蘭參觀當地的一所小學時,馬旭和顏學庸摸著孩子們的頭說:“我們雖然沒有孩子,但捐助家鄉的孩子讀書,就是把他們當做我們的孩子。”馬旭夫婦雖然沒有過為人父母的感受,但他們共同付出的卻是慈父慈母般的無私大愛。
有媒體問:“您覺得馬老什么時候是最美的?”
顏學庸毫不猶豫地回答:“她一直都是最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