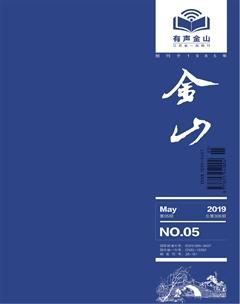夜色迷蒙西津渡
唐紅生
很久以前就讀過唐代詩人張祜的一首《題金陵渡》:“金陵津渡小山樓,一宿行人自可愁。潮落夜江斜月里,兩三星火是瓜洲。”乍看“金陵”二字,以為是南京,其實在鎮江。因為西津渡三國時叫“蒜山渡”,唐代名為“金陵渡”,宋代以后才用此名,而當地人更愛叫小碼頭。
家鄉隸屬鎮江,路過西津渡時,也只在白天走馬觀花。隨著年齡的增長,對古鎮古街興趣漸濃。一直以為行走在西津渡這樣有歷史、有文化的地方,需在夜間,最好是在冬夜,于是決定前往。
西津渡位于云臺山麓,與鎮江博物館比鄰而居。穿過城市的燈火,到達后突然靜謐了許多。踏著石階而上,兩邊青磚圍墻,時光切換,仿佛走進了歲月長廊。北風嗖嗖,少有游人,暖色的景觀燈為寒夜帶來絲絲暖意。一道磚砌的拱券門立于坡頂,上書“西津渡街”。
穿門而過,頓時變窄,青石板鋪就的彎彎巷道,燈光像為它抹上一層蠟,油光锃亮,更顯幽深古樸。眼前的五十三坡,共有53級臺階,古時它是通往渡口的唯一通道。不知多少人在此惜別,又有多少人在此相逢。
一個轉彎,就見喇嘛塔式過街石塔,矗立于通道之上,周身潔白如玉。這座元代石塔又稱昭關石塔,歷經700多年風雨,神態依然。
石塔一側是康熙年問的救生會,帶有慈善性質的水上安全救助機構;另一側是宋代的觀音洞,墻體斑駁。讀著幾座券門上“同登覺路”“共渡慈航”的字樣,彌漫起宗教氣息。古時江面寬闊,千百年來,一葉扁舟在波濤中橫渡,幾多危險,人們只能祈求于菩薩的護佑。這其中有渡江人,也有船夫,吉兇不知,生死未卜。想到這里,競有點傷感。
圍墻上一側門通往觀景臺,映入眼簾的是另一番景致。屋脊、檐口、瓦當、馬頭墻,被輪廓燈光一一勾勒,層層疊疊,錯落有致,如微波細浪一直涌向長江,格外迷人。
古道開始沿階而下,青石板中間是一坡面,當中有一道深深的車轍。這是當年運貨物的獨輪車留下的。遙想人來貨往的繁盛景象,耳邊傳來千年的歷史回聲。
昔日的碼頭早已沉降到地下,千年街基的石痕,用鋼化透明玻璃圍罩其上。始創于六朝時期,歷經唐宋元明清的古道,一層層疊加,“一眼看千年”,觸發了思古之幽情。鎮江地處長江與京杭大運河交匯處,是南北水上交通、漕運樞紐。古渡原緊臨長江,清朝以后,江灘淤漲,江岸逐漸北移,現在距江岸已有300來米。
一旁暗紅的“待渡亭”早就失去待渡功用,成為游人憩息場所。變換的是滄海桑田,刻錄的是歷史印記。先賢們的腳印、六朝后的痕跡依舊清晰。王安石揚帆北上,蘇軾、米芾在此候船,迷戀江南的乾隆帝是否逗留?
白日素面朝天的小碼頭街已濃妝艷抹,儼然變成胭脂美人。不寬的街道蜿蜒延伸,兩邊一二層的小店鱗次櫛比,或掛匾、或挑旗,連同灰磚墻、木板門、雕花窗,都被紅紅的燈籠涂抹上時光的古韻。有的店已經打烊,行人三三兩兩,無喧囂、無吆喝,十分安靜。本地的各種特色,諸如鎮江香醋、鍋蓋面、肴肉應有盡有。高高疊起的蒸籠熱氣騰騰,氤氳中散發出米糕的香味。咖啡店中,兩位金發碧眼的女郎正喝著咖啡,享受異國風情。
明月當空,隨意穿過一條小巷,都往時間縱深里鉆。那翹角飛檐、朱漆廊柱、墻上枯藤,無不娓娓訴說著古渡老街的千回百轉。
冷月下,臘梅暗香浮動,斜依在花格窗上,靜靜流淌出雅韻。眼前的蒜山雖不高,卻孤峰突兀。蒜山因“山多澤蒜”而名,當年江水經年不息地拍打著山崖,也成了扼守江岸的屏障。山頂一小亭,書寫著智者的傳奇。相傳三國時期,諸葛亮和周瑜在亭下共商破曹大計,二人在掌心都寫了“火”字,“火燒赤壁”成了以弱勝強的著名戰例。因此,小山也多了個美稱“算山”。
驀然抬頭,云臺山頂的云臺閣,被橘黃色的燈光映得晶瑩剔透,四周不斷變換斑斕的色彩,如夢如幻。古棧道宛如一條泛著鉆石般光暈的“珠鏈”掛在頸下,高貴典雅。
不見張祜筆下的“小山樓”,卻見池塘邊一座古戲臺,帷幔垂掛,富麗堂皇。現在雖無人,想必白天熙熙攘攘,穿著古裝的現代人,和著滔滔江水的節律,唱出西津渡的千年風情,唱出新鎮江的繁華美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