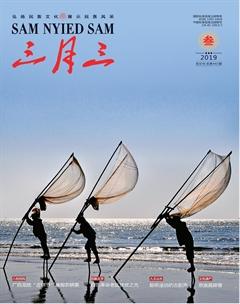潿洲島觀鯨記
梁思奇

三月學雷鋒日,我隨北海民間志愿者協會登潿洲島,參加海島環保分會成立儀式和植樹活動。下午,廣西北部灣海洋哺乳動物聯合研究組陳默博士說,有船出海觀鯨群,植樹活動結束后我便和他一起去了碼頭。
跳上可乘坐六七個人的快艇時,我看了一下手機:4點10分。我不止一次坐過這種被當地人叫作“艇仔”的小船從潿洲島到斜陽島。這兩個島相距9海里,30多年前就聲名鵲起,有“大小蓬萊”之稱。記得有一次在教師節前我到斜陽島采訪執教近30年的程霖,正好遇上一個從潿洲島前往斜陽島的豪華釣魚團,我便蹭了他們租的一艘艇仔。船一出海,西南浪一浪高過一浪,艇仔像一匹馬被扎了屁股,拼命地尥蹶子,把人的五臟六腑都抖得移了位。同行有個大漢,光著肩膀,身上文著花花綠綠的游龍,像九龍壁。他在途中臉色蒼白,差點哭出聲來。由于艙里養魚箱的塞子掉了,水漫到腳下,他以為是船漏了,用大冷天牙齒打架一般顫抖的聲音說: “進……水……了!”
我現在回想起他當時那種哭腔還想笑,他讓我知道一些表面強悍的人實際比一般人還脆弱。不過那一次真的挺恐怖的。人們常說“狂風惡浪”,其實海上最可怕的不是浪,而是涌。特別是當海面出現白色的浪花時,從岸上看去像是蓮花朵朵,煞是美麗。但在漁民眼里,這種“白頭浪”能躲則躲。浪盡管白了頭,卻并沒有衰老,只是一個老奸巨猾的魔鬼戴著一項“假發套”。記得當時的浪涌像連綿的山脈,一個接著一個壓過來,我們一船人都闃寂無聲,陷入聽天由命的沉默中。人類離開海洋已億萬斯年,重新身陷不知深淺的茫茫大海中,則完全失去了對命運的主宰。也許只有在這個時候,才意識到人本質上的那種無助與孤獨。
而這回的浪遠沒有那一次大,艇仔也比那一次小。剛過豬仔嶺,就進入了“蕩秋千”模式,浪涌像一頭蠻牛調戲著艇仔,將它頂起又放下,船底嘭嘭作響,讓人不由得擔心它會不會散架,這把第一次乘坐艇仔的人嚇得夠嗆。
我們直接駛往斜陽島東側海域,把船停在那兒。船像一片葉子在海面漂浮,附近還有幾片同樣的“葉子”,開船的鄧師傅說那是釣魚船。
海面輕波蕩漾,四面無邊無際的藍色,一時間我有一種天幕倒懸的不真實感。我幻想自己可以像《射雕英雄傳》里的鐵掌幫幫主裘千仞那樣在水上如履平地,健步如飛。今天真的能見到鯨魚嗎?它可不是誰家豢養著的牛。茫茫大海,這是它的天地,它可以逍遙自在,自由往來,它能滿足我們見到它的欲望嗎?畢竟我們的目的性太強了。墨菲定律說,如果你擔心某件不好的事要發生,那它就很有可能會發生。還在當記者時,我曾聽合浦沙田的老漁民說,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他們去捕捉現在已經絕跡的美人魚(學名“儒艮”),要是事先說出來,次日一定會一無所獲。我們事先嚷著去看鯨魚,如果鯨魚還真的現身,那它也太講義氣了。
但鯨魚真的就這么講義氣,或許知道我們求見心切,它很快就現身了。我們停下來不到10分鐘,在側前方約兩三百米的水面,一個黑色的尾巴從水里探出,有人驚叫起來。
我興奮得渾身發抖。陳默博士說鯨魚的叫聲屬于低頻,人們不能直接聽到,而它是不是能聽到人說話,如今還不能確認。我們還是壓低了聲音,用手機、相機、攝像機一通狂拍,但估計沒有幾個人拍到,因為它“驚鴻一現”就沒了蹤影。
我們像在叢林中發現了虎跡,高度“警覺”。我單手端著手機,像持著一柄隨時要扣動扳機的手槍,瞄準鯨魚出現的地方,另一只手攬住斜拉著艇仔頂篷的繩子。要是繩子斷了,我一準會掉到海里葬身鯨腹。陳默博士說鯨魚不會吃人的,它只吃魚。那我應該首先是葬身魚腹,然后才間接地葬身鯨腹。不承想,一向處于食物鏈頂端的人類,在茫茫大海中,變成了食物鏈的末端。
我們盯著的地方沒有動靜,離它幾百米靠西的方向,卻有一個鯨背露出了水面。這回每個人都看清了!大家又是一通狂拍。我來不及查看手機的畫面,只管不停地點擊按鍵,我相信自己拍著了。除了在電視和電影里,我沒有在海里見過活鯨,只見過死鯨。2004年2月24日,一條超過10米的布氏鯨擱淺在冠頭嶺西北的沙灘上,據說是漁民從瓊州海峽拖回來的。工人們在那兒連續作業一個多星期,剝開它的皮,用汽車將巨大的骨架拉走。當時做記者的我每天都跑到臭氣沖天的現場問這問那。現在想想,它也許就是這些在潿洲島、斜陽島附近海域出沒的鯨魚們的前輩。
我繃緊神經盯著海面。鯨魚像是與我們捉著迷藏一般,它不時在前面出現,又在左邊出現,又在右邊出現,在我們的側后方出現。天啊,我們被鯨魚包圍了!鯨魚像一群頑童,從不同的地方浮起,剛在這邊看到一個鐮刀狀的背鰭,另一邊又有一條像潛水艇一般浮出水面,噴著水柱,散開漫天霧氣。每次聽到“嘩啦”一聲巨響,伴隨著水牛擤鼻似的聲音,回過頭準能看到出水的鯨魚。
艇仔不停地搖晃,我試圖蹲下來保持平衡,后來干脆雙膝跪下。陳默博士說鯨魚覓食的時候,會先把魚群驅趕到一塊,然后大快朵頤。海鳥顯然知道這個秘密,成群的海鷗追逐著鯨魚,發出像集市一樣吵鬧的喈喈聲。我看到兩條鯨魚沖著天空張開巨嘴,露出白色的腹部,海鷗翔集,從鯨魚的巨口中奪食。動物之間常常有這種“相依為命”的現象,比如,有一種“燕千鳥”會飛到鱷魚嘴里幫它剔牙;成群的鬣狗總是跟在獅子后面,等待獅子獵殺羚羊時分一杯羹。那是一種血腥的慘象,不像海鷗與鯨魚之間這么和諧美好。陳默博士說,這個季節鯨魚常做露出白色肚子的求偶動作。
下午五點半歸航時,我們兩次被鯨魚“剪徑”,它們先后幾次出現在快艇右側兩三百米處,似乎存心要逗留我們到天黑。陳默博士說,鯨魚對于人類來說,還有許多未解之謎,比如它們與白海豚誰的智商更高?它們在夜間怎樣攝食?他所在的廣西北部灣海洋哺乳動物聯合研究組已觀察識別到超過20頭布氏鯨在這片海域覓食,這片海域也是我國己知的唯一一個大型須鯨的攝食場所,通俗地說,就是它們的“食堂”。鯨群逗留的時間段為每年9月到次年5月,至于其他時間段它們去了哪里不得而知。

就在我們觀察到鯨魚的當天,在同一片海域,有人目擊了一群白海豚在波光粼粼的海面追逐嬉戲。這些像“大人物”的海洋哺乳動物吸引著越來越多人的興趣。陳默博士說,觀鯨作為必要的科研活動,要盡量減少對它們的干擾。持續的打擾會嚴重影響它們的捕食、休息和育幼。把鯨魚的生活習性放在首位,才能讓它們更愿意留在附近,才能觀察到更多有趣的自然行為。我不無滑稽地想到,人們到動物園觀賞動物,都是“反客為主”,動物們被關在籠里,接受人們的評頭品足,而在這里,鯨卻是理所當然的主人。這里原本就是它們的家園,而我們才是闖入它們領地的侵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