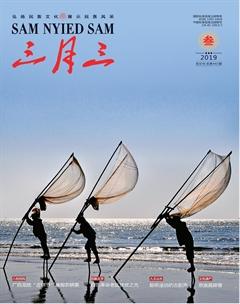素以為絢艷梅姿
石藝
讓綠城觀眾意想不到的是,單雯參加梅花獎競演的傳承版《牡丹亭》竟如此樸素又如此豐富,畫龍點睛般點染了中華戲曲的麗與美,如鹽入水般提取出中華戲曲的味與道。
單雯的《牡丹亭》無繁復的舞美,也摒棄了迷幻的燈彩,凸顯的是一方樸素的舞臺。無論是具體的湖石花樹,還是抽象的春光鳥喧,一律由單雯精湛的表演來呈現。單雯不僅以嚴謹的動作摹出湖石花樹之形,更以優美的身段繪出湖石花樹的奇姿艷影。讓人嘆為觀止的是,單雯那一絲絲貼切的眼神和表情,生動地表現了杜麗娘見此良辰美景時細膩的情思,也淋漓地詮釋了杜麗娘游園前后的心緒變化。這種表演融技、藝、道于一體,給人以美的享受。原本空蕩蕩的舞臺已是無限豐盈的藝術世界,每一寸空間與每一刻時間都被美的創造力填充。由此,觀眾所處的劇場不再是一個物理的空間,而是一個審美創造不斷生成的藝術時空;觀眾在劇場中也不再是被動地坐觀,而是在單雯表演藝術的引領下,與這種藝術之美進行積極的互動交流。近些年來,戲曲界形成了一股利用現代技術手段打造豪華舞美的風氣,單雯反其道而行之,向藝術表演純粹的內在回歸,這種素以為絢的美既難得又寶貴。
單雯《牡丹亭》的唱腔沒有因為參加梅花獎競演便刻意追求花哨的小腔來展現自己的風采,而是更注重對昆曲“水磨調”悠遠意蘊的展現,更強調對以張繼青為代表的諸多昆曲藝術家藝術探索與積淀的傳承。這種價值取向,貌似會讓單雯的表演很沒有特點,很不“單雯”,但實際上,這恰恰又讓單雯的表演最傳承、最豐厚、最突出,因而也最“單雯”。
“單雯”這個名字本身,就含有一種素以為絢的辯證。單雯在綠城的這場競演,素以為絢,即成就了她自己的風格特色,也成功地演繹了昆曲《牡丹亭》的本色所在,恰與“梅不爭春春自早”的風姿神韻相契合。對于綠城觀眾而言,只有單雯、昆曲《牡丹亭》、梅花獎“三合一”之時,那才是一種最圓滿的辯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