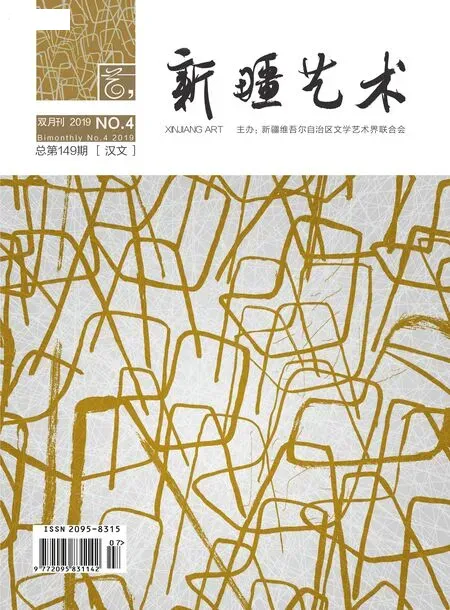張俠:一個詩人與生命對視
□ 李東海
我與張俠的最后一面,應該是在2006年8月昌吉州文聯舉辦的“奇臺半截溝筆會”結束的早上。我和張俠、陳漠等早晨六點的樣子就下山趕到“新絲路網站博客開通儀式”的現場。我們一起吃了早飯,參加完活動就分手了,沒想到這就是訣別。在我離開新疆送女兒上大學的路上,朋友打來電話說:張俠病逝了!我的腦子當時一片空白。我們剛剛分手也就不到十天啊。
張俠曾是昌吉文學的名片,是優秀詩人。他對詩歌的熱情、執著,一直令新疆的文學寫作者欽佩。他曾與陳友勝創辦了新疆民間詩報——《博格達詩報》,后又在網絡上“拍磚”、“殺伐”,忙得不亦樂乎。他的詩歌,至今仍被很多人談論和傳頌。我至今都記得他拿著詩集——《與生命對視》到我辦公室的情景。
張俠的詩歌,可以說是新疆詩壇近三十年來很重要的詩歌作品。無論在詩歌藝術,還是在思想深度上,都是新疆詩歌的上品之作。張俠出版有四本詩集,今天,我就他的《與生命對視》這本詩集里的作品,做一淺顯的解讀。

詩人張俠
張俠在詩集《與生命對視》的后記中寫到:“我寫這些詩的過程,是我的心態從躁動到平靜的過程。1995年11月,我觸摸了死神的手指。死神的手冰冷而滑膩,我們互相對視,死神的背后是黑暗的深淵。”我在讀他這本詩集時,內心不斷地產生震撼和痙攣,我感到,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詩集,這是一個詩人在向世界的最后告白:赤誠而犀利。俗話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在詩集《與生命對視》里,第一首詩就是《空杯》,詩的后半部分這樣寫到:
日子醉倒在你的掌心
今天和明天
誰將注滿下一杯苦酒
等待充盈的日子
你和我一樣虛弱
時光的潮水退盡
我們都會從一個失衡的空間跌落
這是對人生的忠告,還是自言自語的警示?人生一世,艱難困苦,但最后的酒杯,空空如也。雖然“日子醉倒在你的掌心”,但“時光的潮水退盡”,一切都歸于寂靜。誰是時間的主人?“誰將注滿下一杯苦酒”?生生不息的我們,為了“等待充盈的日子”,孜孜以求,奮力拼搏。可最后的我們,“都會從一個失衡的空間跌落”。張俠曾是一名軍人,對于人生是不服輸的。但在病魔的長期折磨下,他不能不深深地嘆息!但他仍像位歌者,劍指長空,引吭高歌:
那個歌者是誰
胸前的彈洞血流如注
一面悲憤的琵琶
淚流滿面
歌者兀立高處
以一把長劍的姿勢
指向天空
鐵質的歌聲
在劍鋒上震顫
——《歌者》
這是張俠寫的自傳,也是他生前寫給自己的墓志銘。他不僅在為自己立傳,也在為自己立言。一個詩人,就是時代的歌者。歌唱生命和自由,而不是歌唱上帝和救世主。就如《國際歌》中唱到:“從來就沒有神仙皇帝,也不靠救世主。要實現人類的解放,全靠我們自己。”當張俠長眠于青山后,我才看到他獨立寒秋,劍指長空“鐵質的歌聲/在劍鋒上震顫”的身影。現在想起張俠,很多人都感嘆他的仗義豪情。張俠的故事,常常被新疆詩人傳為美談。我們不僅看到了他劍指長空的豪氣,也看到了他“一面悲憤的琵琶/淚流滿面”的悲情。張俠很像寫《老人與海》的美國小說家海明威,可以被命運打倒,但不會屈服。他在寫《與生命對視》這本詩的時候,已經與死亡對視了十年。一個堅強的詩人,像戰場上的英雄。在病床上的時候,他就給自己的小女兒寫下遺詩《病中示小女》,在詩中他說到:
我最后的軀體
將鋪展成道路
我會讓每一棵樹木
都成為路標
讓你們乳香的腳印
從我的心口啟程
我不敢想象,一個重病中的詩人,在與死亡對視的時候,還會寫下如此美麗的詩行!張俠的詩,既有豪氣又有柔情,這就是《與生命對視》被新疆詩人反復提起和閱讀的原因。他寫過一首看似清淡,但讀起厚重的小詩《風吹過林子》:
下午六時
風吹過林子
我聽見一只塤
在空中嗚咽
所有的樹木
垂下頭顱
一個女人
在一瞬間蒼老
青春枯落
隨風飄零
下午六時
一只塤
在我生命中低鳴
這是生命之詩,是繆斯之言,像西川的《起風》,隨意而深刻。中國詩家很早就從《詩經》中總結出“賦、比、興”的藝術手法:賦者,鋪陳其事直言之也;比者,以此物比彼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詩人張俠在這首詩里,要向我們說些什么呢?他要向我們說:他的生命已到了最后的時刻,像悲鳴的塤聲;人人都會有這樣的時刻,誰也抵不過時間。一陣風過,所有的樹木都低下了頭顱;一個瞬間,一個女人就蒼老枯萎。他在《與生命對視》的后記里這樣說過:“死神讓我不僅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也讓我領悟到生命的意義和生命的寶貴。”由此,我們才能理解“生命不息,奮斗不止”這句話的意義。
張俠活的時候,還真是個多情的男人,寫下過許多情詩。在這些情詩里,我們足以看出他對女人的細膩和深情,也可以看到他詩歌的才華和激情。譬如《用心寫字的女人》:
今晚,立在窗前
想看看月亮
一片云熄滅了
我心中的燈盞
我回到案頭

作者與詩人張俠
將自己變成一只
茫然的鼠標
一次又一次點擊
那個永遠也打不開的網頁
城市的那頭
一個用心寫字的女人
用月亮的光澤
鍍亮了靈魂
這個夜晚最動人的傳說
是一個如月的女人
一個用心寫字的女人,是一個如月的女人。一個如月的女人,用月亮的光澤,鍍亮了詩人的靈魂。所以即便一片云熄滅了詩人心中的燈盞,可是城市的那邊,一個用心寫字的女人,又用如月的目光點亮了詩人靈魂的燈盞。詩人為情所動,為情所活。詩人張俠是了解寫詩的女子的,他的精神常在女子的靈魂里來回穿梭。無論是情詩的傳遞,還是網絡的神聊,他都樂此不疲。然而在他失落低沉的夜晚,當他“花間獨飲,在酒杯中斟滿孤獨”的時候,他也看到:
城市的那頭/那扇不眠的窗口/一個女人用文字釀酒/灌醉自己/用虛幻的愛情/焚燒寂寞
——《一個女人用文字釀酒》
張俠的孤獨,似乎不是他一個人的孤獨;城市那頭用文字釀酒的女子的寂寞,似乎也不是她一人的寂寞。在中國城市化的過程中,網絡、手機、汽車、飛機,似乎并沒有增強人們的親密感,反而讓人們日益陌生化,人情的冷淡更加劇了人們的孤獨和寂寞感。
冰封的西部/一個盛滿痛苦的巨大傷口/午夜的寒流/破門而入/鋒利的冰刃/沿我的骨頭襲來/逼近心臟/愛情與火/都在日歷上冷卻/而一支枯萎的玫瑰/仍以無怨無恨的姿態/在我生命里站立
——《冬天懷想愛情》
張俠在情詩中,像自由翱翔的雄鷹,生機勃勃。語言的張力,像鷹的喙,準確而具有穿透力。所以哪個女子不為他所動呢?
你躺在一本陳舊的書里/讓無聊的情節/填充一個個空虛的日子/我口銜帶毒的玫瑰/用一匹桀驁野馬的熱血/寫滿陽光的信箋/沿著你生命的季節/彈鋏而歌/我劍鋒上勃動的熱情/會吻干你風中凝望的淚眼
——《太陽的語言》
張俠堅守的愛,仍在內心深處生長和開花。“午夜的寒流/破門而入,/鋒利的冰刃”“ 逼近心臟”,可“一支枯萎的玫瑰”依然在我的生命里亭亭玉立。張俠雖然剛剛活過五十,但他的生命像燃燒的火焰,在夜空里高蹈。他本人就像一首激蕩的詩歌。張俠的情詩越走越深,越寫越隱秘和大膽。在這個方面,他已不弱于尹麗川和沈浩波:
那個夜晚,我以海盜的方式/洗劫了你的靈魂/你仰臥在水面,讓自己在浪頭上顛簸/我沒有聽見你呼救的聲音/你滑過黑暗的玉手剝落恥辱/為一支罪惡的槍口導航/這場突襲沒有預謀/我最初想用一場溫柔想新雨/去滋潤寂寞的空谷/讓青藤一般的句子爬滿你的生命/我沒有想到我依然是一座火山/地心的巖漿依然燃燒/我沒有更好的選擇/一只狼在我的血液嘶叫/我撕下面具的那一刻/我才發現我正是在伊甸園的善惡樹下/我就是那個迷失本性的亞當
——《撕下面具的那一刻》
在新疆,我沒有見過詩歌在寫情愛上達到這種程度的。能把詩歌寫到這種精致唯美的水平,足見張俠的詩歌功力,這還真是在與生命對視。張俠寫到這種水準的詩歌不止一首,他的那首《一支歸隱的獵槍》和《液化的月光》,也不亞于《撕下面具的那一刻》,例如:
一張床 粉紅色的
鋪展在歲月的臀部
激情的肉搏
狂飲巫山的云雨
戰爭的車輪將日子
碾成一張成年的獸皮
愛情在消瘦中沉淪
一點冷火照亮骨雕的風景
床在時間里流動
在秋天的枯草中拋錨
春天的被褥已經腐爛
淺紅的睡衣一身疲憊
筋肉蓬松的歲月
一個獵手痛苦地下崗
——《一支歸隱的獵槍》
在這首詩里,張俠用一系列指示性的詞來暗示他的表達:床、臀部、獸皮、睡衣等將愛與欲望糾纏在一起,愛欲的激蕩與燃燒,在張俠的詩里一幕幕呈現。美國法蘭克福學派的哲學家赫伯特·馬爾庫塞在他的《愛欲與文明》里探討的哲學問題,在張俠的詩里被表達和解讀。馬爾庫塞說:“非壓抑性生存方式旨在表明,向現階段文明有可能達到的新階段過渡意味著,使傳統文化顛倒過來,不論物質上的還是精神上的,就要解放迄今為止一直受到禁忌和壓抑的本能需要及其滿足。”再看他《液化的月光》里的一段描寫:
在八月,我/吐出的每一個詞/都將你灼傷/八月的火焰/一道刻有我姓氏的刀鋒/割開你裹緊的孤獨/讓一滴鮮血/綻放成艷麗的花朵/囹圄在月中的女人/看不見鋒刃/銳利了我的目光/我刺破你的那一刻/那些遺忘的詞語/會在你傷口上成熟
張俠的八月是艷麗成花的八月。他要讓他姓氏的刀鋒,割開她裹緊的孤獨,打造她成熟的詞語。張俠在愛上充滿自信和膽量,也在不斷剖析自己的靈魂。張俠在詩歌寫作上對自己要求很嚴,他眼觀中國各路詩歌豪杰,又對新疆詩歌悉心注視,他滿腦子都是詩歌。最后,他感到自己的身體已經支撐不住,時日不多,在《病房詩抄》里,他把自己比作“一部廢棄的機器/每一個部件都已銹蝕”,直至最后寫下了向生命訣別式的詩歌《與生命對視》,這也像他為自己寫的墓志銘。他說:“這一刻,我站在展開的稿紙上/把日子拆卸成詞/然后拼裝成句子/去填充生命的空格”。他在做最后的努力,他抓緊每一天的時間,寫最后的詩歌。他多想留下更多的自己最滿意的詩啊!他說:“我以夕陽的方式/和生命對視”,太慘烈了,像個即將英勇就義的戰士:
如水的日子/從我身后流走/我聽見生命被蠶食的聲音/這聲音細微而恐懼/我們從母腹出發/穿過生命的四季最終會抵達那塊黑色的墓地
——《與生命對視》
張俠走了,走得清醒。但他走得太早!他活著的時候,是臺高度運轉的機器,高強度的運轉,讓他這臺機器早早地損毀。可他給我們留下的詩歌卻隨著時間的打磨日益閃亮。他在新疆詩歌史上,是一顆亮麗的星。詩人劉貴高說:“他的詩歌散發著燧石一般的神靈之光,使我們感到沉靜的思索會成為一種精神體系,浸潤人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