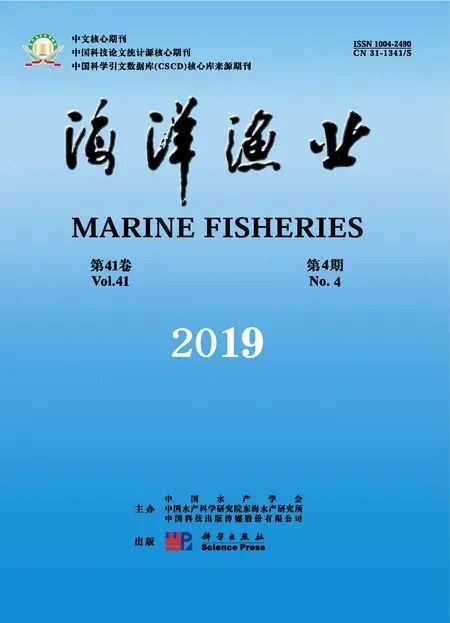三沙灣夏季大型底棲動物群落結構及其和水產養殖活動關系
王 楠,紀煒煒,付 婧,周 進
(1.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東海水產研究所,上海 200090;2.上海海洋大學水產與生命學院,上海 201306)
大型底棲動物是海洋生態系統中最為重要的生物類群之一,其具有較高的物種多樣性、較強的次級生產能力和較為理想的環境指示功能。在中國近岸水域,針對此類群已有較多研究,內容涵蓋種群、群落和生態系統等多個層次。其中,群落研究仍是目前底棲生物研究中的重要內容之一,本研究的區域三沙灣也是如此,針對此水域內的底棲群落結構已有多篇研究[1-9]。因底棲生態學研究中常用的抽樣調查方法特點所限,基于有限樣本的群落結構描述和實際群落組成之間存在一定差距,因此針對三沙灣水域底棲群落結構的進一步研究仍有較為重要的學術意義。
本研究區域三沙灣是我國東海區最為典型的水產養殖海灣之一,主要網箱養殖大黃魚(Pseudosciaena crocea),是我國養殖產量最大的單品種海水魚類。近年來,三沙灣大黃魚養殖產量約占全國的70%[10]。網箱養殖引發養殖衍生有機物(aquaculture-derived organic matter,AOM)沉降,其在沉積物環境中的過度積累可通過營養關系影響底棲生物群落,該假設在國內外均已被證實[11-15]。同時,區域內存在的貝類養殖也已被證明可能影響底棲群落或環境[16-17]。然而,養殖活動對于底棲生物群落的影響受養殖強度和區域水文動力、沉積物特性等自然地理狀況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影響,故已有的針對不同海灣的研究結果之間存在差異。目前對于三沙灣內水產養殖活動對底棲生態環境效應的認識尚不全面,已有相關研究多通過對比分析不同類型水域(養殖和非養殖以及不同養殖類型)內群落時間變化趨勢的差異[6,8],部分關于群落空間差異的分析結論通常基于較為有限的采樣站位數據[4,8],故基于較大空間范圍和較多采樣站位數據的空間差異研究亟待補充。
本研究根據2016年夏季在三沙灣水域內大面積采樣的生物群落和環境因子數據,描述區域內大型底棲動物群落結構特征,探究群落和典型環境因子的相關性,揭示典型群落參數在魚類網箱、海帶吊繩、鮑魚筏式養殖水域以及自然水域共4種不同類型區域間的差異性,以期在描述區域群落結構現狀的基礎上,揭示水產養殖活動對于底棲生物群落的影響。
1 材料與方法
1.1 三沙灣養殖狀況
三沙灣水產養殖活動始于20世紀80年代,伴隨大黃魚人工養殖的成功,90年代開始海灣內網箱養殖規模迅速增加。2017年三沙灣大黃魚網箱養殖產量已達1.47×105t[10]。同時,該水域內海帶(Laminaria japonica)、龍須菜(Gracilaria lemaneiformis)和鮑魚(Haliotis discus hannai)的養殖產量也維持在較高水平,2014年三者濕重產量分別為1.3×105t、1.9×104t和 1.6×105t。大黃魚養殖方式主要為標準網箱養殖(尺寸:3 m×3 m×4 m),網箱遍布海灣各區。網箱養殖周期為1—2年,幼魚通常在4—5月和10—12月期間繁育,培養至體長10 cm后按照1500尾/網箱密度進行養殖,約8—13個月后長至商品魚尺寸后出售。養殖餌料主要來源于我國近海捕獲的小型雜魚,通常包括鳀(Engraulis japonicus)、沙丁魚(Sardine pilchardus)、龍頭魚(Harpadon nehereus)和帶魚(Trichiurus lepturus)等。海帶和龍須菜采用吊繩方式養殖,遍布海灣中部及內灣各區,12月至次年5月為海帶養殖期,6—9月為龍須菜養殖期。鮑魚使用筏式養殖,僅限于灣口區小范圍水域,主要餌料為灣內養殖的海帶和龍須菜。
1.2 樣品采集時間和站位
本研究于2016年8月在三沙灣采集大型底棲動物樣品及同步環境數據,共設置4種類型共41個采樣站位(圖1)。距離養殖設施5 m范圍以內區域定義為養殖水域,其內共包括23個大黃魚網箱養殖站位(6、7、9~12、16~24、28~30、32、36、38~40號)、9個海藻吊繩養殖站位(2、3、5、13、27、31、33、37、41號)和 2個鮑魚筏式養殖站位(34、35號)。距離養殖設施600 m以外區域為自然水域[18],水域內共包括7個采樣站位(1、4、8、14、15、25、26號)。
1.3 底棲生物采集及處理方法
使用面積為0.04 m2箱式采泥器采集底泥樣品,每站成功取樣2次合并為1個樣品。使用最小孔徑為0.50 mm篩網沖洗樣品,所獲大型底棲生物樣品使用75%酒精現場固定并保存。固定樣品在實驗室內使用1%虎紅(rose bengal)溶液染色,靜置24 h后進行粗分。粗分后樣品進行分類學鑒定、個體計數及稱重(濕重),計算豐度(個·m-2)和生物量(g·m-2)。具體操作方法參考《海洋調查規范》(GB/T 12763.6-2007)相關要求進行。
1.4 環境因子數據采集及檢測
溫度、鹽度、pH和溶解氧等水文環境因子使用多功能水質參數儀(YSIEX02)現場獲取。沉積物環境因子重點選擇與水產養殖活動關系較為密切的要素,包括 δ15N、δ13C、C/N比、總氮、總有機碳、總磷、含水率、硫化物和粉砂-黏粒含量。環境因子和生物樣品同步采集,環境因子檢測方法參照唐盟[19]相關敘述。
1.5 參數計算
分析三沙灣底棲動物群落結構與環境因子關系時,本文選取最為典型的6種群落參數:物種數(S)、豐度(N)、生物量(B)、Shannon-Wiener多樣性指數 (H′)、Pielou均勻度指數 (J′)、Margalef豐富度指數(d)。
1.5.1 Shannon-Wiener多樣性指數(H′)
各采樣站位 Shannon-Wiener多樣性指數(H′)公式為:

式中,Pi為第i種的個數與該樣方總個數之比值,S為樣方種數。

圖1 三沙灣2016年8月航次大型底棲動物和環境因子采樣站位圖Fig.1 M ap of the study area
1.5.2 Margalef豐富度指數(d)和Pielou均勻度指數(J′)
各采樣站位 Margalef豐富度指數(d)和Pielou均勻度指數(J′)公式分別為:

式中,S為種類數,N為總豐度,H′為 Shannon-Wiener多樣性指數。
1.6 數據處理
本文選取7種最為典型的底棲群落參數進行研究,包括物種數(S)、豐度(N)和生物量(B)、多樣性指數 (H′)、Pielou均 勻度 指數 (J′)、Margalef豐富度指數(d)和單純度指數(C),各參數通過Primer 6.0軟件計算獲取。分析群落參數在不同類型水域之間的差異時,首先通過Shapiro-Wilk方法檢驗各參數是否符合正態分布,再通過Bartlett檢驗進行數據方差齊性檢驗。結果表明本研究計算出的7種群落參數大多數數據組不能同時滿足正態分布和方差齊性的要求。此外,由于鮑魚養殖區樣本有限,僅包括2個采樣站位,故本研究使用非參數Kruskal-Wallis方法檢驗群落參數的組間差異,顯著性水平設為P=0.05。同時,利用Behrens-Fisher方法進行兩兩比較,兩兩比較的顯著性檢驗進行Bonferroni校正。此部分計算通過R軟件完成。
為分析三沙灣夏季底棲動物的群落相似性,文章根據豐度數據對41個采樣站位的底棲群落進行聚類分析(cluster analysis)和非度量多維尺度排序分析(nMDS),此分析利用Primer 6.0軟件完成。因Bray-Curtis similarity模型計算樣方之間的半幾何距離可避免樣品間相似性受到樣品中均不存在物種的影響,比較符合本研究數據的特性,故本研究使用此種模型方法構建樣方相似性矩陣。同時對于原始豐度數據進行平方根轉化,以對少數優勢種(大個體種)或多數稀有種(小個體種)進行平衡權重。聚類計算時,采用層次分析法中較為溫和的average-linkage算法,以避免出現基于過度相似性或非相似性的聚類結果。
研究三沙灣底棲動物群落結構和環境因子關系時,首先對三沙灣水域群落數據進行除趨勢對應分析 (deternded correspondence analysis,DCA),以確定群落數據的分布類型(單峰型或線性分布)。在本研究中,DCA分析結果顯示4個軸重最大梯度超過4,因此選擇基于單峰模型的典范對應分析方法(canonical correspondence analysis,CCA)。上述分析通過Canoco 4.5軟件完成。
2 結果與分析
2.1 群落結構現狀
2016年8月三沙灣海域采樣共鑒定大型底棲動物6門75種(表1,附表1)。其中,環節動物物種數占據絕對優勢,共計48種,占總物種數64.00%;其他門類物種數按從高到低順序分別為節肢動物、軟體動物、棘皮動物、紐形動物和腔腸動物。
三沙灣大型底棲動物的豐度和生物量均值分別為371.34個·m-2和21.82 g·m-2(表1)。環節動物對于底棲生物豐度和生物量的貢獻量均為最大,類群豐度和生物量均值分別為292.68個·m-2(占底棲生物總豐度78.82%)和13.06 g·m-2(59.87%)。豐度和生物量在站位間存在較大差異,豐度最大值出現在網箱養殖站位第17號站,為1 075.00個·m-2;最小值出現在海帶養殖站位第13號站,為25.00個·m-2。生物量最大值出現在網箱養殖站位第9號站,為128.23 g·m-2,最小值出現在海帶養殖站位第41號站,為 0.15 g·m-2。
三沙灣大型底棲動物群落多樣性(H′)均值為2.56(變化范圍0.00~3.51),單純度(C)均值為0.26(0.10~1.00),均勻度(J′)均值為 0.83(0.00~0.97),豐富度(d)均值為0.97(0.16~1.75)。
2.2 群落優勢物種的空間分布
2016年8月三沙灣底棲群落中平均豐度位居前6位的物種皆為環節動物(表2),按數量從高到低順序分別為絲異須蟲(Heteromastus filiformis)、不倒翁蟲(Sternaspis scutata)、歐努菲蟲屬一種(Onuphis sp.)、索沙蠶科未定種(Lumbrineridae)、角海蛹(Ophelina acuminata)和絲鰓蟲屬一種(Cirratulus sp.)。此外,軟體動物胡桃蛤屬一種(Nucula sp.)和焦河籃蛤(Potamocorbula ustulata)以及棘皮動物倍棘蛇尾屬一種(Amphioplus sp.)在群落中也較具數量優勢。數量優勢物種通常在鮑魚筏式養殖和網箱養殖水域中形成較高種群數量。

表1 2016年夏季三沙灣大型底棲動物群落組成Tab.1 Species com position ofmacrobenthic community in Sansha Bay in summer,2016

表2 2016年夏季三沙灣數量優勢大型底棲動物棲息密度的空間分布(豐度值位居前10位物種)Tab.2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abundance of top ten numerical dom inant macrobenthos in Sansha Bay in summer,2016 (個·m-2)
2.3 典型群落參數在不同類型養殖水域之間的差異
Kruskal-Wallis檢驗結果表明,本文研究的7個群落參數在魚類網箱養殖水域、海藻吊繩養殖水域、鮑魚筏式養殖水域和無養殖水域之間均無顯著差異(P>0.05,圖2)。后續兩兩比較顯示顯著性差異僅出現1次,即群落多樣性指數(H′)在魚類網箱養殖水域和無養殖水域之間存在顯著差異。
2.4 三沙灣底棲動物群落結構的聚類分析
基于豐度數據的聚類結果顯示,三沙灣大型底棲動物群落結構的空間異質性較高。按照30%相似性水平,區域內底棲生物可劃分成11個群落(圖3)。在同等類型的水體中,不同采樣站位內的群落結構也呈現出較大差異,例如無養殖水域、海藻吊繩養殖等水域的站位均體現出此種空間差異。

圖2 2016年夏季三沙灣大型底棲動物群落參數在不同類型水域間的差異Fig.2 Differences of indices ofmacrobenthic community between different waters in Sansha Bay in summer,2016
nMDS分析結果顯示壓力系數為0.19。在二維排序空間中,采樣站位之間的位置較為分散(圖4)。在各種類型的采樣站位中,無養殖水域和海藻吊繩養殖水域站位之間空間差異性較強。
2.5 群落結構和環境因子的相關性分析
物種豐度值的除趨勢對應分析(DCA)結果顯示最長軸長度為6.330,故采用典范對應分析方法(CCA)進行排序,結果顯示前兩軸特征值分別為0.411和0.307,種類和環境因子排序軸的相關系數高達0.974和0.913,物種和環境關系累計百分比顯示前兩軸環境因子對物種分布特征的解釋量可達71.8%,排序軸較好地反映底棲生物群落與環境因子之間的關系。

圖3 2016年夏季三沙灣大型底棲動物群落的聚類分析Fig.3 Cluster analysis ofmacrobenthic community from different samp ling stations in Sansha Bay based on abundance data in summer,2016

圖4 2016年夏季三沙灣大型底棲動物群落nMDS分析Fig.4 The nMDS analysis ofmacrobenthic community in Sansha Bay in summer,2016
水體溫度、鹽度、水深和沉積物含水率、粉砂-黏粒含量、總氮和總有機碳等環境變量軸長較長,顯示三沙灣內此類環境因子對于群落的影響較大(圖5)。沉積物含水率、粉砂-黏粒含量、總氮和總有機碳等環境變量之間夾角較小,顯示此類因子之間具有較強的正相關關系。大部分數量優勢物種和水深以及沉積物總氮、總磷、總有機碳和含水率呈現較為顯著的正相關關系。數量絕對優勢物種(如1、2、4、5號物種等)多位于排序軸的中央位置。

圖5 2016年夏季三沙灣大型底棲動物與環境因子典型對應分析排序圖Fig.5 Ordination diagrams of species(abundance data)and typical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in Sansha Bay based on canonical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in summer,2016
3 討論
3.1 三沙灣大型底棲動物群落結構特征
根據2016年8月的采集樣品,三沙灣共出現大型底棲動物75種,涵蓋環節動物、節肢動物、軟體動物和棘皮動物等淺海水域習見大型底棲動物類群。其中,環節動物物種數占群落物種總數達60%,類群數量優勢明顯;節肢動物和軟體動物次之,其他門類較少。此種群落組成特征與中國近海其他水域內的底棲群落相似,在溫帶和亞熱帶軟泥底質的生境中,環節動物物種數量在底棲樣品中較具優勢[20]。三沙灣大型底棲動物的豐度和生物量均值分別為371.34個·m-2和21.82 g·m-2,此種數量水平和東海近海水域內的其他相關報道數據相似[21],符合暖溫帶淺水水域底棲生物多樣性的典型特征。
盡管三沙灣底棲生物在物種數、豐度和生物量等數量特征方面體現出與鄰近海域內群落的相似性,但區域內群落具有其獨特特征,例如三沙灣的底棲群落物種組成特征。以同屬東海區、且同為養殖海灣的象山港和樂清灣為例,象山港底棲群落優勢物種為異足索沙蠶(Lumbrineris heteropoda)、長吻沙蠶(Glycera chirori)、多鰓齒吻沙蠶(Nephtys polybranchia)和不倒翁蟲等[22],樂清灣群落優勢種主要為西格織紋螺(Nassarius siquinjorensis)、白沙箸(Virgularia gustaviana)、不倒翁蟲、小頭蟲(Capitella capitata)、棘刺錨參(Protankyra bidentata)等[15],三沙灣內最具數量優勢的物種絲異須蟲在上述海灣不具數量優勢,另一數量優勢物種角海蛹在上述海灣則未有分布。此種相鄰區域內底棲群落組成呈現顯著差異的現象說明大型底棲動物是海洋生態系統中物種多樣性水平較高的生態類群之一,且底棲群落形成機制較為復雜。同時,本文的聚類分析結論顯示,三沙灣大型底棲動物群落結構空間異質性較高。即使按較低的30%相似性標準,水域內底棲生物仍可被劃分為十余個群落。聚類分析重點旨在組群劃分而非連續尺度上樣品間關系的呈現,此方法比較適用于環境條件空間異質性較高、樣品可被明確劃分成組的情況。相比之下,排序方法可更好地表達生物群落對于比較連續的環境梯度的響應特點。nMDS標序是近年來底棲生態學中較為常用的方法之一,即按照樣品間的非相似性等級順序將樣品排放在二維標序圖中,同時引入壓力系數以反映相似性等級與標序圖中相應的距離等級的不一致程度。本文nMDS分析中壓力系數為0.19,說明相關排序結果基本可信。本文的nMDS分析和聚類分析結論相似,均顯示采樣站位之間的相似性較低。
三沙灣內如此高的群落結構空間異質性較為特殊,可能源于其存在的多重外源脅迫。首先,區域內存在魚類網箱、鮑魚筏式和海藻吊繩等多種水產養殖方式,不同生產方式對于底棲生境的影響可能存在顯著差異。同時,在水產養殖活動影響之外,海灣內頻繁的船只航行、海洋工程建設等人類活動也可能對底棲生境產生擾動,此類脅迫容易造成底棲生境的不穩定性,從而影響區域內的底棲群落。例如無養殖水域4號站位豐度僅為75個·m-2,此站位較淺的水體(1.5 m)導致區域內底棲群落易受船只航行的影響。此站位中的寡鰓齒吻沙蠶(Nephtys oligobranchia)和雙鰓內卷齒蠶(Aglaophamus dibranchis)在三沙灣其他站位中出現頻率極低,顯示該站位獨特的物種組成。寡鰓齒吻沙蠶和雙鰓內卷齒蠶同屬多毛綱齒吻沙蠶科,此科物種對于物理擾動具有較強的適應能力,例如在長江口洋山深水港碼頭建設工程水域多毛類物種多樣性極低,但此科物種仍可生存[23]。
3.2 三沙灣底棲動物群落對于水產養殖活動的響應
本研究結果顯示三沙灣水域大型底棲動物物種數、豐度及生物量在采樣站位之間變化范圍較大,如豐度和生物量高值可數百倍于低值(兩者變化范圍分別為25.00~1 075.00個·m-2和0.15~128.22 g·m-2)。然而,站位之間的差異并非由水域類型的差別決定。例如三沙灣底棲生物豐度在網箱養殖、海帶養殖、鮑魚養殖和無養殖水域均值分別為430.98個·m-2、367.19個·m-2、437.50個·m-2和 223.21個·m-2,4種類型水域間無顯著差異,兩兩比較結果顯示任意兩種水域之間也無統計學差異。在三沙灣內,豐度最大值出現在網箱養殖站位第17號站,可達1 075.00個·m-2,此種高豐度并非由少數機會物種所致,而是由于站位內高數量的絲異須蟲、不倒翁蟲、歐努菲蟲屬和索沙蠶科物種共同作用而成。同時,此站位Shannon-Wiener多樣性指數為2.82,印證了站位內底棲生物維持在較高的物種多樣性水平。生物量最高值也出現在網箱養殖站位(第9號站位),站位內的甲殼動物和棘皮動物對于總生物量貢獻較大。
KAPSAR等[24]對餌料的研究表明,網箱養殖餌料的3/4總氮和總磷將排入水域,其中65%總氮和10%總磷沉于海底。海灣內的鮑魚和海藻養殖則無需投入動物性蛋白。根據PEARSON等[25]提出的經典底棲群落演替理論,三沙灣高強度網箱養殖活動引發AOM的過量沉降應會造成區域內底棲群落呈現較低的生物量和豐度,并引發區域內甲殼動物和棘皮動物等類群數量較少、環節動物多毛類動物數量較多等狀況。然而,本研究結果表明三沙灣網箱養殖并未對底棲群落產生顯著影響。因此,本文結果與之前較為普遍的網箱養殖為高污染養殖方式的認知存在差異。特別是本研究采集的站位中,豐度和生物量的最大值均出現在網箱養殖站位。同時,本研究的聚類結果表明,即使在相同類型的養殖水體中,底棲群落結構也呈現出較大空間差異,例如無養殖水域、海藻養殖等水域內的站位皆是如此。唐盟[19]對三沙灣底棲環境因子的空間分布特征進行研究,結果顯示三沙灣內典型環境因子呈現較為均質性分布的特征,其空間格局并未體現出水域類型之間的差異性,因此本研究揭示的群落參數空間分布特點與環境因子相符。彭廣海等[9]利用AMBI、M-AMBI和Shannon-Wiener多樣性指數等方法評價水產養殖對于底棲環境影響,結果表明網箱養殖活動并未對底棲環境造成明顯的負面影響,本文結果與之一致。
筆者部分未發表的數據表明,三沙灣內氮、磷的主要來源包括水產養殖和來自毗鄰陸域的農業面源污染和畜禽養殖排放,水產養殖活動承擔了外源營養物質輸入的主要貢獻量。以2014年數據為例,養殖活動使三沙灣內總氮和總磷分別增加了1.2×104t和2.4×103t。因此,本文認為區域內網箱養殖的環境影響客觀存在,且維持在較高強度。但因三沙灣內良好的水動力條件和復合養殖等客觀條件,擾動被有效減緩,從而未對底棲群落產生顯著影響。
一些研究表明較高強度水產養殖活動對于底棲群落未產生顯著影響,如象山港網箱養殖區底棲生物物種數、豐度和生物量均高于自然水域,顯示出AOM對于底棲生物多樣性的支持功能[26];黃河口較大規模的海水池塘養殖對于鄰近區域的影響也限于較小范圍和較低程度[27]。然而,也有研究顯示,網箱養殖對于底棲群落會產生顯著不利影響,如大亞灣大鵬澳內的網箱養殖活動降低了底棲動物的生物量和豐度[14];樂清灣養殖和非養殖區內群落結構差異顯著[15]。此種差異性結果的出現表明底棲群落和養殖活動脅迫之間的關系較為復雜,養殖對于群落的影響程度受養殖強度和區域水文動力、沉積物特性等自然地理狀況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影響。
海藻養殖是三沙灣內重要的生產方式之一。本文和象山港的相關研究[22]均表明,部分海藻養殖水域內底棲群落較為退化,顯示此種養殖方式對于底棲群落可能產生潛在的負面影響。目前,在國內海藻養殖因其具有消除富營養化的作用,因而多被認為具有積極的生態作用,相關負面的生態效應報道較少。然而,在國外關于海藻養殖引發的負面生態結果已有報道,如在坦桑尼亞沿岸水域,海藻養殖導致底棲生物豐度和生物量降低[28]。因此,本文認為海水藻類大規模養殖對于區域底棲生態環境的影響值得深入研究。
3.3 群落結構和環境因子的相關性
三沙灣內底棲生物和典型環境因子的典范對應分析結果表明,區域內水體溫度、鹽度、水深和沉積物含水率、粉砂-黏粒含量、總氮和總有機碳等環境因子對于群落的影響較大(圖5)。上述環境因子可歸納為兩類,第一類環境因子為底棲生物生境的基本理化因子。底棲生境通常包括底層水體和沉積物環境兩種類型,水體溫度、鹽度和水深是水體環境中影響底棲群落最為重要的環境因子,溫度和鹽度影響生物基本新陳代謝特征,不同物種在長期演化過程中形成獨特的溫度和鹽度適應性,溫度和鹽度基本決定區域內生物多樣性和區系特點;水深是影響水體水文動力特征的重要因素,可影響水動力交換水平,同時也影響有效光照等關鍵生態條件,通過初級生產途徑進而影響底棲群落特征。沉積物含水率、粉砂-黏粒含量為沉積物環境的基本物理特征,影響沉積物中營養物質和污染物質的賦存,從而影響底棲生物群落。第二類環境因子作用于底棲生物的營養功能。例如,總氮和總有機碳的數量特征通常表征生物的食源范圍,是影響生物群落的核心過程[29]。
本研究結果和已有研究結果存異,例如ZHOU[6]研究結果表明,在眾多環境因子中,水體溶解氧含量、沉積物酸性可揮發性硫化物含量、沉積物氧化還原電位和大型底棲動物群落結構之間相關性較強,而沉積物中總氮和總磷與底棲生物群落無顯著相關性。此種區域相同但結果存異的現象表明不同數據來源、不同實驗設計方法對于生物群落和環境因子相關性結論的獲取存在較大的影響。
在自然條件下,各種環境因子之間協同和拮抗作用復雜,使得影響生物群落的關鍵環境因子難以甄別。本文揭示在三沙灣水域非核心環境因子也具有較為重要的生態作用,例如底層水體溶解氧和沉積物酸性可揮發性硫化物含量等。日本國內曾頒布“Law to Ensure Sustainable Aquaculture”,該條例將養殖底層水體溶解氧、沉積物酸性可揮發性硫化物特征和大型底棲動物群落作為判定底棲生境質量的3條標準,三者之間具有較強的相關性[30]。在東海區養殖海灣中,象山港網箱養殖區沉積物中總碳、總磷和總有機質和對照區近似相等,但其內的硫化物含量顯著較高[26]。三沙灣內底層水體溶解氧和沉積物硫化物對群落影響較小的原因應在于此兩種環境因子的分布特點,與日本典型養殖海灣內報道的相關數值相比[11],三沙灣內沉積物硫化物含量較低,而底層水體溶解氧含量較高,同時兩者在海灣內的分布皆較為均勻。
三沙灣內大部分數量優勢物種和水深、沉積物總氮、總磷、總有機碳和含水率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顯示三沙灣內營養物質的累積尚未造成區域的過度營養化,目前有機物質的輸入對于維持區域生物多樣性和種群數量具有積極的支持作用。數量絕對優勢物種(如圖5中的1、2、4、5號物種等)多位于二維排序軸的中央,體現此類物種對于特定種類環境要素的依賴性較弱,同時也說明此類物種具有較為寬廣的生態適應能力。
因采樣條件等客觀因素限制,本研究選取的環境因素雖較為典型,但數量較為有限(共13個環境因子),雖能基本反映養殖活動的脅迫狀況,但未能很好地體現其他外源脅迫的影響程度,例如區域內水上交通、海洋工程建設等人類活動對于底棲環境的擾動作用,此方面研究在后續工作中有待補充。
致謝:日本京都大學橫山壽教授對于本研究實驗方案設計、樣品采集及處理方法制定等工作提供重要指導,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東海水產研究所唐盟和溫州大學彭廣海兩位研究生同學協助野外樣品采集工作,謹致謝忱。

附表1 三沙灣大型底棲動物物種名錄及序號(按優勢度降序排列)Appendix 1 Directories and sequence number ofmacrobenthos species in Sansha Bay(descending sort w ith dom i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