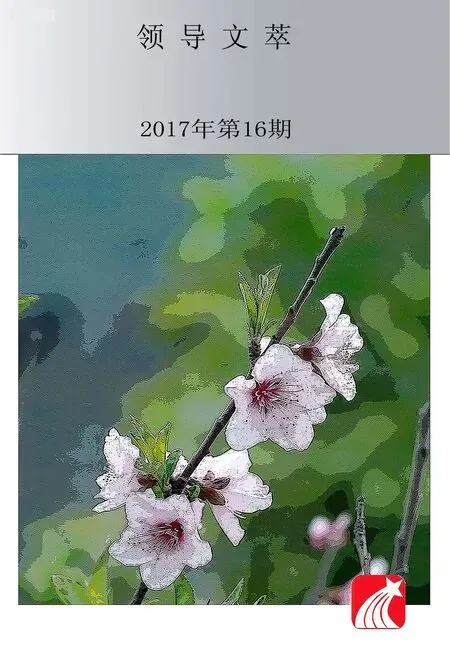曹操為什么不稱帝?
華說
在今日一般民眾的心目中,曹操的形象相當負面,說得好聽一點,是“奸雄”,說得難聽—點,是“奸賊”,總而言之,是一個大奸大惡之徒。這印象的得來,大抵源自于《三國演義》。在這部傳世的著名古典小說中,羅貫中將曹操塑造成為“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的大反派。《三國演義》流傳至今,傳播既廣且久,這形象也隨之深入人心。
這是小說、戲曲中的曹操,與真實的曹操無關。歷史上的曹操雄才偉略,乃“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也。古人云,不朽有三:立德、立功、立言。曹操既“立功”而又“立言”,三者有其二,古往今來能有幾人?不止此也,曹操還寫得一手好字。唐朝張懷瓘在其所著《書斷》中,以“神、妙、能”三品排列歷代書家,曹操躋身章草“妙品”八人之列,足見其草書的水平之高,亦登堂入室矣。
當然,曹操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立功”。東漢末年,天下大亂,群雄并起逐鹿中原,曹操降黃巾,逐袁術,敗張繡,滅呂布,破袁紹,斬袁譚、高干,擊劉表、馬超、韓遂;又降服烏桓、南匈奴、鮮卑,平定外患,一統北方中國。
雄豪并起的漢末,為什么是曹操而不是別人最終在競爭中勝出,將對手一一擊敗,克成洪業?建安十五年,曹操發布《讓縣自明本志令》,其中有一段話道出了他為人處世的一個根本原則:“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眾,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己離兵為人所禍也。既為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為也。前朝恩封三子為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為榮,欲以為外援為萬安計。”曹操說得清楚,“慕虛名而處實禍”的事情,他是不干的。
是的,不慕虛名,注重實際,是曹操最大的性格特點。愚以為,正是這一點,讓曹操對自己以及競爭對手面對的局限條件看得清楚,審時度勢地制定戰略戰術,進而屢戰屢勝,最終在群雄中突圍而出,一覽眾山小。
且以他最大的競爭對手袁紹為例類比之。《世說新語》記載了青年曹操和袁紹的兩則逸事,其一云:“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為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遑迫自擲出,遂以俱免。”其二云:“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劍擲魏武,少下,不著。魏武揆之,其后來必高,因帖臥床上。劍至果高。”從這兩件小事上看,曹操的機警和權謀遠在袁紹之上。在某種意義上說,這似乎是兩人之間未來決戰的一個暗示。
曹操與袁紹的生死決戰,是在官渡。曹操與袁紹的帳下,可謂謀士如云,曹操這邊,以荀彧、荀攸、賈詡為代表,袁紹那里,則以田豐、沮授為首。那可都是一等一的高人,在戰爭期間各為其主,頻出妙計。面對著這些計謀,兩軍主帥的表現可謂去之天壤。曹操善擇良策:用荀攸計,斬顏良誅文丑,火燒袁紹運糧車;認為荀彧分析正確,于是放棄返回許昌的念頭而堅守官渡;甚至,他還用了從袁紹陣營叛變過來的許攸的計策,偷襲袁紹部隊的屯糧之所烏巢,袁軍因此而大敗。反觀袁紹,對田豐、沮授所籌劃的計謀,“不許”,“不聽”,“不從”,“復不從”……其剛愎自用如此!
官渡之戰的尾聲,有一個細節耐人尋味。“公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曹操在收繳的袁紹的信件中,發現了一些許昌下屬和軍中人士與袁紹往來的信件,這是通敵的證據,但是,曹操全部把它們燒了,并沒有追究當事人的責任。曹操為什么要這么做?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公云:“當紹之強,孤猶不能自保,而況眾人乎!”曹操所說,固然是實情,而又以己推人,有人情味,也彰顯其寬宏大度。然此舉其實亦是出于利害之考量:一則事情已經過去,而袁紹已敗,通敵的危害不復存在;二則天下未平,正是用人之際,將通敵的書信燒掉,足以令當事人感激涕零,死心塌地為其效勞,何樂而不為?換言之,以通敵的書信治罪,有害而無利,將通敵的書信“皆焚之”,有利而無害,何去何從?以曹操“不慕虛名”的做事原則,不言自明矣。
曹操之不慕虛表,講究實際,在選拔人才上表現得最為深著。建安十五年,曹操下了一道《求賢令》,態度鮮明:“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于渭濱者乎?又得無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七年之后的建安二十二年,曹操又下了一道《舉賢勿拘品行令》。
前后兩道令,用人的標準和原則一以貫之:我要的不是道德楷模,而是有治國用兵才能之人。不管其出身如何,品行如何,名聲如何,唯才是舉;只要有治國用兵之術,哪怕是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皆可起用。是的,曹操的人才觀完全是實用主義或者說功利主義的。無他,因為他要的不是虛名,而是成就一番霸業。他看得透徹:“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
自建安元年迎接漢獻帝至許昌起,曹操正式開啟“挾天子以令諸侯”模式,一手把持朝綱,權勢熏天。天下人都知道,朝廷的真正主人,不是漢獻帝,而是曹操。建安二十二年,“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銀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頭戴懸垂有十二根玉串的禮帽,乘坐專門的金銀車,套六馬,配備五色安車、立車各一,合十乘,皆駕四馬。漢獻帝給予曹操的,完全是皇帝的禮儀規格。也就是說,從權力到生活待遇,曹操享受著天子的一切,其實質,就是一位皇帝,所缺的,只不過是一個名號而已。
實際上,在這期間,不斷有人勸他稱帝,其中既有陳群、桓階、夏侯敦這樣的部下,也有他的對手孫權——建安二十四年,“孫權上書稱臣,稱說天命。王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耶!”(《魏略》)然而,終其一生,曹操至死沒有捅破這層窗戶紙,沒有代漢自立為皇帝——此事最終由他的兒子曹丕完成。
曹操為什么不稱帝?? ?
內中的緣由,實際上在將孫權勸他稱帝的書信展示給眾人時已經說了,“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耶!”曹操對局勢看得清楚,雖然自己一統北方中國,但天下未平,東南有孫權,西南則有劉備,兩人皆一時豪杰,是不可小覷的競爭對手。“挾天子以令諸侯”,發動戰爭師出有名,是正義的,他曹操站在政治上和道義上的制高點上。但是,一旦自己稱帝,則一切隨之反轉,孫權、劉備將站到政治上和道義上的制高點上,他們的軍隊將成為“正義之師”,可以借此召喚天下英雄豪杰,而自己則變成了亂臣賊子,不復政治上和道義上的優勢,陷入水深火熱之中。
稱帝與否,要視稱帝帶來的收益和成本而定。曹操的賬本其實是一目了然的:從權力到生活待遇,曹操享受著天子的一切,是一個事實上的皇帝,而所缺少的,只是一個名號。因此,稱帝所能獲得的,也就是這個“虛名”而已,這是稱帝的收益;但其成本——即稱帝帶來的禍害卻是巨大的:將自己陷于亂臣賊子的境地,將政治上和道義上的制高點上拱手奉送給對手。權衡利弊,“慕虛名而處實禍”,收益低而成本高,不得為也。
或曰,曹丕即魏王位后,同樣面臨著東南有孫權,西南有劉備的格局,何以其廢黜漢獻帝自立為皇帝?卻不知曹操、曹丕之輪替,即是一重大局勢轉變也。兩人性格不同,為人處世的原則不同,更為重要的是,曹操于群雄紛爭之中殺將出來,統一北方,武功蓋世,此即其威權所在,足以御群下,有沒有皇帝這個名號不重要。但曹丕沒有這不世功勛,權勢和地位世襲而來,駕馭群臣,有沒有皇帝之名的加持,情形大為不同也。
“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為也。”縱觀曹操一生,此誠為其人生的座右銘也。
(摘自《歷史之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