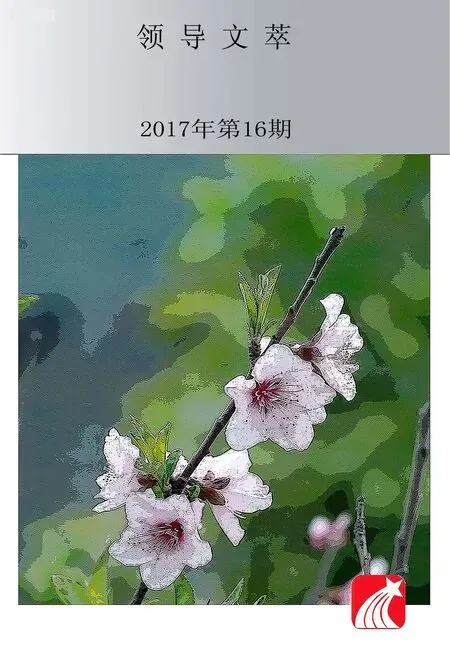周總理和《梁祝》
遠(yuǎn)歌
20世紀(jì)60年代,小提琴協(xié)奏曲《梁祝》問(wèn)世。周恩來(lái)聆聽(tīng)《梁祝》之后,對(duì)這部作品非常欣賞,更使他高興的是,創(chuàng)作演出這部作品的都是新中國(guó)培養(yǎng)的年輕人。這一時(shí)期,周總理經(jīng)常陪同到中國(guó)訪(fǎng)問(wèn)的外國(guó)國(guó)家元首來(lái)上海。在上海,總要安排文藝演出,周總理差不多每次都點(diǎn)名要聽(tīng)《梁祝》。
一次演出后,俞麗拿被邀請(qǐng)參加在錦江俱樂(lè)部舉辦的舞會(huì),周總理也來(lái)了。俞麗拿默默地坐在一個(gè)角落里,面對(duì)著那么多國(guó)家領(lǐng)導(dǎo)人,她既緊張又激動(dòng)。舞會(huì)開(kāi)始后,周總理突然穿過(guò)人群,向俞麗拿走來(lái)。“我能邀請(qǐng)你跳舞嗎?”周總理微笑著,做出一個(gè)邀請(qǐng)的手勢(shì)。“你是俞麗拿,我多次聽(tīng)你拉《梁祝》,很好啊。”周總理看著俞麗拿,目光溫和而慈祥。
“總理,我……我不會(huì)跳舞,會(huì)踩你腳的。”俞麗拿忐忑不安地說(shuō)。“踩腳也沒(méi)關(guān)系嘛,”周總理依然保持著微笑,“你是音樂(lè)家,一學(xué)就會(huì)的,來(lái)吧。”
和著音樂(lè)的節(jié)拍,周總理和俞麗拿在舞池里像散步一樣慢慢走著。他很有興趣地詢(xún)問(wèn)了《梁祝》創(chuàng)作的情況。俞麗拿發(fā)現(xiàn),周總理對(duì)她的情況很熟悉,不僅知道她首演《梁祝》,還知道她們的四重奏在柏林獲獎(jiǎng)。總理說(shuō):“你們的四重奏能在這么大的壓力下獲獎(jiǎng),很不容易。你們辛苦了。”
聽(tīng)到這里,俞麗拿心里一熱,腳步踏錯(cuò)了節(jié)拍,踩到了總理的腳。周總理笑了笑,帶著俞麗拿調(diào)整了腳步。他怕俞麗拿不安,又問(wèn)道:“你的名字,到底是俞麗娜,還是俞麗拿?”
第一張小提琴協(xié)奏曲《梁祝》的唱片,是俞麗拿灌制的,唱片封面上把她的名字錯(cuò)寫(xiě)成“俞麗娜”,周總理也注意到了。在這樣的交流中,俞麗拿覺(jué)得總理就像個(gè)和善的長(zhǎng)輩,緊張和忐忑漸漸消散了。
俞麗拿把心里的苦惱也對(duì)總理說(shuō)了,小提琴在中國(guó)缺乏群眾基礎(chǔ),外國(guó)的曲子工農(nóng)群眾不愛(ài)聽(tīng),不知該怎么辦。總理想了想,笑道:“中國(guó)有那么多民間音樂(lè),可以用小提琴拉。你們年輕人,要敢想敢闖嘛。”
一年后,俞麗拿和她的同學(xué)們?cè)谝黄馂橹芸偫硌莩鲂√崆冽R奏,拉的是中國(guó)《步步高》《四季調(diào)》《花兒與少年》等民間音樂(lè)。演出結(jié)束后,周總理接見(jiàn)了他們,總理一見(jiàn)俞麗拿,就笑著夸獎(jiǎng)道:“你一年前談的問(wèn)題,現(xiàn)在不是找到答案了嗎!你們的演出很好,是一條通向廣大群眾的道路。小提琴在中國(guó)會(huì)有知音的。”俞麗拿沒(méi)有想到,一年前她和總理的談話(huà),總理竟然一直記在心里。
這之后,俞麗拿又有幾次機(jī)會(huì)為周總理演奏《梁祝》。一次,周總理陪一個(gè)外國(guó)國(guó)家元首來(lái)上海,在歡迎宴會(huì)上,俞麗拿又演奏了《梁祝》。演出結(jié)束后,周總理從主桌上站起身,走到一邊,讓工作人員把俞麗拿叫了過(guò)來(lái)。“小俞,和你商量個(gè)事情。”總理的語(yǔ)氣很溫和,但態(tài)度很認(rèn)真,“我覺(jué)得《梁祝》太長(zhǎng)了一點(diǎn),你和兩位作曲家去說(shuō)一下,能不能改得短一些,這樣演奏效果可能會(huì)更好。”俞麗拿愣了一下,一時(shí)不知說(shuō)什么好。她沒(méi)想到周總理會(huì)提這樣的意見(jiàn)。周總理見(jiàn)俞麗拿不吭聲,又說(shuō):“當(dāng)然,這只是我個(gè)人的意見(jiàn),供你們參考。”說(shuō)罷,他又轉(zhuǎn)身回到宴會(huì)席上。
那天晚上回家,俞麗拿心里有點(diǎn)七上八下。當(dāng)時(shí),《梁祝》已經(jīng)廣為流傳,《梁祝》的旋律已經(jīng)深入人心,俞麗拿認(rèn)為《梁祝》是一個(gè)定了型的作品。可是周總理提了這樣的意見(jiàn),如果回到學(xué)校里一傳達(dá),肯定從上到下都會(huì)極度重視,要落實(shí)總理的指示。可是《梁祝》怎么改?能不能改?俞麗拿思忖再三,覺(jué)得她拉熟了的《梁祝》不能再改。她想,總理只是以個(gè)人的意見(jiàn)和她商量,她沒(méi)有必要大事張揚(yáng)。回到學(xué)校,見(jiàn)到陳鋼和何占豪,她猶豫了一下,終于一字未吐。
幾個(gè)月后,周總理又一次陪外賓來(lái)上海,在文藝演出的節(jié)目單上,他仍然點(diǎn)小提琴協(xié)奏曲《梁祝》。還是那個(gè)宴會(huì)廳,還是俞麗拿,還是那一曲未經(jīng)改動(dòng)的《梁祝》。周總理看著在舞臺(tái)上拉琴的俞麗拿,很投入地聽(tīng)著。演出結(jié)束時(shí),他一邊鼓掌,一邊看了看手腕上的表。
宴會(huì)結(jié)束后,周總理見(jiàn)到俞麗拿,直截了當(dāng)?shù)貑?wèn)道:“小俞,你們沒(méi)改嘛,《梁祝》還是那么長(zhǎng)?”俞麗拿有點(diǎn)緊張,她站在那里,看著周總理,笑得有點(diǎn)尷尬。周總理沉吟了一下,笑著揮了揮手,大聲說(shuō):“我不能苛求藝術(shù)家,能不能改,由你們自己決定吧。”此后,周總理再也沒(méi)有提起此事。他以后又多次聽(tīng)俞麗拿拉《梁祝》,每次都聽(tīng)得很入神。
這件事,俞麗拿一直沒(méi)對(duì)人說(shuō),但她永遠(yuǎn)記得周總理寬容的微笑,記得他揮手的動(dòng)作。在她的記憶中,周總理是一個(gè)真正熱愛(ài)藝術(shù)、懂得尊重藝術(shù)家的偉人。
(摘自《上海紀(jì)實(sh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