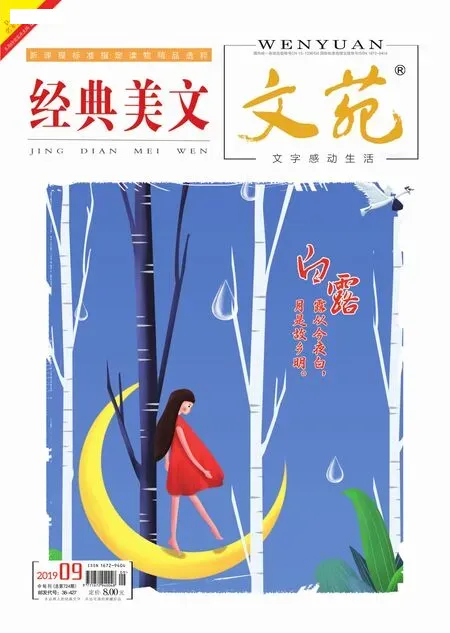劉亮程:書寫有翅膀的文字
文/舒晉瑜

有人說,劉亮程是土地里“長”出來的作家。是的,在土地上活久了,他也活成了一塊土。
昔日牧羊人
劉亮程,1962年生于新疆古爾班通古特沙漠邊緣沙灣縣的一個小村莊,并在那里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時期。小時候他放過羊。羊群永遠是半步半步地走,邊吃草,邊望天。看著看著,他成了羊群中的一只。
躺在草地上的時候,他便成了草;看云朵飄過天空,他便成了云。他放任自己像植物一樣隨意生長。偶一回頭,他發現身后的草全開花了,一大片。好像誰說了一個笑話,把一灘草惹笑了……
后來,他當了十幾年鄉農機管理員,一年做兩次報表,平常的時候騎摩托車在田間地頭轉,指導農民種地,推廣先進機械。就像他的散文集《一個人的村莊》里寫的那個閑人,每天太陽升起前,他一個人站在村外,以自己的方式迎接太陽升起,每天黃昏獨自目送日落。他認為此時此刻天地間最大的事情是太陽要落了,這么大的事情沒有人管,那他就代表所有人目送日落。
更閑的時候,他寫寫詩,發表過幾首。一直到三十歲,他才走出鄉村,在一家報社做編輯,同時開始自己的散文寫作。
即使走出了,也仍是在鄉村的感覺。他幾乎所有的文字都是與他所生存過的鄉村有關,對人類所生活的一種土地和狀態進行深刻敘述。像是等待農作物緩慢地成長,他在鄉村的歲月里以悠閑而緩慢的生活方式,熬出了獨有的味道和情懷。1998年,《一個人的村莊》悄然走紅,文壇似乎突然意識到劉亮程的存在,他甚至被譽為“20世紀中國最后一位散文家”和“鄉村哲學家”。
隨后,他先后完成《虛土》《鑿空》。鄉村生活不全是云淡風輕,但是劉亮程的筆下沒有提及任何苦難。他把大地上的苦難消化了,從沉重的生活中抬起頭,讓破滅的夢得以重生,引領土地上笨重的生命朝天上仰望甚至飛翔。
這就是劉亮程,他在書寫有翅膀的文字。
如今“捎話者”
劉亮程能夠完成新作《捎話》,也許是預料之中的事情。但是他仍然帶給我們諸多的驚喜,關于戰爭、關于死亡、關于哲思,以及敘述的視角和干凈靈動的語言。
他曾在小說《鑿空》中寫過一群驢;《捎話》中寫了一頭叫謝的小驢。《鑿空》中那些毛驢斜眼看著人,其實也是現實生活中驢的眼神。他似乎一直想弄清楚毛驢和人的關系,想看懂驢的眼神,想聽懂驢的叫聲。《捎話》寫到最后,懂得幾十種語言的捎話人“庫”,終于聽懂了驢叫,并在后來成為人驢間的“捎話者”。
“我構造的是一個人和萬物共存的聲音世界,在這個世界里,人聲嘈雜,各種語言自說自話,需要捎話人轉譯,語言也是戰爭的根源。而所有的語言聲音中,驢叫聲連天接地。這種未曾走樣無須翻譯的聲音,成為所有聲音的希望。”劉亮程說,人可以從身邊其他生命里看到未來,這恰恰是人的希望。
《捎話》中那頭叫“謝”的小黑毛驢,和捎話人“庫”一起穿越戰爭。而這場戰爭,并沒有正義和非正義的呈現,它是一場荒謬的戰爭,一場影子之戰。劉亮程如此介紹這本書的源起:“東邊的毗沙國修了一道高高的院墻,把遠在千里之外的黑勒國早晨的陽光擋住了,戰爭就這樣開始了。戰爭的這種荒謬性,并不能削減戰爭的慘烈,任何一場戰爭,不管起因是什么,一旦開始,它都是一個收割人頭的機器。所以《捎話》呈現了一場又一場的戰爭,故事也在戰爭中鋪開。”
有戰爭,必然有死亡。但劉亮程的著重點在于書寫死亡的儀式和尊嚴。“當死亡來臨,死亡并不是結束,結束的是生,而死剛剛開始,我寫了幾個漫長的死亡過程,這樣的書寫是對死亡的尊敬,死亡本身有其漫長的生命,這恰恰被我們忽視。”
能夠流傳至今的偉大作品,無不在傳承著“捎話”的使命,所以劉亮程說,從小說第一句開始,故事就帶著這樣的使命上路。被隱藏的故事才是最后要講出來的,用千言萬語,捎那不能說出的一句。小說家也是捎話人,小說也是捎話藝術。
萬物皆有靈
“一個人一出世,他的全部未來便明明白白擺在村里,不可能活出另一種樣子。”劉亮程的全部,就在他的村莊里。
寫《一個人的村莊》時的劉亮程,走出家鄉孤身一人在烏魯木齊打工,整天背著一個小包在街上奔波,跑稿件、拉廣告。這段經歷卻使他有了望鄉的體會,也使他得以從城市的喧囂和塵土之中,遙遠又真切地認識了家鄉。他覺得村莊突然被自己看見了,看得那么真切,那么深情;村莊的雞鳴狗吠,村莊的白天黑夜,云朵飄過的聲音以及花開的聲音,所有的聲音全部被他聽見了。
于是,從《一個人的村莊》開始,萬物有靈。
劉亮程對此解釋為:與生活有關。他從小就在鄉村萬物中長大,能夠更多地去貼近或者感受人之外的其他生命和非生命。“現在我回想起小時候,更多會想到的是包圍村子的草木、荒野,我會更多回想到一年四季刮過村莊的風和它帶來的聲音,在風聲中塵土的聲音、木頭的聲音、屋檐的聲音,還有天空的聲音。”
似乎他天生就能感知那些有聲音的生命,以及它們的靈魂的訴說。這樣的感受在劉亮程真誠自然的書寫中,帶給我們無比新奇的感受。
2006年,劉亮程出版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虛土》,它的文體既像散文又像小說。《虛土》的整個思維和情緒都是詩歌式的,似乎是早年沒有寫完的一首詩,最后寫成了長篇文章。緊接著,劉亮程推出《鑿空》。盡管他認為這將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長篇小說,讀者從開篇第一句話就會認同它是小說”,可是實際上,這部作品無論感受還是相對零散的結構仍然未能完全擺脫散文的影子。
劉亮程并不否認。他太沉溺于對自然的敘事,有時故意讓故事的速度慢下來,把筆墨放在看似不相干的事物上。“耐心讀《鑿空》,會發現我呈現的與主題不相干的細枝末節的描述,可能是最有意義的。寫作中,我也會把主題忘記。《鑿空》本來就是一部沒有設定明確目的的作品。我也不愿意讓它明確地到達目的。我不想讓文字跟著主題去趕路。”
從一開始,劉亮程就不缺乏自信。《鑿空》入選亞洲周刊評選“2010年十大小說”,被認為是描寫中國式孤獨的罕見的作品。
劉亮程很喜歡這個評價,他早期的散文便是“一個人的孤獨”,他說,《鑿空》是一個地方一個群體的孤獨,有“孤懸塞外”的味道。
極盡自然主義
從《一個人的村莊》開始,劉亮程的文學創作就在朝自然主義文學的方向努力。自然主義文學在中國的淵源,至少從莊子開始。劉亮程認為,山水詩、田園詩,甚至鄉村文學,是有傳統脈絡的文學理念,他認為的自然文學,最核心的是自然本身。在我們以往的文學中,自然是作為喻體存在的,總是借助自然抒懷,在這樣的書寫過程中,自然不是它自己,一棵草、一朵云都被賦予了使命,不是自然的本身而是比喻的工具。那么,自然文學應該把自然放在最自然的位置,讓自然本身說話。
在劉亮程看來,文學不是一個生命簡單的說明書,而是讓生命變得更加有感覺。文學讓生命的氣息有溫度,讓生命的神秘感重新塑造出來。比如對待一棵草,通過觀察的方式,了解這棵草是哪年生,什么時候開花,什么時候枯萎,科學只能把植物呈現到這樣一種程度。文學則是有靈魂的寫作,自然主義首先承認的是萬物有靈,文學是通過人的靈魂與自然界的靈魂溝通的時候呈現出的表達方式。
“古人講靈感,靈感不是人的,是他物的,與他物突然產生靈魂上的溝通,出現了美妙的碰撞,這是自然給我們的。”劉亮程這樣談他對靈感的理解:對一般的寫作者來說,靈感是偶爾的、短暫的、求之不得的;對作家來說,靈感應該是常態的。莊子在寫草木時,是草木在說話。作家所呈現的草木,肯定不同于自然科學的草木,它生活在天地間,有氣味、有顏色,在風中有姿態、有聲音,作家從草木上可以看到情感,可以看到生命的過程,可以感受到花草樹木的全部。莊子追求天人合一,心境融入天地之間,與天地精神之往來,這才是自然主義。很長時間以來,有兩種東西阻礙了和萬物有靈的接觸,一是科學知識,我們用科學的手段分析、剖析一個生命,呈現簡單的科學說明。當然不能認為它是錯的,它是解釋萬物的方式之一,卻妨礙了對自然的進一步了解;二是我們缺失了和自然表達的語言。《詩經》中就建立了完整的語言系統,古典小說中也總會出現大段的自然描寫,而現在的讀者已沒有心境去欣賞自然。
崇尚自然主義的劉亮程并不拒絕網絡,他天天上網,主要看新聞、搜資料,也有博客、微信、微博。以前熱衷,現在卻不怎么寫了,也不怎么看了,因為“太浪費時間”。“我們通過網絡了解了一個看似豐富實則虛遠雜蕪的世界。太多信息并不能豐富人的內心,反而將心當成了垃圾庫。心靈最好的收獲是向內自省,朝天想象。”他說。
曾問劉亮程,當讀者和作家都無法和自然保持親近的時候,為什么你依然能做到?“可能在我的心智中還保留著一種天真,和自然萬物交流的門隙還沒有徹底封死。我從小生活的環境,村莊比較遙遠,能大片聽到自然的聲音。”劉亮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