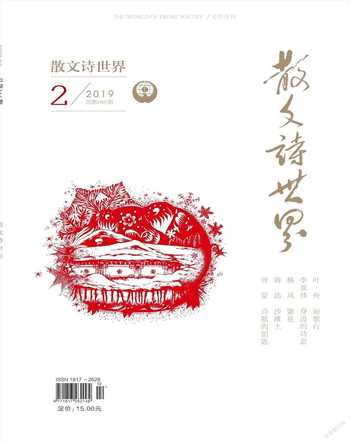詩歌的鑰匙 (二篇)
曾蒙
被上蒼的不公正所擊打
寒冷的蒼穹
葉芝
突然我看見寒冷的、為烏鴉愉悅的天穹
那似乎是冰在燃燒,而又生出更多的冰,
而想象力和心臟都被驅趕得發了瘋
以至于這樣或那樣偶然的思緒都
突然不見了,只留下記憶,那理應過時的
伴著青春沸血,和早已被勾銷的愛;
而我從所有感覺和理智中承擔起全部責備,
直到我哭喊著哆嗦著來回地搖動
被光穿透。呵!當鬼魂開始復活
死床的混亂結束,它是否被赤裸裸地
遣送到道路上,如書上所說,被上蒼的
不公正所打擊,作為懲罰?
(王家新譯)
W·B·葉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出生于距離愛爾蘭首都都柏林不遠的山迪蒙(Sandymount),是一位肖像畫家的兒子。他的童年分別在都柏林和倫敦度過,早期學習繪畫,是倫敦藝術家和作家團體中年輕的一員。愛爾蘭詩人、劇作家和散文家,著名的神秘主義者,是“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的領袖,也是艾比劇院(Abbey Theatre)的創建者之一。葉芝的詩深受浪漫主義、唯美主義、神秘主義、象征主義和玄學詩的影響,并逐步演變出其獨特的風格。
1889年,葉芝結識了小一歲多的愛爾蘭著名民族主義者毛德·崗 ( Maud Gonne, 1866—1953)。毛德·崗非常仰慕葉芝的早年詩作《雕塑的島嶼》,并且主動和葉芝結識。葉芝深深地迷戀上了這位毛德·崗,而這個女人也極大地影響了葉芝以后的創作和生活。據說葉芝第一次見到她后就在日記中這樣寫道:“我一生的煩惱開始了”。經過兩年的密切交往后,葉芝向毛德·崗求婚,卻遭到拒絕。其后,他又共計向她求婚三次,分別是在1889年、1900年和1901年,均遭到了拒絕。1917年夏天葉芝和當年的毛德·崗重逢,并且向她的養女求婚,但是也遭到了拒絕。
第一次讀這首《寒冷的蒼穹》,是十幾年前在四川民刊一四川詩人的隨筆中,即被深深打動,十幾年來,不斷重復閱讀,而每次閱讀都是新鮮的激動與戰栗。這首譯作也經過譯者多次修改,我至少見過三個版本。此次收入的這個版本是譯者最新出版《帶著來自塔露薩的書:王家新譯詩集》(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所收錄,想必是譯者認可的。
葉芝早期名詩《當你老了》,發表于 1893年,獻給終身的精神戀人毛德·崗。這首詩歌雖然有多個翻譯版本,但人們對其喜愛有加,已經成為中外經典愛情詩歌。人們對愛情的渴望,老來后對戀人的回憶、渴望,柔情斷腸,這是多么美好的一幕。
然而,愛情固然美好,但人生是由很多殘缺構成。寫出《當你老了》的葉芝,二十多年后寫出了《寒冷的蒼穹》,該詩發表于1914年,據說這首詩是葉芝聽說毛德·崗結婚后所作。
縱然我們有千般理由來為一對戀人祈福,但是當戀人嫁于他人,內心除了祝福,恐怕更多的還是失望、痛苦,難言的悲傷。這樣的感情如果用詩歌如何去表達呢?
且看葉芝。他如此道來:
突然我看見寒冷的、為烏鴉愉悅的天穹
那似乎是冰在燃燒,而又生出更多的冰,
在失去戀人的葉芝眼里,他看到的是“寒冷的、為烏鴉喜悅的蒼穹”,寒冷的蒼穹,烏鴉很喜悅,這意味著什么?古往今來,烏鴉經常出沒在詩歌與哲學領域,他們大體意思相近,因為它總是與不祥之兆相關。卡夫卡曾經寫到“僅僅一只烏鴉/就足以摧毀天空”,愛倫坡也寫過《烏鴉》,都是作者唱出壓抑愛的詩篇。中國詩人于堅也寫過《對一只烏鴉的命名》,當然,那是一次語言學意義上的探討了。
詩歌以烏鴉這一意象開篇起意,那么,我們不妨考察一下烏鴉這個意象了。
烏鴉在各國的待遇與兇吉是不一樣的,我國遠古,把太陽稱為“金烏”,“金烏西墜,玉兔東升”。古代帝王身后常常有幾面旗子,其中就有金烏旗和玉兔旗,以顯示王者氣象。漢代以前,烏鴉在中國民俗文化中是有吉祥和預言作用的神鳥,“烏鴉報喜,始有周興。”,漢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同類相動》中引《尚書傳》載,“周將興時,有大赤烏銜谷之種而集王屋之上,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古代史籍《淮南子》《左傳》《史記》也均有名篇記載。至于人們認為烏鴉是不祥之物可能與后弈射日的神話有關。
美國人也喜歡烏鴉,尤以西雅圖人為最,被稱之為吉祥鳥、神鳥。其實不只是美國人,好多國家都把烏鴉稱為神鳥,如埃及、印度、日本、斯里蘭卡等等。斯里蘭卡還把烏鴉作為其國鳥。此前我見過這首詩的其他版本把“烏鴉”翻譯成“白嘴鴉”,我猜想,不用歐洲的白嘴鴉,而用國人更清楚寓意的“烏鴉”,在翻譯上也是為了更能讓讀者理解其寓意。
“為烏鴉愉悅的天穹/那似乎是冰在燃燒,而又生出更多的冰”,蒼穹像冰在燃燒,但不僅僅是冰。燃燒的冰,如此寒冷而又孤獨,整個蒼穹都被籠罩都被覆蓋。
而想象力和心臟都被驅趕得發了瘋
以至于這樣或那樣偶然的思緒都
突然不見了,
想象力與心臟因為不斷的擊打與打壓,已經不見了,就像“這樣或那樣偶然的思緒”,頭腦一片空白。整個蒼穹之上,“想象力和心臟都被驅趕得發了瘋”,一些偶然的思緒。是什么思緒如此絕望?
只留下記憶,那理應過時的
伴著青春沸血,和早已被勾銷的愛;
“只留下記憶”,寒冷的蒼穹的記憶,“那理應過時的/伴著青春沸血,和早已被勾銷的愛”。這里,葉芝寫到了愛,誰的愛?顯然,是他們混合了熱血,屬于青春的愛,但是很久以前失之交臂的愛。失之交臂的愛!錯失的愛,開出寒冷的蒼穹下孤獨的花朵、絕情的花朵。
而我從所有感覺和理智中承擔起全部責備,
直到我哭喊著哆嗦著來回地搖動
被光穿透。呵!當鬼魂開始復活
死床的混亂結束,它是否被赤裸裸地
遣送到道路上,
說到這里,詩人有近乎絕望的態度,來面對一場失敗的戀愛。同時,我們仿佛又覺得這不僅僅是葉芝個人情感失敗的記錄,而是我們的人生、我們的社會整個的反觀:
如書上所說,被上蒼的
不公正所打擊,作為懲罰?
如果把葉芝《當你老了》與這首《寒冷的蒼穹》對照來讀,你會發現,同一個詩人,在兩首詩里仿佛判如兩人。前者熱烈,如火,纏綿悱惻,后者冷峻,如冰,寒徹刺骨。或許這種對照沒有道理,畢竟兩首作品相隔二十一年。但是,對兩首情詩的對照閱讀,你可能會理解葉芝晚年為什么會傾心于神秘主義了。就像牛頓晚年醉心于唯心主義,對一個偉大的物理學家,相信人有靈魂,而且計算出輕重。這多少有點令吾輩不解。
奧登(Wystan Hugh Auden,1907—1973)在《以葉芝為例》(葉美譯)說的可能正確:
“從生活講回到詩歌:今天任何一個詩人,就算他否認觀念對生活的重要性,也能理解神話對詩歌的好處——例如,神話幫助葉芝把他的私人經驗變成公共事件,同時也可以把他對公共事件的觀點從個體的角度思考。他還能夠理解在詩歌里所有觀念都可以變成神話;就是說詩歌的審美可以被看成是神話,這樣的結果是詩人或讀者其實并不在乎表達的內容是否真實可信,有說服力。所有葉芝求助一切神話——任何神話,只有他認為有用——來達到自己的寫作目的。”
把私人經驗改寫成為公共事件,或者把公共事件的觀點切換成為個體的思考,這或者是一種寫作才能,更是一個詩人成熟成為標新立異的創作沖動。種種道德約束、人為的成見都不會成為阻擋寫作的動力。
繼而奧登認為:小詩人和大詩人的區別不是看誰寫出來的詩好看。確實有時候我們看到小詩人的作品單獨拿出來,比大詩人的要完美得多,但大詩人有一個明顯的優點,那就是他總是持續地發展自己,一旦他學會了一種類型的詩歌寫作,就立刻轉向了其他方向,去尋找新的主題和新的形式,或兩者同時進行。
不斷地轉變、突圍,不斷地試驗,以語言作為盾牌,又使得語言成為語言。寫作的難度不斷超越,不斷形成新的難度,不斷地突破自己。這是個周而復始、沒有終點的圓周運動,哪里都是起點,這也是詩人不斷創造的源泉和秘密。
愛爾蘭詩人謝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1939—2013)認為,葉芝《寒冷的蒼穹》是這樣一首詩作,它昭示了生命的整體性目標;它通過韻腳、節奏及抑揚語調等詩藝手法內在地完成了這一宗旨。這些技術創造了一種力量和一種秩序并以其高揚了這樣的信念:在我們自身的存在中存在著一種無所不在的更偉大的力量和秩序。
葉芝被另一位愛爾蘭詩人T·S·艾略特稱為“我們時代最偉大的詩人”。他因“以其高度藝術化且洋溢著靈感的詩作表達了整個民族的靈魂”而獲得1923年諾貝爾文學獎。
1939年葉芝去世,奧登寫下《悼念葉芝》,詩中寫道:“他在嚴寒的冬天消失了:/小溪已凍結,飛機場幾無人跡/積雪模糊了露天的雕像;/水銀柱跌進垂死一天的口腔。/呵,所有的儀表都同意/他死的那天是寒冷而又陰暗。”(查良錚譯)他死于寒冷的蒼穹,也葬于寒冷的蒼穹,他與天空合二為一,成為神奇的愛爾蘭,成為神奇的愛爾蘭另一種神話。
我的靈魂變得像河流一般深邃
黑人談河流
休斯
我了解河流:
我了解像世界一樣古老的河流,
比人類血管中流動的血液更古老的河流。
我的靈魂變得像河流一般深邃。
晨曦中我在幼發拉底河沐浴。
在剛果河畔我蓋了一間茅舍,
河水潺潺催我入眠。
我瞰望尼羅河,在河畔建造了金字塔。
當林肯去新奧爾良時,
我聽到密西西比河的歌聲,
我瞧見它那渾濁的胸膛
在夕陽下閃耀金光。
我了解河流:
古老的黝黑的河流。
我的靈魂變得像河流一般深邃。
(申奧譯)
這是美國著名黑人詩人蘭斯頓·休斯(Langston Hughes,1902—1967)發表的第一首詩,題目是《黑人談河流(The Negro Speaks of Rivers)》。寫這首詩時,他還是一個中學生,只有18歲。而這是他著名的詩篇。鄒絳、趙毅衡等詩人都翻譯過這首詩歌,申奧的譯本是首譯,所以印象深刻。
這是一首憂傷深沉的詩歌,我不記得是多久讀到的,反正是很小的時候,一讀到它便被深深吸引住。只知道休斯是黑人,并無更多他的個人資料以及寫作背景。但是這都無關緊要。好詩是沒有理由的。記得在達縣讀高中時,辦的《青少年讀寫輔導》,我還專門把這首詩歌登出來,另外班級的英語老師說我欣賞水平蠻高。其實,他并不知道,《黑人談河流》只是我喜歡的其中一首,我喜歡的詩歌數不勝數。
1902年2月1日,休斯生于密蘇里州的喬普林市。由于父母離異,從小跟隨外祖母、母親和親友生活。1922年進入哥倫比亞大學。1923年輟學。曾到達過西非海岸,后流落巴黎,當過夜總會的看門人和飯館廚師。回國后又當過洗衣房工人和旅館侍者。生活在社會底層,對黑人在美國社會的遭遇有很深的了解,社會經驗豐富。他涉獵多種體裁的文學創作,小說、戲劇、散文、歷史、傳記、小品、詩歌,尤其以詩歌聞名,被稱為“哈萊姆的桂冠詩人”。主要詩集包括《猶太人的好衣服》(1927)、《夢鄉人》(1932)、《哈萊姆的莎士比亞》(1942)等。長篇小說《不是沒有笑的》(1930),短篇小說集《白人的行徑》(1934)、《共同的東西及其他故事》(1963);幽默小品集《辛波爾說出他的思想》(1950)、《辛波爾孤注一擲》(1957)等;自傳《茫茫大海》(1940)和《我漂泊,我彷徨》(1956)。休斯成名后沒有離開哈萊姆黑人聚居區,他始終關注著黑人,尤其是下層黑人的生活。他的作品從黑人民間音樂和民歌中汲取營養,并受其啟發,在風格上傾向于爵士樂,把爵士樂的韻律和節奏融入自由詩中,清新、熱情、奔放、開闊、凝練、深沉、舒展,格調清新,意境深遠,具有震撼人心、深不可測的感人力量,表達對種族歧視的控訴,抗議政府對黑人的歧視,對美國與非洲黑人詩歌的發展、黑人民族的進步,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晚年期間編選了不少黑人作家的選集、短篇小說集和詩文集,為黑人文學的推廣不遺余力。
1920年,年僅18歲的詩人乘坐火車途經密西西比河去往墨西哥。西西比河流淌著美國南方奴隸制時期黑人悲苦的血淚史,波光泛濫的西西比河流觸發了詩人敏感的神經:詩人父親對自己黑人同胞從來都有“奇怪的厭惡感”,看不起自己的同胞,詩人的想法卻是,沒有同胞的愛,黑人會更黑。必須無條件熱愛自己的民族,為自己種族的文明和尊嚴而驕傲。正是這次旅行,偉大的西西比河激發了詩人噴發的靈感,一氣呵成寫成了這首詩,按照詩人自己的說法,這首詩歌他“用了十分鐘至一刻鐘時間”。詩人在談到這首詩的寫作過程時說,列車緩緩從密西西比河上的鐵橋上駛過,他由這條古老的河想到黑人的命運,想到阿貝·林肯總統為了廢除奴隸制,親自乘木筏沿著密西西比河順流而下到新奧爾良,他又想到黑人過去生活中的其他河流──非洲的剛果河、尼日爾河和尼羅河。詩于是就這樣產生了。
對于蘭斯頓·休斯來說,他父親的身份有兩重含義:第一,他父親是一個不成功的商人。而父親作為一個商人的失敗是黑白種族之間斗爭的訊號。在《黑人藝術家與種族大山》中,蘭斯頓·休斯說“白”是一種黑人必須符合才能進入的標準。相對于這種標準,他認為,黑人藝術家需要翻越一座大山才能發現黑人的個性和共性。蘭斯頓·休斯感覺到沮喪,因為他身處在由白人控制的美國。對他來說,其父親商業上的失敗是必然的,既是經濟大蕭條和種族歧視的必然結果,更是源于他父親作為一個黑人卻自相矛盾地藐視印第安人、黑人和窮人的態度。他父親的自我憎恨體現了他父親本性中最為惡劣的部分。他父親的自我憎恨不僅僅在心理上對蘭斯頓·休斯產生了影響,還導致他采取了一種反對白人歧視的態度,而且以黑人文化作為自己的創作向導。
蘭斯頓·休斯與他父親之間復雜的關系明顯地表現在《黑人談河》中……《黑人談河》的視野也許是既史實又虛構的。雖然蘭斯頓·休斯用一種富有想象力和抽象的方式描述了一些黑人文化的慣例,如他選擇了河流來代表黑人獨特的歷史。剛果和尼羅河體現了美麗的黑色和它的成就;它們自然而然地在幼發拉底河邊出現并暗示了黑人文明的起源。用這種方式,蘭斯頓·休斯明確地告訴他的父親和美國民眾,非洲黑人及黑人文化在歷史上是高尚性的。河流帶入持續的歷史流程,同時也暗示了奴隸制度早已在密西西比河畔被廢除。蘭斯頓·休斯完成了面對美國文化和父親的雙重任務(參見曾艷《蘭斯頓·休斯:一個矛盾的詩人》《作家》 2012年14期)。
黑人是一個古老的種族,《黑人談河流》沒有直接描寫黑人的苦難史和斗爭史,讀完全詩,不難體會,詩人由對密西西比河對自己的沖擊起句,從第一印象中的強烈感受寫起,
我了解河流:
我了解像世界一樣古老的河流,
比人類血管中流動的血液更古老的河流。
即刻重疊成內心的感受,直接、深刻,毫無拖泥帶水,點石成金:“我的靈魂變得像河流一般深邃。”
進而穿越時間與空間的束縛,展開想象的世界,把世界上著名的河流幼發拉底河、剛果河、尼羅河盡收眼底,
當林肯去新奧爾良時,
我聽到密西西比河的歌聲,
我瞧見它那渾濁的胸膛
在夕陽下閃耀金光。
這里閃耀著“渾濁的胸膛在夕陽中閃著金光”,重新還原了新奧爾良的史實,使得詩歌變得厚重:詩人敘說了美國黑人的非洲起源史,也厘清了美國黑人的全部文明史。拓展了詩歌的眼光,深邃而開闊,又加大了詩歌的深度。
詩歌復調般的韻律再次響起,就像一首抵達靈魂的憂傷的歌謠:
我了解河流:
古老的黝黑的河流。
我的靈魂變得像河流一般深邃。
客觀地講,休斯在美國文學甚至世界文學史上,影響并不是很大,他的存在說明一個問題:什么是好詩,什么樣的詩歌值得后人學習?作為黑人的詩人休斯,他以這首天才之作、少年之作做出了這樣的回答:詩歌沒有標準,沒有公式,沒有一成不變的定理,它需要真實具體的感情,需要從內心發出自己的吼聲。
很多偉大的詩歌可以說是天才之作,情感豐沛,勢不可擋,渾然天成,無需修改。休斯的名作《黑人談河流》又是一證據。
據說,1960年代,黑人領袖馬丁·路德·金那篇膾炙人口的演講《我有一個夢想》,跟休斯另一首詩歌《夢想》“夢想若是消喪,/生命就像貧瘠的荒野,/雪覆冰封,萬物不再生長。”有了直接的呼應,成為兩位偉大黑人靈魂的交融:
我夢想有一天,幽谷上升,高山下降;坎坷曲折之路成坦途,圣光披露,滿照人間。
這就是我們的希望。我懷著這種信念回到南方。有了這個信念,我們將能從絕望之嶺劈出一塊希望之石。有了這個信念,我們將能把這個國家刺耳的爭吵聲,改變成為一支洋溢手足之情的優美交響曲。
有了這個信念,我們將能一起工作,一起祈禱,一起斗爭,一起坐牢,一起維護自由;因為我們知道,終有一天,我們是會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