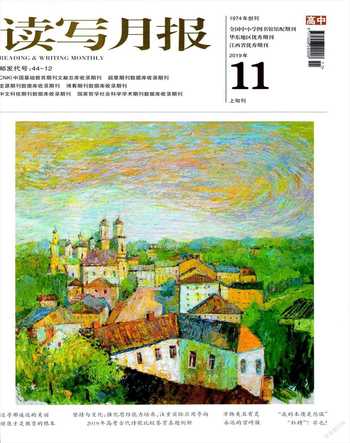截圖與對景
談勝軼
周邦彥的《蘇幕遮(燎沉香)》是一首抒寫夏日思鄉的經典詞作。思鄉是中國文學里一個重要的永恒的文學母題,千百年來佳作不斷涌現,要想在這上面再翻出新意實非易事。文學創作之難,不僅難在內容,更難在審美形式的創造,周邦彥的這首《蘇幕遮》在審美形式上有何創新之處呢?
我認為,該詞在章法上巧妙地運用了“截圖”和“對景”,并使之成為思鄉情的重要載體。周邦彥給自己思鄉的心靈尋找到了一個絕妙的通道,這個通道僅屬于有“詞中老杜”之稱的周邦彥。他是一位極富藝術意識和審美意識的詞人。作為欣賞者,若能發現此一審美通道,明心見性,力爭以慧眼覷見詞人的美好心靈,抉發其神思想象,探究超軼常態的藝術形式之美,著眼于作品之精神內涵與審美形式的有機統一,則庶幾可以進入本詞的深邃意境;否則,只能在詞作外圍作一些人皆能言卻不得要領的解讀。
被時間淘洗成經典的文學作品對歷代的解讀者來說都是一種高難度的考驗,這首《蘇幕遮(燎沉香)》也不例外。譬如,該詞以荷花為中心意象,在上下片之結穴處分別營構了“風荷玉立圖”和“芙蓉歸夢圖”,并將思鄉之情熔鑄其中。這兩幅圖畫如果照生活邏輯的順序排列,究竟誰先誰后?二者在整篇詞作中又有何審美關聯?對于這兩個關乎詞作藝術形式方面的問題,每一位解讀者都不應回避。
元豐初年,周邦彥以布衣入京師,“游太學,有俊聲”(《咸淳臨安志》)。七年(1084),獻《汴都賦》,受神宗賞識,由太學外舍生擢為試太學正,從此聲名震耀。這期間,他久居京師,泛起思鄉之情,自是常理。況且錢塘自古繁華,“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荷花成了錢塘的名片,也成了觸發詞人鄉思的重要媒介。但是,詞人在詞的起調二句并未言及荷花,他只是很平靜地敘說這初夏的天氣潮濕、悶熱異常,心里有些煩躁,只好以熏燒沉香的方式來驅濕消暑以求心靜——“燎沉香,消溽暑”。
待暑氣略退,詞人才勉強入睡;但破曉時分,巢居屋檐的鳥雀們又探頭探腦、呼朋引伴、嘰嘰喳喳地叫開了——“鳥雀呼晴,侵曉窺檐語”。詞人已被鳥雀叫醒,這是一、二句與三、四句之間的一個簡單的關聯。但這里還有一個重要的細節被許多解讀者忽略了,那就是詞人夜晚所做的一個美夢也被叫醒了!
按照常規邏輯,在一、二句之后,詞人應該接著敘述夢境,再寫如何被鳥雀吵醒,以致“喚回曉夢天涯遠”(辛棄疾《蝶戀花·和趙景明知縣韻》)。原來,這個夢境畫面被詞人故意截取下來,安置到詞的下片歇拍處了。這種章法技巧,就是所謂“截圖”:在有些詞作里,作者會故意將一個完整的事件擊碎,拾掇其中的某一片段,把它鑲嵌在詞的上片或下片或橫跨上、下片的醒目處,使之極富畫面感而成為全篇最搖人心旌的一幕。此詞被截圖處理的是“芙蓉歸夢圖”:“五月漁郎相憶否?小楫輕舟,夢入芙蓉浦。”詞人在夢中喃喃自語:農歷五月的家鄉,那些曾經一塊垂釣的玩伴還記得我嗎?我們劃著船槳,舟遙遙以輕飏,飄入了那片充滿童年歡樂與溫馨的荷塘。這個夢境迷離恍惚,其中的人事景象皆模糊而不具體。詞人以落想對方的方式來強化自己的鄉思,情感具有雙向流動的迂回曲折之美。
如果將此一虛寫的圖畫與屬于實寫的“風荷玉立圖”按照生活本來的邏輯,一前一后地并置于詞的上片,那就會導致全篇有頭重腳輕、上下片語言長度失衡的弊病;并且二者的對比度也會因其跨度的縮小而大大減弱,不利于詞作整體意境的營造。夢醒之后,詞人已明確地意識到了自己的游子身份,心中有些悵然、煩悶、不寧靜。對這些情緒,他只能以庭院荷池一隅的清新景致來紓解,“葉上初陽干宿雨,水面清圓,一一風荷舉”。王國維在《人間詞話》里對這幾句頗為贊賞,謂“真能得荷之神理”。單就寫景而言,王國維的評價是切中肯綮的。詞人確實以爽凈的筆墨,表現出了荷之神韻風采和盎然生機,創造了怡人的優美意境;在初陽、宿雨、水面、荷葉、荷花、清風這些意象組織而成的圖畫中,我們可以看到時間的推移、生命的涌動以及思鄉之情的潛滋暗長。詞人對景物的描寫做到了形神兼備、如在目前,并無“隔”之遺憾;語言亦真色天成,自然成趣。
因有了王國維的高度贊美,此后的論者在賞讀該詞時,對這幅“風荷玉立圖”的分析可謂是不厭其煩;但我看到的一些解讀文字大多仍是局部的、靜止的,很少有人去分析它對于整篇詞作的作用以及它與被截圖至下片的“芙蓉歸夢圖”在章法上的聯系。我認為,該詞中的這兩幅圖畫正好形成了一種“對景”關系。所謂“對景”,指的是在軸線或視線端點上的景,互相對視,互為欣賞景致的審美關系。這原本是中國古代園林藝術中的概念。我覺得完全可以用來欣賞中國古典詩詞的章法美。有時,我們欣賞一首詩詞,也如同園林漫步,須懂得其景點安排上的藝術匠心。
為了對“對景”關系有一個感性的認識,我們不妨以頤和園中的銅牛為例。頤和園昆明湖東堤岸畔有一尊大小與真牛相仿的鍍金銅牛,它體態優美、栩栩如生,常引得游客流連忘返。如果要拍攝這頭銅牛,該如何取景呢?多數游客是正對著銅牛的頭部拍攝,其實這種效果是欠佳的;若繞到它的后面拍攝,你將會發現它正翹首凝望湖對岸的佛香閣,是那么的含情脈脈、神態宛然,它仿佛在凝神諦聽,又仿佛在深情企盼。如此拍攝的畫面意境才是幽深感人的。這里,銅牛與佛香閣就形成了對景關系。
本詞上片的“風荷玉立圖”與下片的“芙蓉歸夢圖”便與此類似。隔在兩幅圖畫中間的“故鄉遙,何日去?家住吳門,久作長安旅”四句就如同頤和園的昆明湖,悠悠思鄉水潺湲流淌,年復一年。其空間之“遙”,時間之“久”的感慨,在詞人情感的湖泊里是直接流淌而出的。但它們在“對景”的結構形態中,卻又是通過象征隱喻來表現的。本篇詞作之對景結構的象征涵義有如下兩種:一是空間上的遙遙相望,“風荷玉立圖”的空間是京城汴京(詞中以“長安”借代),“芙蓉歸夢圖”的空間是夢里吳門(借指詞人的家鄉錢塘)。這兩幅圖畫在互相對視中,就意味著在“我”思念家鄉的時候,家鄉也在思念“我”;二是時間上的日夜相思,“風荷玉立圖”的時間是白天,“芙蓉歸夢圖”的時間是夜晚,其互相對視,就意味著這種思念是日日夜夜、綿綿邈邈的。這種對景結構連接著虛與實,過去與現在,模糊與清晰,個中情感亦處于隱蔽狀態,顯得含蓄而極富韻致,整篇詞作的意境亦深邃窈遼。
凡有離鄉體驗者,心中皆可泛起思鄉之情;但要言說之,則有語言形式上的高下優劣之分。周邦彥的《蘇幕遮(燎沉香)》因有了超乎常理的截圖、對景這兩種形式技巧的創造性運用,讓思鄉之情或顯或隱,走向了深摯;尤其是對景結構在時空上的互相守望的象征,使得該文本成了思鄉的永恒的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