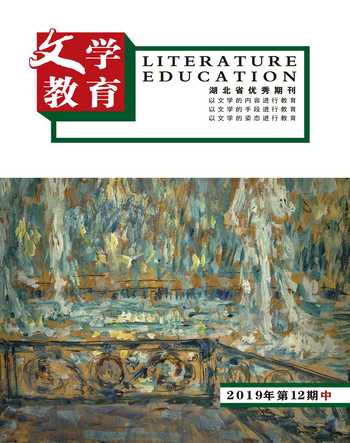書如其人
黃曉嬌
書如其人。讀一本書,就是讀一個人,仿佛聽他在跟你說話,你也在跟他對話。他說出來的話你懂了,他就沒有白說;你懂得了他的話,你就沒有白讀。書被讀過,你和他一起,完成了一本書的共同創作,比如手頭這本叫《桂子山上的樹》的散文集。
人其實是孤獨的。我們很難面對面與別人敞開心扉,但是如果隔著一層東西就會不一樣。隔著手機屏幕,再陌生的人也能相談甚歡。隔著遙遠的距離,再羞于啟齒的話也能說得出口。如果隔著書,隔著紙頁的話,時間和距離就更不是問題了,說話的人和聽說話的人不必同時在線。說的人盡管說了,話都留在那兒,而聽的人什么時候想聽都行,隨時捧起書,都能得到言猶在耳的感覺。讀者和作者的心靈可以隨時隨地不約而同地跳動,這種交流的快樂是迷人的,它讓孤獨走開,它讓一個人的心與別人的心一起共振,哪怕是悲傷絕望,哪怕是憤慨苦悶都有回應,這回應讓人的心感到快樂。書讓我們在大千世界,在蕓蕓眾生中找到彼此,閱讀讓我們感知到自己的存在。讓我們因為知道自己并不孤獨,所以快樂。
曉蘇是溫情的,每每讀到他寫親情的文字,總忍不住熱淚涌動。已年過半百的人,猶記得兒時父親把自己扛在肩頭爬山時累得大氣喘吁吁,記得父親送自己上大學時扛著沉重的大木箱累得大汗淋漓。他不避諱說父親的不好,但是他更懂得要感恩,要知好歹。他說:“作為兒女,如果我們對父親一時的過錯念念不忘,并且耿耿于懷,甚至當作不敬不孝的借口,那我們就未免太狹隘了,太偏激了,太荒唐了。倘若真是這樣的話,我們這些當兒女的,不是缺心眼就是缺良心。”他的話句句都敲打人心,不知多少人看到這些話要感到汗顏。
對逝去的堂兄“大哥”,曉蘇的回憶率真,樸實,溫情中有含淚的克制。回憶的結尾,他說:“一年來,不知大哥在天國里過得怎樣。但愿天國里什么都有,有煙吸,有酒喝,有肉吃,有人陪你唱酸歌,陪你說笑話,陪你打上大人,還有人給你送繡花鞋。”這才是真兄弟,真情真性真懂你,毫不矯情。
曉蘇是個重感情的人,不僅對自己的父母親友很重感情,對自己的師長也一往情深。他寫他的中學老師程家箴,記憶仿佛穿越時光回到了三十年前的中學校園,他記得老師穿的衣服,記得老師吃的菜,記得老師講課的動作,記得老師為他改過的作文,如數家珍,歷歷在目。程老師一腔熱情傾灑在教育上,他教學有方,帶領孩子們走出校門,走到田間地頭去體驗生活,去采訪勞動者,他改作文“善于在關鍵處落筆,三言兩語的旁披就能讓我豁然開朗,心明眼亮。”可以說,沒有程老師的影響,就不會有后來熱愛寫作并卓有成就的曉蘇。在桂子山,曉蘇又遇到了生命中另一位更重要的恩師,那就是著名學者王先霈教授。曉蘇孜孜不倦聽從王教授講座,三十年來幾乎聽到癡絕的地步,他細數王教授講座的地點和篇目,令人驚嘆他的記憶是如此之好!也許對恩師的仰慕是觸及靈魂的,所以老師的風采他鐫刻于心。我想起了孔子的弟子們,把恩師的一言一行記載于冊,無比敬仰,無比虔誠,字字璣珠在心里灼灼閃光。
我常常想,我們何以是“我”?在閱讀中,我是我,因為在書中我看見別人的喜怒哀樂生離死別,我照見了我自己也有一顆跳動的心,這顆心會激動喜悅,會悲傷失落,會歌哭,會艷羨,會感慨,會思索。對著書本,把自己痛痛快快地當個人物的感覺真痛快啊!書,就是李白的月亮,舉杯一邀就在那兒,跟你掏心掏肺的。你心里有什么,就能在書里看到什么,沒有比它更懂你的了。你讀過的每一本書都能照出你的一段生命,每一本書里都有一個兩個甚至更多的人陪伴過你。曉蘇《桂子山上的樹》里有許多人,男女老少皆有,有的已經逝去,有的正在新婚,有人的未來已經結束,有人的前程正在展開。他們熱熱鬧鬧說著笑著,安安靜靜走過活過,正過著你我即將或者曾經的人生。文字真好啊,曉蘇的世界里有那么多人,看似尋常,只因有文字的記載,他們的生命力就不會如煙塵散啊。無論什么人,在有情懷的人眼里筆下,都存在得有價值。我感念曉蘇的一支生花的筆,一顆溫軟的心,他讓讀者如我,作為一個旁觀者的心靈也得到許多慰藉。
曉蘇的散文有學者的莊重,有源自油菜坡農民的質樸,有天性的實誠,更有智者的幽默俏皮。他關注故鄉的變化,他買菜做飯支持愛人看奧運,他為朋友的孩子主持婚禮,他給博導的書寫序,他給青年作家寫書評,他給中學教師談話,他談小說創作,談文學評論,他的膽子要多大有多大,他的人緣要多好有多好,他秉持一顆與人為善的心,寧愿為難自己,常常多行善事,多積福德,所以他成全了別人,也成就了自己。讀曉蘇的書,仿佛挖掘一座寶藏,能陶冶情感,能豁達心境,能提升水平,能關照人生。幸會《桂子山上的樹》。幸會曉蘇!
(作者單位:湖北省十堰市藝術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