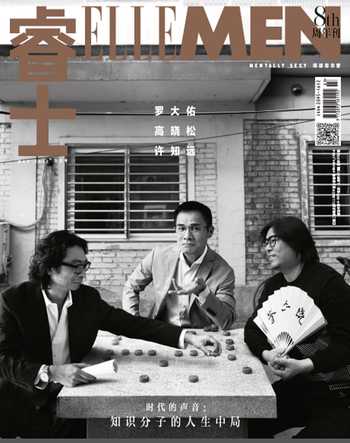如今般的春節
2019-09-10 07:22:44王丹陽
睿士
2019年3期
關鍵詞:上海
王丹陽
照舊俗來說,在上海過年應該是很熱鬧的,但近來兩三年,我家過年亦如平日,只草草地弄些應景的吃食,也沒什么備置饌肴的興致,且俟年歲流過那道除夕的檻。
要說上海的年味,那實在是要從記憶的殘渣里打撈了,只覺得記憶里一層覆于一層如冬天楓林的紅漬,再也分不清哪一年吃了什么,如何拜年,統統混攪成一團,揙壓、捶打成那么幾樁無新意的事。連朋友圈里流傳的文章也年年一樣,講述上海的無非是茅盾的《上海大年夜》和豐子愷的《過年》——連朋友圈都懶得過年。那些文章里歷歷描述的要做的年事,只有在我極幼年時履行過,但也都是簡略版的。
備年貨就不是輕松事,南京路步行街上的南貨店曾經是我們的年貨“裝備站”,只是如今誰還一個勁跑南貨店跟南京路上的觀光客攪和一氣?首先,糕團是不愛吃的了,糕團這種多用來清供的擺設性食品大概在祭祖祀神時還用得著,但沒有人會在除夕夜再燃香點燭了吧?雖然舊社會時蓬門也得堂堂地在那天迎個灶神。現在,恐怕只有在菜市場里能找到那么個攤位賣灶神畫,總有那么個老頭還撐著門面不打烊,多數也不是上海人,只感覺怪可憐的。
高級點的南貨是“機關槍”,也就是火腿,我小時候叫它“琵琶腿”,長得極像琵琶,硬邦邦、實甸甸,膏腴成霜結在表面,封在牛皮紙里。但吃起來需割了再封存,到底不如奶酪般易吃易放,也沒有人為了幾片火腿吊個鮮而備那么一大把。……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22年9期)2022-10-10 10:02:28
散文詩(2021年24期)2021-12-05 09:11:54
環境衛生工程(2021年5期)2021-11-20 05:45:36
少先隊活動(2021年5期)2021-07-22 09:00:02
環境衛生工程(2021年3期)2021-07-21 05:34:40
環境衛生工程(2021年2期)2021-06-09 09:11:16
家庭影院技術(2020年11期)2020-12-28 01:22:42
上海質量(2019年8期)2019-11-16 08:47:12
小主人報(2018年24期)2018-12-13 14:13:50
電器工業(2017年1期)2017-04-11 10: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