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 火
2019-09-10 07:22:44羅俊士
百花園
2019年9期
羅俊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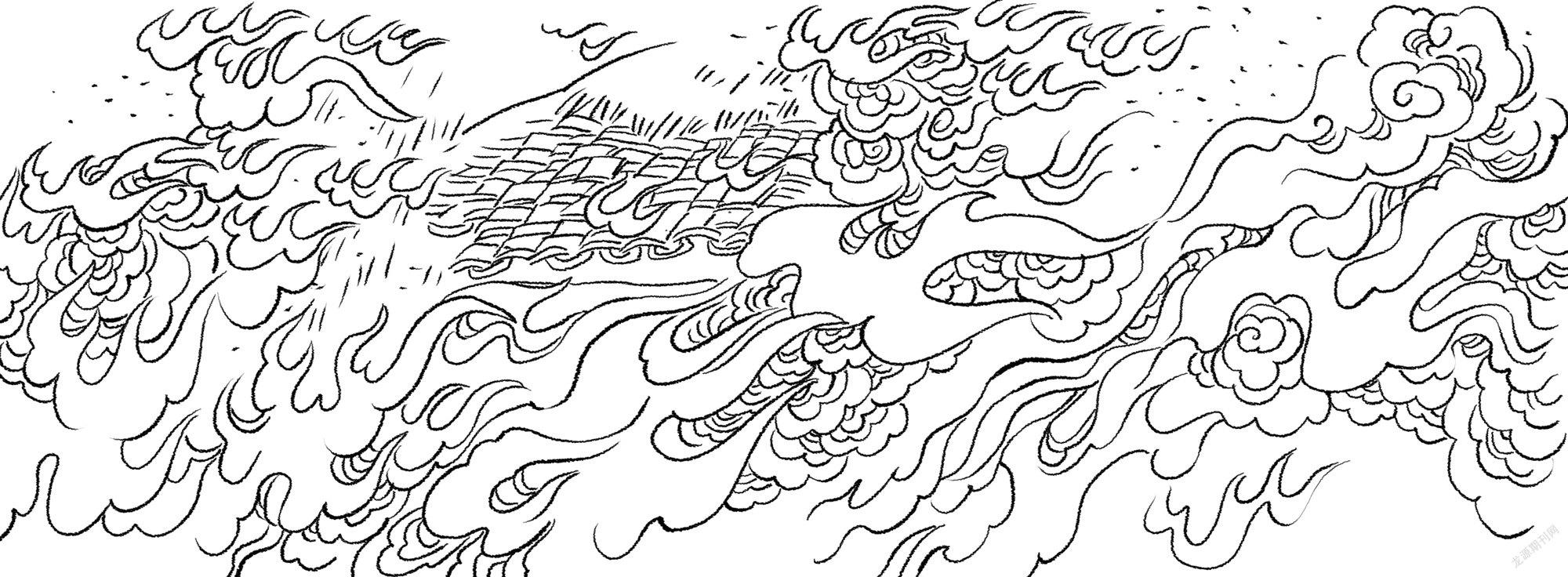
1972年初冬的一個晚上,我家東院堂屋那副對扇榆木屋門吱嘎一聲響,隨之闖進一股濃濃的柴油味,已經睡熟的弟弟被嗆到,打了個噴嚏,翻翻身,皺皺眉繼續睡,打著小呼嚕。
我和爺爺住在西院兩小間平房里,屋當地有個生鐵火盆,幾根木棍已經燒透,彌漫著淡淡的煙霧,仍不失暖意。如果不是我爹在東院可著喉嚨吼叫,我肯定會一覺睡到大天亮。
我爹上工的地方是公社農機站設在我村的分站,有人戲稱他二牌站長,其實只是個看場子的。堤北有塊雞刨地,種不成莊稼,分站就設在那里,距我家百來米。站長量才使用,因了我爹的正直。分站只有兩輛專門犁地的東方紅,我爹白天黑夜守場子,守的也就是幾桶柴油。這晚,四位機手和炊事員老張頭兒都請假回家了,我爹見縫插針,用管鉗擰開桶蓋,倒出大半紅瓦盆柴油,端回家時,我娘正在摸黑納鞋墊。
“把燈點上,這不,有燈油了!”我爹邊說話,邊去灶臺摸那盒泊頭火柴。
我爹不知道柴油里面有著汽油的成分,他見過老張頭兒用柴油添燈。相比起煤油,柴油冒煙多些,燈捻得勤挑勤撥,但擋不住照亮,總比黑燈瞎火強吧。我爹嚓一下劃著火柴,就聽,轟!紅瓦盆里騰起的烈焰直沖屋頂。紅瓦盆距離土炕只有半步,我爹顧不得細想,出手捉住紅瓦盆就往屋外扔,速度那才叫快,絕對不超過三秒。
院子里頓時成了火海。
沖門屋地上有火苗伸長著餓狼似的舌頭四處亂舔,我娘瘋子般跳下炕,抓過一把笤帚拼命掃打。……
登錄APP查看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