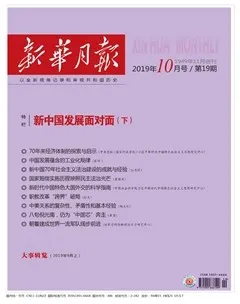一個中國警察的歷史見證
我從18歲就開始當警察,到現在已經44年了。在此期間,我親眼見證了我們祖國與警察科學的迅速發展。
我是第一個以警察身份進入日本警視廳的中國人。
1985年,我還是公安部的一個年輕警察。當時,我到日本出差學習,第一次走進了日本警視廳的指揮中心。當時墻上有一張電子地圖,由無數小燈組成。如果有人撥打110,報警地點的燈就會亮,指揮中心會自動通知就近的兩輛巡邏車。日本警視廳承諾,在東京地區,巡邏車4分20秒就可以到達現場。這時,東京已經引進了GPS衛星定位系統,這對中國警察來說無疑是巨大的震撼。我對指揮中心的日本警官說:“我能不能把這個快速反應系統拍下來?”日本警官說:“不能!這一項技術是對中國保密的。”于是我換了一種方式說:“那么我能不能在這里給我自己拍一張照片?”日本警官說可以,然后我拍了一張照片,那應該是我們中國人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快速反應系統。
作為一個中國的小警察,當年看到日本警用科技的發展,真是震驚,可是我們這一代人又非常幸運,僅僅過了30年后,當我再回到日本的時候發現,我們在飛速地前進,而我們的日本同行盡管起點很高,但這些年來他們幾乎是在原地踏步,技術上并沒有什么新的進展。
這些年我們國家提倡科技強警,不說別的,光是我們公安大學的模擬指揮中心,在某些方面比歐洲一些中等國家的國家指揮中心還要現代化。
有一年我隨一個我們國家的高級警官代表團去日本訪問,我們在日本的警察大學講社區警務。我帶著一臺筆記本電腦去,可是他們的投影儀很落后,我的電腦和投影儀連不上,只好放棄使用電腦。我們講完課以后,日本警察起立鞠了一躬說:希望你們留下寶貴的意見。我們就說:“你們的裝備有點落后了,要好好花錢買一點新裝備了。”
再說說中國的治安情況。1991年我去英國埃克塞特大學念書,成為我國首批派往西方學習警察科學的留學生之一。那里被稱作女王的花園,地處富人區。那時我才35歲,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可是我在街上見到那些頭上刷了發膠、上面撒著紅紙屑,牽著狗、彈著吉他的小流氓,離了200米遠我就停下腳步,讓他們先走,不去惹他們。因為我知道,他們要是打了你那是白打。
一天我剛到宿舍,樓下有人說有電話找我(那個時候還沒有手機)。結果我一接電話,原來是我在英國考雅思時的老師,一位叫馬美麗的英國人,她和她愛人曾在北京住了三年。兩口子請我到他家去吃餃子。吃飯時,我問他們:“你們在北京三年,最難忘的是什么呢?”馬美麗沒有說長城,也沒有說烤鴨,而是深情地說:“晚上12點我敢騎著自行車滿北京溜達。世界上任何一個城市,特別是首都中心城市,是根本做不到的。”我們中國的治安由此可見一斑。
我從英國學成歸國的時候復印了70公斤資料,都是外國最新的有關警察科技的專著。我回來用了4年寫出我國第一本警察理論專著,叫《英美警察科學》。這本學術著作全面系統地研究了西方警察科學,并搭建了研究西方警察科學的理論框架,創造性地翻譯了60多個西方警察科學的專有名詞。應當指出,我們國內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大部分都是清末從西方引進的。但是,由于那時西方警察科學并不成熟,加之1949年前關于西方警察科學的翻譯和引進的大部分成果都被帶到了臺灣,所以引進西方警察科學的歷史重任就必然落到了新中國警察學者的肩上。
起初有的臺灣學者看不起大陸對警察學的研究,但后來我有個研究生在圖書館看到臺灣人寫的一篇論文,說:大陸有一個人叫“王大佛”,他寫了一本《英美警察科學》讓我們臺灣的警察學者都汗顏。為什么說叫“王大佛”呢,是因為“王大偉”的“偉”字是簡體字,臺灣人不認識,以為那是“大佛”的“佛”字。
無論是犯罪學還是警察科學,大家可能都知道一個美國的學派叫“芝加哥學派”,它是20世紀20年代形成的,主要研究的是城市和犯罪的關系,最有名的理論就叫“同心圓理論”。芝加哥學派認為城市犯罪率比較高的地方往往是城鄉接合部,相當于北京四環、五環的位置。
芝加哥學派最后一個掌門人叫沃爾夫岡,1985年我在日本念書的時候,沃爾夫岡就是我的老師,所以我和芝加哥學派還是有一定淵源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20世紀80年代左右,北京西城區木樨地曾經醞釀了一次學術的爆發和革命,那就是“木樨地學派”。
當時在木樨地也就是今天公安大學的附近,聚集了公安大學、司法部勞改勞教研究所、公安部某研究所等諸多關于犯罪學的研究單位,出版了很多學術研究雜志,比如《公安研究》《世界警察參考》《勞改勞教研究》和一系列學術專著,承擔了國家“七五”課題,叫《中國現階段犯罪問題研究》。這是改革開放以后第一個最重要的犯罪問題科研項目,當時在公安大學建立了當時中國唯一的犯罪數據統計研究中心,有 15個年輕人參加這項研究,我有幸成為其中的一人。
我們主要進行實證研究和犯罪數據統計研究。1980—1987年,我們在我國15個省、直轄市公安廳(局)建立相應的組織機構,把新中國成立以來大量的犯罪統計數據、原始資料輸入計算機,這在當時的中國是非常超前的,僅輸入計算機這一項就干了5年。
研究中,我們發現了犯罪學中很多前人沒有發現的規律。
比如,犯罪時間分布規律,又稱“犯罪月歷”。我們輸入計算機的數據大概有幾萬個,經過分析研究之后,發現各類案件在每個月份中的分布是不一樣的。
比如說,我們現在在講課中常用的那個小歌謠,叫:
平平安安三月三,
四月五月往上躥,
夏天多發強奸案,
冬季侵財到峰巔。
這就是根據當時一系列數據與圖表總結出來的。
一般來說,全國氣溫最高的一天之后再過15天,強奸案統計達到最高峰,這在以前的犯罪學研究中是沒有的。
首先,夏天“青紗帳”長起來,犯罪分子容易隱蔽隱藏和接近女性;其次,在農村夏天晚上很熱,所以女孩子睡覺有的時候不關門不關窗,在城市,特別是“三大火爐”,有的時候女孩子甚至會在街上睡、在街上乘涼。這些現象包含了社會學、氣象學、民俗學等諸多因素,這段時間中會出現犯罪率的小幅上升。
又如,犯罪空間分布,又叫“犯罪地圖”,包括“兇殺通道”分布與“販毒鐵錨”分布。
1998年,我去芬蘭赫爾辛基的歐洲和北美犯罪預防研究所學習和工作。去之前,研究所所長馬蒂鳩森對我說:“大偉,你到我們這兒來,我就把我們最新的成果展示給你。”他們主要研究犯罪的時間與空間分布,很多結論與我們的研究趨同。但我一看到心里就笑了,我們的數據樣本比他們多得多,而且我們的結論、公式不是一個兩個,是幾十個。這時候我才知道,我國的犯罪學研究,特別是實證研究和統計數字的研究,曾經領先于世界十年以上。
“木樨地學派”不僅限于中國的犯罪的犯罪學研究,還是引進西方警察科學的中心。當時公安部某研究所與公安大學合并,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比較警察的研究機構,叫“中外警察比較研究室”,出版了《公安研究》《世界警察參考》等學術雜志,更重要的是當時還出了一個英文版的《中國警務研究》,我們叫做“小藍皮本”,曾經賣到美國,很受歡迎。
英國的兒童安全教育一直長期領先于我國。無論是從安全教育的理念,還是具體操作的方法,都有其獨特之處。所以我回國后也積極地引進了西方警察在兒童安全教育方面的理念和操作。
我國警察的平安警語是向英國警察學習的。英國平安警語的特點是:一句簡單的話,用詞越少越好;具有可操作性而不是空泛的話;平安警語必須是從犯罪的案例中提煉出來的,絕不能是憑空想象,要有具體的防范對策和科學依據。比如,針對盜竊犯罪,英國警察的平安警語是“不帶今天不用的錢”,而中國警察的平安警語是“民警同志提示你注意錢財”。
我們根據兒童的特點,仿照英國警察的平安警語,在多年的教學實踐中總結出十句平安警語:
1.背心褲衩不許摸。
2.向陌生人說不。
3.壞蛋可以騙。
4.堅決不打黑車。
5.小小秘密告訴家長。
6.發生突發事件可以自己逃生。
7.一定要走斑馬線。
8.火災來了,彎腰捂嘴往下逃。
9.學會見義勇為。
10. 緊急避險時可以打破常規。
后來,平安警語又發展到平安童謠、平安童話。有的時候我們到幼兒園、小學去講案例,一講到小女孩被性侵害、小男孩被壞蛋劫走,很多小孩馬上就說“我不聽我不聽”,有點兒害怕。我們就把現實生活中血淋淋的案例變成童話,讓小朋友聽了哈哈一笑,又學了平安知識。
后來,我又發明了平安童操,這在世界上都是首創的。做這項工作,一是受到了英國警察的啟示。我在英國時,看到英國警察巡邏的時候常會帶一個小玩具,比如小熊,綁著一條白色的緞帶,上面寫著一句話叫Say no to strangers,翻譯成中文就叫“不和陌生人說話”,還有的上面寫:“小褲衩、小背心兒神圣不可侵犯。”我借鑒這些,編了一個小童謠:
小熊小熊,好寶寶,背心褲衩兒都穿好。
里邊不許別人摸,男孩兒女孩兒都知道。
二是當時福建南平出了一件事。有一個犯罪分子早晨跑到一個小學門口,等7點半一開門,53秒鐘殺害了13個孩子。當時很多孩子不會保護自己,有的孩子不會跑,甚至有的還從遠處沖著犯罪分子跑了過去。所以我連夜就編成了兒童平安操,以平安童謠為基礎,朗朗上口,配上音樂、配上動作,以此來教育兒童保護自己的安全。
就這樣,我們創造了平安警語、平安童謠、平安童話、平安童操等一系列兒童安全教育的好方法。可以說,在這個領域中,我們趕超了歐美國家的先進水平。
(摘自《縱橫》2018年第11期。作者為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一級警監、中國青少年犯罪學會常務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