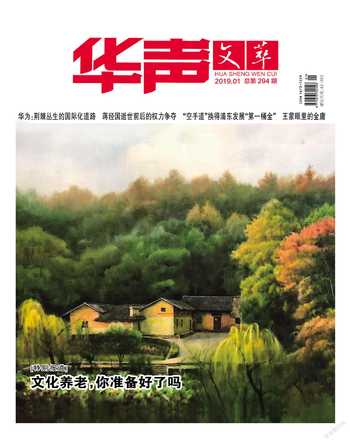父親腦海中的橡皮擦
郭娟
從客廳到廚房,再到陽臺,現在是父親的疆域。
自從前年冬天在酷寒的夜里險些找不到家,父親就很少下樓了。之前他還能到附近市場買菜,或到餃子館吃午飯。父親經常拿著百元大鈔買幾根蔥或買二斤肉,不等找零就走了。父親一度天天買肉、絞肉餡,冰箱都裝不下了;一度愛買香其醬,家里經常放著十幾袋。我們說,就當是父親撒些零錢做善事了。那時父親還能下樓走動,還能走回自己的家。自從那次找不到家,冰天雪地里凍了大半夜,父親已經沒有外出的欲望了。
家里空蕩蕩的。上班上學的走了,從早6點半到晚6點半,父親在他的疆域里巡視,無人說話。電視漸漸也想不起打開看。漸漸地,父親的腳步慢了,一點一點地挪動。一點一點挪,有可以扶的桌、柜、墻,他都依靠著;無所依靠時,就擺動著胳膊,邁著京劇里老員外的那種步子,慢慢地晃著、挪著。我知道以后打電話,要等著多響幾聲,等父親從沙發里艱難起身,一步一步來接電話。
父親一步一步挪過長長的客廳,到他轉進廚房,我可以看完兩頁書。我悄悄起身,跟過去,看見父親在廚房里這兒摸摸,那兒摸摸,又挪到陽臺上,不知要干什么,也是摸摸,撫撫。然后轉回來,站在臥室門口,停下,半天一動不動。父親一生勤勞,白天從不肯上床睡一會兒,雖然現在他更多的時候是坐在沙發里打盹。
睡著的父親還像是原來的父親。他腦中的那塊橡皮擦是一刻不停地擦著,還是也有時停一下?最初,擦去一點記憶時,誰也沒有察覺;等到又擦去一些,父親就失去了對時間的感知,常常把一日當成幾天;漸漸地,在親人的錯愕和輕忽中,父親對于自己的記憶失去了自信。
目前,父親還認得大部分親人,我不敢想那一天,當他不再認識我們時,在他的意識里究竟是完全不想我們,還是焦灼地找卻找不到我們。我盡量不再回憶父親以往的叱咤揮灑、談笑風生,也不愿預判他的未來,預支悲傷。誰不是百年過客?生命本是向死而生的一次逆旅。當我有機會和他在一起,我就快樂地、溫柔地待他,尊敬地對他,耐心地和他聊一聊。那些還沒有被擦去的往事,是我和他棲息的花園小島,一片溫馨——盡管這個小島終將被淹沒。
我離家那天的午后,父親坐在窗前,背對著我,望著外面。我走了,父親不知,也許這朝夕相處的三天也已經忘了。我說:“爸,8月我還回來看你。”他鄭重而干脆地說:“好!”
我不知他能否記住對我的期盼。
(摘自《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