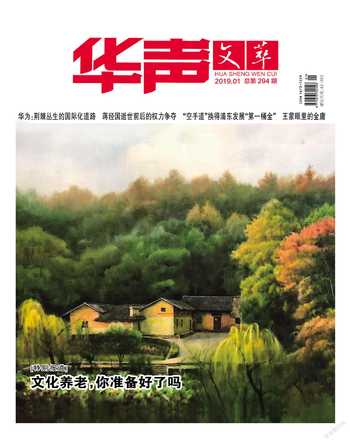曹禺與萬方:“扭結”了一輩子的父女
1952年出生的萬方,1969年到吉林省扶余縣插隊。那段日子里,對父親的回憶就像開著的機器,在她不注意的時候反復播放著:父親在給她和妹妹講自己編的故事,他講得那么生動、迷人……那些記憶在她心中散發出愛的光芒,讓苦難也有了美麗的色彩。
那時,萬方雖然有個“反動學術權威”父親,但畢竟比一般“狗崽子”運氣要好一些。沈陽軍區前進歌劇團的政委顏庭瑞也是作家,非常崇拜曹禺,他冒著風險想為他景仰的前輩做一點事情,于是便把萬方從農村調出來搞創作。想不到的是,這一調動改變了萬方的命運,1979年,萬方轉業回到北京,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了專職作家生涯。
萬方步入文壇,原非父親所愿。曹禺深知文學藝術創作過程中的艱辛,且又沒有統一的評判標準可循,因此他更希望孩子從事自然科學。尤其是曾遭受一系列“莫須有”罪名的摧殘之后,他更希望孩子做一些“有明確標準”的工作。
然而,萬方有著自己的苦惱。萬方從小對數學就充滿挫敗感,與此相反,文字創作的基因對她的影響卻頗大。從上小學開始,萬方就經常寫一些作文和小詩,但當時她還沒想過將來要成為一名作家,在她幼小的心靈里,作家的稱號是只有像父親這樣的人才當之無愧擁有的。
陰差陽錯,20世紀80年代初,萬方開始寫小說了。看過她第一篇發表在雜志上的作品《殺人》后,曹禺說:“你真的行,你可以寫出好東西了。”
從此,萬方每回創作,總忘不了悄悄思忖———父親看過之后會怎么說。萬方筆耕至今已超過40年,她的大多數作品如《空巷子》《空屋子》《空鏡子》《香氣迷人》等都是專注于女性題材的,其中一些還被改編為影視劇,獲得了不錯的收視率。
萬方承認,她對于愛情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受家庭的影響。父親曹禺有過三次婚姻,萬方的母親方瑞是父親第二任妻子,因病于1974年去世。1979年,69歲的曹禺又和56歲的李玉茹結為夫妻。其實,早在1937年,曹禺和李玉茹就已結識,成了亦師亦友的知心人,然而由于種種原因,兩人沒有能夠在一起。沒想到這段姻緣卻在兩人都步入晚年時得以繼續。萬方回憶:“我的繼母李玉茹那時是上海京劇院副院長,又是名角,但為了照顧我的父親,她放棄了很多。”不過萬方也體會到了李玉茹的那種滿足。直到去世前兩天,李玉茹還對萬方和小女兒李如如囑咐,要她們多看看當年自己和曹禺的通信———那整整一大箱子的通信,每一封都代表著她得到的幸福愛情。
萬方的第二任丈夫因癌癥去世,在帶給她極深悲痛的同時,也使她開始反省人生。“我愛人在的時候我們也會爭吵,當他真的病了,走了,才發現一切都是那么值得珍惜。現在我明白了,夫妻間,要接受對方和你的一切差異,多一些寬容,多一些理解,這也是為你自己好。”
(摘自《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