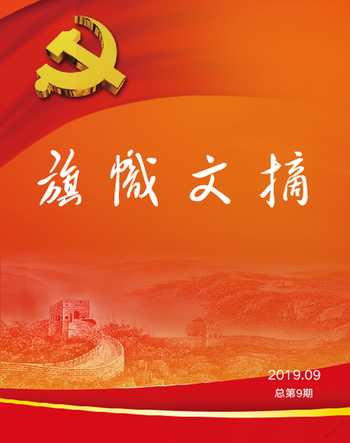杜潤生的兼容哲學(xué)
宋春丹
2018年12月18日,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杜潤生被授予“改革先鋒”稱號,并獲評“農(nóng)村改革的重要推動者”。
杜潤生,原中共中央農(nóng)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wù)院農(nóng)村發(fā)展研究中心主任,從1982年到1986年參與主持起草五個“中央一號文件”,確立了“包產(chǎn)到戶”的合法性,被譽為中國農(nóng)村改革的“總參謀長”。
1979年2月,剛剛成立的國家農(nóng)業(yè)委員會正式開始辦公,王任重為主任,杜潤生是三個副主任中排名最后的一個(后又增加了兩個)。
杜潤生畢業(yè)于北平師范大學(xué)文史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領(lǐng)導(dǎo)了中南新解放區(qū)的土改運動,提出給農(nóng)民“四大自由”——商品交換的自由、借貸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關(guān)系的自由。在農(nóng)業(yè)合作化運動中,中央農(nóng)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和秘書長杜潤生都主張不要冒進,堅持自愿原則,受到毛澤東批評,被指責(zé)為“像一個小腳女人”。
杜潤生被趕出農(nóng)村工作部門,調(diào)到中國科學(xué)院擔(dān)任黨組副書記兼秘書長。對于自己66歲重新出山、回歸農(nóng)口,風(fēng)向雖變,但矛盾依然尖銳。其中,是否實行“包產(chǎn)到戶”是爭議的焦點。
1979年3月初國家農(nóng)委召開的七省三縣農(nóng)口負(fù)責(zé)人座談會,是矛盾的一次爆發(fā)。會上,安徽農(nóng)委副主任周曰禮極力主張包產(chǎn)到戶,湖南農(nóng)委主任等跟他激烈爭論,差點拍桌子動手。杜潤生除了偶爾插話,基本沒講什么。
為了準(zhǔn)備會議紀(jì)要,杜潤生一天晚上召集劉堪等幾名農(nóng)研室工作人員開會,并著重交代,對包產(chǎn)到戶要有個“說法”。
兩小時后,初稿擬出。明確規(guī)定“不許分田單干”,初稿回避了包產(chǎn)到戶的問題,兩種意見都講,請中央定奪。
杜潤生對此并不滿意。沉默近半小時后,他提到座談會上有人發(fā)言說,貴州山區(qū)一些住在大山頂上的苗族農(nóng)民、西北山區(qū)住在遠(yuǎn)離生產(chǎn)隊的“吊山莊”上的一些村民從不參加集體勞動,自種自收,每年向生產(chǎn)隊交些玉米即可,提議在“孤門獨戶”上做文章。
向中央?yún)R報時,這一表述順利獲得了通過,并被寫進入會議《紀(jì)要》。1979年4月,中央批轉(zhuǎn)該會議《紀(jì)要》,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允許在特殊地區(qū)實行包產(chǎn)到戶。
受黨中央、國務(wù)院委托,杜潤生每年主持召開一次全國農(nóng)村工作會議,就農(nóng)村工作起草一份戰(zhàn)略性的“一號文件”。
杜潤生喜歡組織各種座談會。會上交鋒激烈,有時甚至像在吵架。杜潤生自己很少講話,尤其不做結(jié)論性發(fā)言,通常是聽完贊成一方意見后會說出幾條“擔(dān)憂”來,聽完反對一方意見后又會講出幾條“問題”來。
他主張“道并行而不悖”,見仁見智,相互容納。他說,千萬不要固化對事物最初的認(rèn)識,那往往是錯誤的,一定要在聽取不同意見中進行修正。
翁永曦回憶,杜潤生強調(diào)“反方向推敲”。一位農(nóng)業(yè)部副部長堅決反對包產(chǎn)到戶,但每次開會討論中央文件代擬稿時,杜潤生一定會請他參與討論。翁永曦感到疑惑,杜潤生告訴他,任何贊同意見都一定會有瑕疵,任何反對意見也一定會有某種合理成分,要最大限度地集思廣益,才能形成合力。
杜潤生極為敏銳,善于接受新鮮事物,對改革中出現(xiàn)的新詞匯新說法都能運用自如。翁永曦說,他善于提出中性詞匯,來凝聚黨內(nèi)外共識,是化繁為簡的高手。
杜潤生認(rèn)為,農(nóng)村改革最大的阻力是意識形態(tài),實際上只要熟悉農(nóng)村的人都知道包產(chǎn)到戶是有用的,關(guān)鍵是要說服各級領(lǐng)導(dǎo)干部。
1986年冬,正在施工的京西賓館新樓搭著腳手架。杜潤生指著腳手架對劉堪說,雖然新的農(nóng)村經(jīng)濟體制還沒有完善,也不能說運行機制已經(jīng)完備,但已經(jīng)有了新的框架。他們都覺得,用“一號文件”來專門針對農(nóng)村工作發(fā)文這個形式可以告一段落了,因為政策性、號召性的語言在這個階段已起不到思想解放初期那么大的作用了,今后需要的是專業(yè)性、操作性的文件,甚至專門的法律法令。
這五個中央一號文件下發(fā)后,杜潤生做了20多場輔導(dǎo)報告。萬里說,農(nóng)村改革中的理論問題,找杜潤生可以講明白。
杜潤生講話只說大白話,從來不念稿子,只有個提綱。如果是重要報告,會自己寫草稿,從不讓人代筆。
他的講話極具說服力,根據(jù)錄音整理出來,不用刪改就是一篇好文章。
杜潤生用人可謂不拘一格。翁永曦說,他對年輕人的重用程度在當(dāng)時所有中央部委里都絕無僅有。
1979年10月的一天,剛分配到《中國農(nóng)民報》做見習(xí)記者的翁永曦奉命將社論清樣送到國家農(nóng)委,請杜潤生審稿。正在看文件的杜潤生說:“小伙子,我沒見過你啊。”翁永曦說,自己剛來報社工作。“原來干嘛的?”“農(nóng)村插隊,八年整,十年頭。”
杜潤生讓他說說體會。他說:“農(nóng)村太窮,農(nóng)民太苦,我覺得國家農(nóng)業(yè)政策應(yīng)該建立在務(wù)農(nóng)有利可圖的基礎(chǔ)上。”杜潤生問他還有沒有第二條,他說:“有,我從小受到的教育是‘大河有水小河滿’。到農(nóng)村后才發(fā)現(xiàn),其實只能是‘小河有水大河滿’。”
這次對話不到五分鐘就結(jié)束了。一周后,翁永曦收到調(diào)令,去國家農(nóng)委工作。32歲的他,與39歲的段應(yīng)碧,都成了農(nóng)委里的“小字輩”。
1980年春季的一天,杜潤生把翁永曦叫到辦公室說:“上午到(姚)依林同志那里開會,中央決定今后十年對農(nóng)業(yè)投資1500億,讓農(nóng)委拿個方案,你去考慮一下。”翁永曦當(dāng)時是一個月工資只有46元的普通科員,剛到農(nóng)委工作幾個月,對杜潤生的重用感到十分意外。
1982年,國家農(nóng)業(yè)委員會撤銷,成立了中共中央書記處農(nóng)村政策研究室(1988年改稱中共中央農(nóng)村政策研究室)和中國農(nóng)村發(fā)展研究中心(1985年改稱國務(wù)院農(nóng)村發(fā)展研究中心),兩個機構(gòu)、一套人馬,杜潤生擔(dān)任主任。因為辦公地點在北京市西黃城根南街9號,“九號院”就成了農(nóng)研室的代稱。
翁永曦說,九號院的一個“怪現(xiàn)象”是允許大膽議論。當(dāng)時,九號院有“三允許”的不成文規(guī)矩:允許研究課題與當(dāng)前中央政策研究的重心不一致、允許研究的結(jié)論與中央的口徑不一致、允許在研究成果未被中央采納時保留個人意見。杜潤生要求大家把工作做活,還為機關(guān)調(diào)研工作定了一條:除經(jīng)中央正面定了的問題外,可以自由發(fā)表意見,說錯了也不要緊,思想要自由點、解放點。
杜潤生對自己70年的工作經(jīng)歷做了總結(jié):“第一條,苦勞多,功勞少;第二條,右傾的時候多,‘左傾’的時候少。”他說,自己還有兩個愿望:一是再轉(zhuǎn)移兩億農(nóng)村勞動力到城鎮(zhèn)去,二是要讓農(nóng)民組織起來。也許自己來不及看到了,有些任務(wù)要交給下一代。
在他的倡議下,設(shè)立了農(nóng)村發(fā)展研究專項基金,評審并頒發(fā)“中國農(nóng)村發(fā)展研究獎”,對在農(nóng)村政策研究、理論研究、調(diào)查研究、方法研究等方面有突出貢獻(xiàn)的優(yōu)秀作品進行獎勵。2004年12月,首屆“中國農(nóng)村發(fā)展研究獎”頒獎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杜潤生出席并頒獎。這是他晚年最感欣慰的事。
2015年10月9日,102歲的杜潤生在北京逝世。翁永曦送上挽聯(lián):兼收并蓄,有辦法使歧見趨一致;德高望重,無山頭卻門生遍九州。
(摘自《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