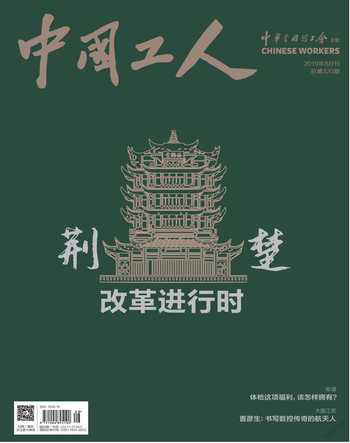為防文學放歌
阿瑩

我曾經為話劇《秦嶺深處》寫過一篇創作談,標題就是《我的血液里流淌著軍工情結》。當我那天接到一部凝結著軍工系統文學新人的作品集,沉甸甸的,墨香濃郁,心里便涌起一陣陣悸動,沉淀于腦海深處的記憶便一幕幕閃現出來,躲在廠房角落寫詩作文的情形也清晰得如昨天一般了。
記得我在十八歲那年的春天,走進了古城東郊的一家兵器企業,吞吐銅坯的軋機,咣當轟隆的沖床,熱浪撲面的退火爐,燈火通明的檢驗臺……便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那些閃爍著黃金般光澤的彈藥筒,便濃縮成了我筆下永遠的字符。
我是被軍工人的生命張力所感染而開始業余文學創作的。幾乎每個晚上我都會趴在窄小的工作室里,伴隨著叮叮咣咣的機械碰撞聲,一筆一畫描寫著滿身油污的工友和披著藍大褂的師傅,體會著他們的酸甜苦辣,感覺著他們的愛恨情仇。即使后來離開了那個企業,每每走過軍工單位的大門,心里就想進去看個究竟,想知道那導彈、那飛機、那雷達今日的狀態;每每與軍工兄弟在噪雜的小店里劃拳把盅,大碗菜端上來,筷子沒動幾下,便想脫掉衣服一醉方休;如今人們已經習慣用計算機敲打文稿了,對大大小小的印刷體已經麻木,沒有了奇妙的感覺,而當年我是多么渴望那歪歪扭扭的手書能夠變成鉛字,至今我還記得處女作在刊物發表時奔走相告的情形。
那時候我常常吃過晚飯便要趕回廠里,躲在一間小屋里,趴在一張小桌上,舞文弄墨爬格子,從晚霞褪盡,到滿天星斗,有時到太陽露頭,卻也一點沒有疲倦,天剛亮釘好稿件就騎上自行車,進城給編輯部老師送去了;或是裝進信封,貼上兩張郵票,投進墨綠的郵筒,常常半天盯著還不.愿離開,滿滿的期待便縈繞在腦際了。所以,那時我非常渴望能有個園地展示軍工人的文學耕耘。記得曾經有過一本反映軍工人創作的《神劍》雜志,給愛好文學的軍工人帶來諸多憧憬,盡管那個刊物曇花一現,但薄薄的雜志帶給人的激勵持久地留在了記憶里。
然而,月真的很無奈,我已經懵懵懂懂走過好多單位,經歷了難以言狀的磨煉,面對許多事物也變得遲鈍深沉了。但軍工情結卻是我不變的情懷,任何時候談起軍工,談起國防裝備我就像打了雞血,常常會賣弄地把支離破碎的軍工見聞一股腦兒顯擺出來,惹得滿屋人嘖嘖贊嘆,心里的虛榮也就得到了滿足。
也許正是這個緣故,我即使離開軍工企業多年,依然與基層的軍工人保持著熱絡的聯系,一年里若是沒有跟他們見面坐坐,喝杯酒聊聊天,心里便感覺空落落的。有人半開玩笑說,現在你們還能有多少共同語言,是那些人找你有事要辦吧?我說不是他們有事要找我,而是我的心靈需要他們的撫慰,思維需要他們的滋潤。千萬別以為他們說話粗俗冷噌,也別以為他們玩笑缺少分寸,其中的智慧和愛憐最為受用。一句話,與他們面對面,我感到踏實!
但是,匆匆掠過即將出版的《秦嶺深處》這部書稿章章頁頁,便感覺有股熱浪撲面,一個個字符就像安裝了發射藥的炮彈,生龍活虎地演繹起神秘的故事——有來自生產一線的詩作,那是機床邊的淺吟,是試驗場的低唱,是計算機里的音符,散發著并不遙遠的豪邁和柔情;有來自工廠車間的美文,浸透著油污和汗水,如同經歷了硝煙洗禮的捷報,可以感覺到苦澀和渴望;而最為新鮮的作品,是從廠房墻報上摘錄的行行字符,吐著火,流著汗,散發著濃濃的機油味,讓我恍如回到了青春歲月。
這些從生產線上流淌出來的作品,蘊含著軍工人特有的質樸,任何有良知的人面對這些文字都會肅然起敬。盡管有些作品還顯得有些稚嫩,而稚嫩正是卓越的萌芽,是作品真摯的活力,所有的成熟都是從稚嫩走來的啊。毋庸置疑,隨著歲月年輪的增添,我們的軍工人一定會愈寫愈老辣,一定會為文壇增添一道道靚麗。
所以,我們應該為呵護軍工文學的國防工會鼓掌!也應該為創造了卓越的軍工人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