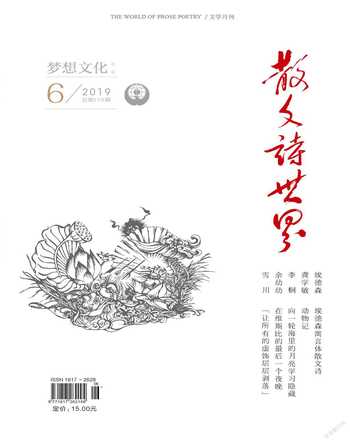我的詩歌進階史(創作談)
吳辰
我的處女作發表于16歲那年,是一篇小散文,為當時的同學也就是現在的愛人而寫。現在讀來,很是稚嫩,但是語句詩化,情感豐盈,應該是受了彼時好讀散文詩和經典散文的影響。有人說,好的文字必定是情感豐盈的文字,畢竟情感欠缺的作品,即便再講究技巧,也只是一具漂亮的軀殼。嘗試寫詩也是從高中時候開始的,學生時代主要寫些自娛自樂的小情詩,很少關注那些大的東西。2011年我開始系統性地業余撰稿,主要寫些副刊體的散文、詩歌和小說,前期主寫散文,近年來主寫詩歌。這些副刊體文字很受報刊歡迎。剛開始我還自鳴得意,為大量作品的發表,但后來覺得不對勁,因為極少有知名純文學刊物用我的作品,作品同質化也很嚴重,很多詩都是為了寫而寫,或者為了迎合報刊而寫。我開始去研讀那些純文學體的詩歌,并反思寫詩的意義在哪里,以及好詩的標準是什么。
在我眼中,好的詩歌一定是有好的詩句和好的立意的。好的詩句給讀者美育,好的立意給讀者德育和智育。我比較喜歡胡弦和劉川的作品。他們這個年紀的經驗、思想以及自身與外界的融合都很成熟,作品力道十足并且都擁有極高的辨識度,最重要的是我能看得懂,并且能從中得到觸電式的感悟。胡弦的詩頗具中國古典美和古詩詞節奏感,這肯定是吸收了很多古典精華的結果。劉川的口語詩短小但極富哲理,讓人過目難忘,驚嘆不已。我也關注了幾個走歐美路線的詩人,他們的作品受譯詩影響很大,多有晦澀,說實話,我不太懂,更不能從詩中獲取什么經驗。再回過頭來看自己以前寫的那些副刊體詩歌,更覺不堪,一部分與詩歌主編李云口中的“小情緒詩歌”別無二致,另一部分非真情實感之作,不具備文本的檔案性。寫詩還是要關注那些大的東西的,比如蒼生、生死、苦難、現實、堅忍、母性等等,也必須要保證真情實感。從個人的小情緒中走出來,走向真實而磅礴的人間,其實就是一個詩人成熟的過程。
寫詩對我來說不是全部,但非常關鍵。曾有一段時間,我走在人生低谷,舉目四望,全無依靠的時候,是寫詩給了我前行的希望和力量。我一直認為作家和詩人是幸福的,因為人人會死,絕大部分人離開人間了,不會留下什么,但作家和詩人不同,其作品會代他們繼續活下去。寫詩也讓我找到了自身的另一種價值。近年來創作有了一點小成績,有了自己的讀者,創作也有了使命感和責任感。本次發表的這組詩其實是我近期生活感悟的一個集合,從身邊熟悉的小事物、小風景、小片段入手,展現它們與人之間的聯系,在它們自身的規律和特質上找到發光點,通過詩句將這些發光點變成一盞盞燈,希望讀者能夠看見。
萬物皆有靈性,我只是代其發聲。用心去觀察和感悟周遭事物,走進它們的身體里,你也會看到不一樣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