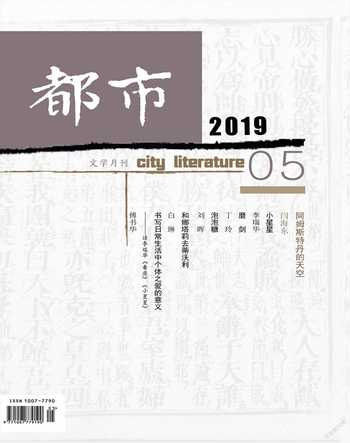看房
李瑞華
她把昨天早上剩下的半碗豆漿和一個豆包加熱,做為早餐,慢吞吞吃下。丈夫照例不在家吃,他要出去吃街上的豆腐腦,他總是不虧待自己,總是這樣。
她吃早飯的時候,他背著包,換好鞋,站在門口,臉上帶著對她慢速度的忍耐。如果是往常,他會抱怨幾句,不過今天他沒有。然而她還是略微加快速度,并且在吃完以后沒有洗碗,把它們放到水槽,迅速去刷牙,拿包,換鞋,出發。在她刷牙時,他開門走出去,拎著一袋隔夜垃圾,說先去樓下扔垃圾去。她嗯一聲,牙刷里傳出的聲音不像她自己的。
他五十二歲,她五十歲。不夠老,也早已不年輕。出發前,她在門口照照鏡子,站定,自嘲地笑一下。的確,她不漂亮,不年輕,唯一可以自傲的瘦,也漸漸消失,被下垂的贅肉所掩埋。瘦,在年齡增長后,一度讓她的臉部凹陷,兩腮尤其嚴重,發福之后,這凹陷沒有被填充起來,反而在地心引力的作用下,越發向下,成為被歲月泥沙不斷沖襲過的溝壑,成為坑洞,嚴重影響了年輕度;贅肉讓臉變長,小腹變突,腰部失去線條,大腿松弛粗笨。不過她仍然持有自信,她喜歡不像以前那樣總是生氣的自己。她對目前的現狀很滿意。
除了房子。
沒有他的催促,她下樓速度又慢吞吞,剛才,她分明是在給他表演,正如他常常這樣表演給她看,表演是融合劑,是給對方面子,也許對方對這些把戲心知肚明,但都不去戳破。少些沖突,多些迎合,正是為了便于在更多的時候,各堅持各的。婚姻自有玄機,高手過招,招式眼花繚亂,卻是在用心過。用心過招,說明彼此對家庭,對對方,都有讓步。讓步是婚姻的最大美德。
她家住在六樓,兩個臥室都在東面,她年輕時,最喜歡每天充斥在房間的陽光味道,陽光照得人身體發癢,七色陽光曾經有好幾年讓她對生活產生嚴重誤解,以為未來會充滿希望。后來,令人沮喪的失望之旅開啟后,真實人生列車載著家庭沉悶向前,陽光強烈時,她習慣選擇關上窗戶,拉上窗簾,把一些不合實際的希望遮擋在外面。失望是希望帶來的,正如離婚原因是結婚。同理。
下樓時間,不是在某一天變長,是越拖越長。當初買房時,他們已經有孩子,從租的房子搬到這里,他們多么快樂,他們三個飛快上樓,跟踩著云朵一樣飛快,女兒兩歲,胖乎乎,時常被他抱著上來,不算個事。
年輕,快樂,那時是這樣。
她自嘲地笑了笑。這時她已經下到二樓,腿有點不聽使喚,下樓都有點累,上樓就更累得厲害。這個磚混結構120平米的房子,質量一般,當時貪著樓層高價格便宜,買的頂樓,這會兒,后悔也來不及。年齡越大,上下樓越是吃力。年輕人蹬蹬蹬上樓,聲音先是在他們身后,然后就跟他們擦肩而過,他們都自覺停住靠在一邊,讓那些年輕的腳步先走。
有那么幾次,他不服輸快步沖上,想要一鼓作氣走到六樓,她跟在后面,拿著買菜的籃子,看著他離開自己,超過自己,他氣喘吁吁的聲音讓她心驚,他站到門口,確實是比她快了那么兩三分鐘,可是他喘息著,手腳都抖,半天連鑰匙都拿不出來,有一次,他在四樓絆了一跤,滾落到三樓,右腿骨折,在家休息好長時間,他幾乎憋瘋,每天想下樓,可她一個人,怎么能把他弄到樓下,即使找鄰居幫忙背到樓下,那么又需要找人再把他弄回去,這年頭,誰愿意干這些體力活,欠人情的事,他們自己也不愿意做,他們都是普通的人,拿什么去還別人的人情呢?他們一窮二白,沒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東西幫助別人。
后來上樓,他們倆都會小心翼翼,走累了,休息一下,再往上走。他性格急,可是也不再快步走,受傷后在家待了將近一百天所帶來的煎熬,對他是個教訓和警示。
所以當他終于提出重新買房時,她沒有理由反對。
理由其實也有。比如,錢。
錢怎么辦?她仿佛自語地說。她自己沒有私房錢,家里所有的錢他都知道。夠買一個差不多的房,可是,那大都是她兼職所得,是早已計劃過,給女兒以后買房時添補。女兒已經在上海就業,成家,還沒有房子。所以,女兒女婿結婚四年,還是不敢要孩子。
他皺眉。他不是不想管女兒,他認為這件事應該由女婿家那邊負責。
“給他們添上點,也不能全給他們。”他皺著的眉頭沒有松開,電視里,一頭鹿正被一頭壯碩的獅子肢解,她扭過頭,手里拿著一件舊睡衣,準備去洗澡。
她覺得自己是那頭鹿,被他撕扯,他除了賺死工資,什么來錢的地方都沒有,她恨這個。
可是,她又何嘗不是被女兒女婿撕扯,她這么想了一下。這么想讓她有點罪惡感。
買個二手房吧,她提議后,懊惱地低下頭去,忽然就不想洗澡了。她來到洗手池旁邊,拿起拖布準備拖地,可是努力半天后,客廳里的地板磚依然暗淡無光,怎么也拖不出來本色,她泄氣地把拖布扔到桶里。
他的身體擺放在沙發上,和贅肉、下垂的臉、半禿的前額,一起在沙發上釋放重量。他沒有回頭,他認命地回答,不然呢。這三個字,代表對買二手房的無奈和認定。
于是,他們不得不去看一個又一個二手房。今天,也是這樣。
到了樓下,她已經看到他在掉好頭的車里玩著手機。她走近車,從后窗到副駕駛,他沒有抬頭,她明明在打開車門上車的一瞬間看到他在手機上打字聊天,不知道跟誰,可是一待她上車,他已經切換到游戲。他和別人聊天,和她卻無話。每天上下樓的疲憊讓兩個人的力氣都消失殆盡了嗎?
手里的游戲以失敗結束后,他發動車。他忘記了剛才還在催她快走。
他窮,年輕時有的,就只是力氣。沒有孩子之前,他背著她走路,抱著她過河,用一句流行語就是,一言不合就舉起她,抱起她。她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是一個愛撒嬌的人,她在他面前,嬌滴滴的,以各種借口賴著少走路,少干活,把出力氣的活計全交給他來做。他也樂顛顛全部都接受。主動,快樂去接受。
有了孩子后,他就背孩子,抱孩子,她也不再讓他背讓他抱。她獨立起來,強大起來。有一天,她做好飯,洗好碗,拖完地,去給孩子輔導作業,驚覺他從接孩子放學后進門起就一直在沙發上坐著看電視,吃飯時都是把碗端到那里去看。
什么時候,這一切成為了習慣?那天天很熱,家里還沒有安空調,她累,又熱,有點眩暈,感覺恍若夢境。
他們現在去看房。
說過看房后,他們已經看了很多房子,但都不合適。第一個房,房主不出現,交給中介公司來交涉,房子是早年裝修好的,一直對外出租著,他們去看房時,租客窩在沙發上看電視,冷冷地接待了他們,正是中午,是午睡時間,雖然覺得不合適,但租客說只有這個時間他才在。
三室一廳,一間門被出租人上鎖,一間靠北的床上躺著一位午睡的老太太,瞇著眼睛,聽不到她的呼吸,身上蓋著一個粉色花團錦簇的舊毛巾被。可能是這位年輕租客的母親。第三間空落落的,擺著一個窄而滑稽的柜子,一個鋪著油膩床單的雙人床。凌亂的陽臺上晾著四件衣服。沒有一件衣服有女性屬性。她搞不明白,這個家里為什么沒有年輕的女主人,也沒有孩子。但不方便問。他們致謝,說了抱歉打擾,就離開。
價格要得不低,裝修卻很爛,不合適。
他們定位是高層,有電梯。二手,價格便宜,安靜沒有噪音。就只這三項,可一直沒有達成心愿。總是這樣那樣不合適。他漸漸急躁,不像她一樣不溫不火,他卻還為她不溫不火感到惱火,仿佛沒有合適的房子是她的錯。也許真是這樣,有個房子,他真的覺得可以,但是她認為不行。那所他認為可以的房子,如果買下的話,那就得把她計劃內給女兒的三分之二都要截掉。她怎么忍心。
女兒出生時,全家在租的房子里住,房東就在對面,是個年齡在六十歲左右的離異男人。老婆帶孩子和存款走后,給他留下一套房子,拆遷時,一座房子變成了兩套,在一樓,面對面。兩套新房,他沒有錢全部裝修,就把西面這套租出去,自己把東面簡單裝修后住進去。
西面就是他們的婚房。結婚時,他們把地上鋪上廉價的地板革,地板革上印著棕色方格花紋,墻上滾上白色乳膠漆,客廳和臥室都在墻上釘幾個釘子,掛新婚照片,后來又掛上女兒百天、周歲時的照片。房子里只放著幾件簡單家具,連梳妝臺都沒有,連鏡子都沒有。房東在過道里一面墻上安裝了一個長長的穿衣鏡,她每天上班前,都在那里匆匆地看看自己。她總覺得,那邊獨居著的房東,會從貓眼里偷窺她。她像個小兔子一樣在鏡子那里逗留一下,便飛快地從鏡子里一閃而過。
后來發生了一件事,證明她的猜測是有道理的。
那天他開早會,六點多走了。她七點起來,吃過早飯,把昨天買的紅色連衣裙穿在身上,從家里走出來。她要照鏡子,照鏡子是對新衣服的起碼尊重。
她站在鏡子那里,比平時站得久了些。陶醉在自己的小虛榮中,以至于她并沒有聽到隔壁那個六十歲的房東什么時候開門出來的,他從她身后把她攔腰抱住,胳膊把她抱得緊緊的,她掙扎著不能喘氣,只有他們兩個人,除了她自己,誰也不能救她。她臀部被頂得生疼,她叫喊,掙扎,都無法掙脫,帶著霉味的氣味在她身后升騰起來,是這個獨身男人常年在自己房間里捂出來的味道,和廁所里的蛆蟲一樣,讓人渾身不適,劇烈厭惡。有個瞬間她看到那男人出現在鏡子里,半張著嘴像要吃掉她的某一部分。她怕得發抖,不過很快那男人就溜走了,她聽到他忽然松一口氣,飛快地松開她,閃向東面,啪的一聲關上房門。
鏡子里又是她一個人,仿佛剛才什么都沒有發生過。她本應該立刻逃回自己的房間去藏起來,可她還仿佛在一場噩夢中醒不來。她看著鏡子。鏡子不因它所照射過的高尚而高尚,也不因它所照射過的齷齪而齷齪。新裙子皺了,她下意識伸出右手在后面摸了一把,立刻摸到了黏黏的東西。
這件事她沒跟他說過。她得忍下來。她后來每次上班下班都盡量和他一起回家。他說她變得黏人了,她也不解釋。她也知道該搬家,可是,找同樣租金和地段的房子,哪有那么容易,況且,搬家也是要花錢的,她折騰不起。
他說跟著他委屈,她說,我愿意。說這話時,是結婚第一天,聽她說完,他背著她在屋子里繞了足足有十圈。五十多平米的小房,總共走不了多少步,可她還是心疼她。她讓他放她下來,可他說,不累。
他們都是死工資,家都在外地,家庭條件都一般。生女兒后,雙方父母各自錯開時間來住了幾天,分別離去,都不習慣這里的熱,的確熱,沒有鄉下涼快。她懷孕后辭掉工作,到女兒兩歲半全托時,才重新找工作,工作之外,又找了兼職。她一步步這樣往前走,誰不是這樣呢?她這樣想。但也知道很多人其實不是這樣。可她又想,大部分人不都是這樣嗎?于是她就繼續這樣走下去。抱著一條道走到黑的決心和堅韌。
二十分鐘后,他把車駛進一個半新不舊的樓盤,他帶著不耐煩的小心,刻意的小心,很多年少見的小心對她微笑,眼角皺紋越發明顯。她不知道他這態度因何而起,他很少因為她賺錢多而對她抱著尊重,反而很是不平。他只有在利用她時,才有這份小心。她不知道今天為什么這樣。
最初,是這樣嗎?是她愚鈍嗎?年輕時,她認為自己雖然不漂亮,但睿智,聰明,認人不至于出太大錯。他雖然沒有錢,沒有太大能力,但是,他純粹,他對她,實心實意。找個對自己好的也行,她這樣想。沒有錢可以賺,沒有能力,可以磨練。誰生下來就什么都會呢。她把自己嫁給了他,跟著他往前走。她沒有預料到,她看人的眼光確實是對的,但她對事物發展的走向卻判斷不力,沒有錢,缺少能力,在他兩鬢斑白時,還是沒有改變,對她好這一項,如果她不想徹底認輸和承認失敗的話,那么算還好吧,沒有家庭暴力,沒有放棄責任,他心里,總歸是有這個家,每個月,工資都是往家里花。
這是對人生的總結嗎?她其實是好強的人,不愿意承認失敗,不愿意認輸,她告訴自己一切還好。就是因為如果她說了不好,承認了不好,她的人生就成了蔫掉的黃瓜,黃拉拉干枯了,敗相很難看。撐著不斷,不爛,還是很難看。她不想面對這個結論。她有權利給自己的人生下結論和做注解,除了她自己,她認為誰都沒有資格。他也沒有。
他們走進這座半新不舊的建筑,走進某個單元,在東邊,幾單元的痕跡已經模糊看不清,她注意到樓下角落里放著一個黃色的三輪車,似曾相識。她沒去多想。她看到單元兩個字樣,心里想起女兒,她女兒小時候,總是把單元兩個字認成草原,女兒好可愛,讓她忘記很多煩惱,像陀螺一樣圍著孩子勞作。一直到她長大,時光飛逝,她考入上海一所大學,二本。又在那里就業,戀愛,結婚。
想到這里她又開始陷入憂愁。女婿是外地人,家境一般,房子是他們面臨的最大問題。她原本想著,把自己現在住的六樓賣掉,再加上攢下的錢,都給女兒,自己租房去住。可是現在,他不肯這樣,要換房子,要買房,即使是二手房,也得費一番周折,簡單收拾,搬家,置辦新的東西,什么都得花錢。現在的六樓是老房子,賣不上價錢,如果換房,恐怕還得貼補進去一些房錢。她想租房,現在就租房。可是她盡量順從,盡量照顧他的自尊心和想法,她一直是這樣跟他相處的。她不想麻煩。
女兒去年懷孕,誰都沒告訴,自己一個人去醫院把孩子打掉。打掉回來住了半個月,讓她一起瞞著女婿,只說工作累,想在家休息幾天。因為沒房,女兒不敢生孩子,她很生氣,可女兒說,怎么可以讓孩子一生下來就吃苦,怎么可以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女兒總是這種論調。好多人都是這樣論調,讓人惱怒又無理由解釋和化解。她只怪自己沒本事給女兒好的起跑線。她不怪他。她自己選擇了他,他也是她的另一條起跑線,她不承認輸。她沿著這條道走著。繼續著。
看房之初她就不熱心,看了兩套,三套,四套,五套之后,她更失望了。他們的車就是個二手車,當初他軟磨硬泡非要買,女兒大學快畢業時,她把自己辛苦攢下的一點錢拿出來,買了車給他。現在,又得重新買房,又得動她的錢,她無奈。她任由他帶著他進入一個又一個二手或者三手的房子。她每次都充滿期待走進去,她想象著里面住著的人,一對年輕的夫婦,有一個兒子,并且是會彈鋼琴的兒子。她不知道為什么會想當然認為是個兒子。也許她骨子里,希望有一個兒子,可是她不敢生,兒子需要花更多的錢,她哪里敢?
在她臆想中的那個家,兒子可愛又調皮,在練習鋼琴的時候,他才會安靜下來,會很專注,她自己年輕時,也非常熱愛音樂,在錄音機一遍遍播出的世界名曲中,有過浪漫夢想。
想象中,彈鋼琴男孩子的父母,年輕夫婦,一個是教師,另一個,是公務員,都干凈,體面。看房時,按過門鈴,房門被彬彬有禮地打開,穿著連衣裙的女主人笑意盈盈請他們進去,男主人沏好茶,邀請他們坐下。
不急,男主人笑著說,喝完茶以后再看房。
于是,他們邊喝茶邊聊房子的事情,他們說,房子很好,剛買下兩年,因為工作調動,因為孩子上小學買了新學區房,因為他們養了一只狗,要去別墅區住,那里有院子,總之賣房的理由都是諸如此類。她希望是這樣。
她舒服地坐下來,接受一杯又一杯熱氣騰騰的綠茶。直到黃昏來臨,霞光照在陽臺一叢叢綠意盎然的綠植上后,他們才站起來,由女主人領著看房,男主人在客廳,他指點孩子彈琴,琴聲在房間里多么好聽,多么溫馨,他們在琴聲中走進主臥,里面有一張大床,兩米的那種,有一個沒有任何裝飾的大衣柜,純木質,柜門上沒有任何可笑圖案,接著是窗臺,巨大,雖然不是落地窗,可上面鋪上格紋的粗布,放著古樸的軟墊,還有個可愛的小桌子,放著零食,切好的水果放在綠色的玻璃盞中。窗戶被擦得一塵不染,別致的一些小飾件在房間錯落有致地擺放著。她依依不舍地出來,到了另一個房間,這是客房,同樣素凈,簡單。接著是書房,書柜足有兩米,是裝好不能動的,發現這一點她十分高興,這是她的私心,搬來可以直接用上。她喜歡看書,她需要這樣一個房間。大書柜有專用的梯子,可以隨便拿書來讀,在書房大書桌上,桌面顯示出高檔的紅色,椅子不是轉椅,是個放在木地板上的靠椅,舒適,結實,好看。
接著是廚房。不是那種華而不實的開放式。這廚房是獨立的,它被玻璃推拉門隔離開,里面有锃亮閃著金屬光芒的炊具,刀具,鍋碗瓢盆都各自有最恰當的位置,她走近灶臺,打開天然氣,藍色火焰無聲無息。除了鋼琴聲,什么都是安靜的,抽油煙機帶走一些聲音,做飯時聲音是和諧的,是安靜的,只要不是噪音,她就可以將其歸為安靜,屬于靈魂的安靜。
女主人帶他們去參觀衛生間,黑白兩種小墻磚和地磚和諧,潔凈。熱水器常年開著,熱水隨時可以出來,一個大大的木桶在衛生間里等待注入熱水,等待身體的休憩。木桶旁邊的盒子里,放著玫瑰干花,牛奶,薰衣草味道的沐浴液。她此刻就想赤著腳,進入其中,讓水汽縈繞在自己的周圍,閉上眼睛享受這美妙的一切。
噢,她的眼睛,簡直要被這想象中的熱氣迷惑。然而,事實是怎樣呢?她從來沒有遇到過一間這樣的房子,一次也沒有。幻想多么傻啊!
有一次,打開門的是一位老太太,隨著門開放的,是撲鼻的老人氣,那味道酸腐,艱澀,使得她倒退了幾步。他早就皺起眉頭。他們走進去,里面光線灰暗,也是個上午,外面陽光好得讓人重新滋生妄想,可一進入屋內,暮氣沉沉,客廳是暗的,臥室是暗的,連對面人的臉色,也是暗淡的。中介沒有來,但他告訴過他們這里住著一對老年夫妻,他們身體不行了,要去兒子家里住。老頭癱瘓好幾年,老太太一直照顧著,現在,老太太查出來癌癥,是胃癌。所以兩個人要一起去兒子家,接受兒子的照顧。不管愿意不愿意,她想,不管兒子愿不愿意,不管老頭老太太愿意不愿意,都必須這樣。他們都必須去投奔兒子,把自己像兩個包袱一樣帶去給兒子處置。
盡管有思想準備,可是房子境況還是令她感到驚心,感到詫異,感到痛苦和窒息。廚房內,馬桶內,客廳內,都骯臟不堪,兩間臥室,同樣彌漫著將死之氣。老頭躺在其中一間臥室里,隔一會兒,就需要老太太去拿痰盂過去,吐一口濃稠的痰。老頭癱瘓的是下半身,她忽然想,如果癱瘓的是上半身,是不是就沒有吐痰的要求了。然而她又想起下半身癱瘓會有屎尿和暗瘡,她不禁反胃起來。她還是忍,強忍住。
照顧病人是痛苦的事情,她知道這個。他父親死于突發心臟病,而母親是腦梗,發作兩次后,就基本生活不能自理。在醫院住了半年后,去世。這期間他經常就在醫院泡著,是女兒考大學的那一年。她也很疲累。照顧女兒已經讓她疲憊不堪,她下班后做飯,他帶飯去醫院,她陪女兒吃過飯后洗碗,做家務,兼職的公司還有一大堆活要做,活是計件,不做,一分錢都沒有。她做兼職,他從來沒反對過,就是在他母親住院期間,他也沒反對過。不因她忙得很少去醫院而和他賭氣。她的錢,每一分都貼補到家里,她很少買衣服,很少給自己買愛吃的零食,醫院需要錢,她給,女兒需要買營養品買復習資料買水果買肉,也是她出。他的那點工資,每月還公積金貸款,交電費水費,所剩無幾,每一分錢,都來得太艱難,太累,誰也懶得抱怨誰。尤其是她,看到他因為總去醫院,全勤獎加班費被扣除,她也不能說什么。只有這樣撐著。
親人去世后他老得很快,仿佛補缺,他變成老人,老態龍鐘,走路蹣跚,每天上六樓,成為他特別辛苦的勞動,買面,買米,那更是可怕,他喘息著,和一個肚子巨大的蛤蟆一樣噴吐著濁氣。可是他也堅持著。如果是送上門那種,要加錢,他還是自己背回家劃算。
看完房,告別老太太出來,她開始害怕老,害怕死,害怕不能健康老死,害怕不得好死。她聽自己母親說,好死的人,都是修下的,比如那些猝死的,被車一頭撞死的,得心臟病一下死了的,高處有個花盆忽然掉下來砸死的,這都是好死。惡死的人,都是作下的,必須狠狠遭一番罪受一通折磨后,閻王才收。她想到剛才在遭罪的老頭,遭罪的老太太,暗暗為他們感到憂心。
她不知道自己最后會怎么死。她希望是說死就死,不遭罪的死。不連累別人,自己也不痛苦。
現在,他們已經走進走廊,電梯顯示在十二樓,需要等一會才來。他說十二樓是頂層。
我們不要頂層了,頂樓太熱,他說。
他對她笑了笑,幾乎讓她以為是錯覺。他通常都在皺眉,一籌莫展的樣子,他很少微笑,她都快忘記他多久沒對她笑過。他父母去世后,他狠狠消沉了一段時間,直到女兒考上大學的通知書到來時,他都沒有緩過來,他對生活有氣無力,他對未來得過且過,只有在看《動物世界》時,她才覺出他年輕過。
電梯里面空無一人,專為他們而來。里面傳來一股生肉的騷味,像牛肉或者驢肉。這令她不快。她的記憶中,曾經非常非常厭惡這種味道。她想起來,那是令她恥辱的記憶。
他常對著父母照片發呆,她把照片收起來,放到柜子里去,每年過年初一的時候,才拿出來,擺在一個桌子上,放上四樣水果,四碗菜,放好筷子,點上香,和他一起磕頭,然后在初二這天下午,燒紙,把紙的灰燼收起來,由他拿到某個十字街口倒掉。他沉悶,少言。女兒大學住校后,家里更加死寂無聲。他開始經常去喝酒,他沒什么朋友,交朋友是需要花錢的,他沒有閑錢。他到夜市上,一個人叫上幾大杯扎啤,叫上二十或者三十串羊肉串,有時候還要吃一碗饸烙面,然后才半醉著回家。于是每天,他都帶回來一股孜然、燒烤香料、辣椒面的味道,還有肉串散發的一股騷味,聽說假羊肉在羊尿里泡過,也許是真的。她躲在自己房間不出來,她起初睡不著,后來能睡著了,被驚醒之后,她再睡。她疲憊。依然是吵架都懶得吵。
他開始整夜不回家后,她才隱約覺出不對勁。有一天晚上,她并不是十分有目的和刻意地走出門,去找他是一閃念的想法,那時已經十二點多了,她去他說過的老地方去,見到角落里,他落寞地對著幾個空啤酒瓶子發呆。穿肉的鐵釬零散在桌子上扔著。她在不遠處的一棵樹背后看著他,站了很久,連腿都快僵了。終于,看到他站起來,她以為他往家走,可是他沒有。他走到那賣羊肉串的女人身邊,幫她收起了攤子,他做得很熟練,顯然這么干很久了。他邊做邊跟那個女人聊天,大部分是他在說,聽不清說什么,只看到他嘴巴在歡快地動。他不誤手中的活,肉在一個箱子里,鐵釬在另一個箱子里,其他的饃片,蘑菇、雞排,魷魚什么的,都穿好了,在第三個箱子里。木炭發出幽暗微火,還沒有徹底熄滅。爐子被他一把就扛了起來,在車上安置好。最后,所有東西都放到黃色三輪車上。女人騎著,他坐到后面,坐在某一個箱子上,從她視線里漸漸遠去和消失。這時已經很晚,沒有幾個食客,沒有人注意他們。除了她,沒人注意這一切。麻辣燙老板也正準備收攤,見怪不怪的樣子。她走過去,要了一份麻辣燙,老板說,這些攤子,數羊肉串老板有錢,都買了三套房了。她一個字都不多問,覺得沒有尊嚴,怕引起老板懷疑,怕走到路上,麻辣燙老板認出她,笑話她,輕視她,把她當做談資講給某些來歷不明的食客聽。她怕這個。
他一夜未歸。
第二天白天,他中午回來吃飯。用后腦勺對著她,把一碗燜面吃完。電視里播放著一場動物廝殺。老虎吃掉了斑馬,他嘿嘿笑一聲。血腥場面沒有使他不快。廣告時間他去廚房盛飯,他又吃掉滿滿一碗。她第一碗飯還沒有吃完,想著跟他說點什么。后來,她放下筷子,走到電視機那里,把電視機關掉,他瞪起眼睛,準備要和他理論,他理直氣壯問為什么要關掉電視,憤怒起身打算重新打開電視,以此來捍衛尊嚴,他的動作很大,差點把茶幾上他沒來得及送的空碗打翻,碗在茶幾上打了個轉,一只筷子掉在地上,碗又牢牢定格在茶幾上。
她眼睛轉向他面前的空碗,不再看他,她說:以后,不要再去燒烤攤了。
又說:家里也有很多活要做。
他愣住,不敢說話,她去餐桌上吃飯。他沒有開電視,走到廚房,默默去洗碗。
電梯在十樓停住,他們一前一后從電梯里出來,他手里拿著一把房主給的鑰匙。他打開門,她吃了一驚。這是新房,是毛坯房。
90平米,他得意地告訴她,手上揚著鑰匙圈。房子的確大,每一間都陽光充足,她可以按照她想象的任何風格來裝修。她很意外,向他投去征詢的目光。
他得意又有點討好地對她說:房子是他表親多年前的頂賬房,人家有房,不住,原價給他們,不用多花一分錢。
她從來不知道他有個表親,多年來從來沒有一個屬于城市的親戚露面。這個表親是誰?
她提出疑問。但他沒有回答。
對這個房子她很滿意。看過那么多二手房,三手房,她已經失去信心。她還有多少年可活呢,她想有個便宜房子來住。她不是沒想過買個新房,自己來裝修,可是房價居高不下,她怎么敢想?現在,這么好一個機會擺在她面前,她有點不敢相信,可她也想趕緊抓住。
他始終沒有回答對他表親的疑問,而是明確房子價錢。他說出的數字令她心中暗喜,按照這個價格,她賣掉以前六樓120平米的房子,除了把給女兒的那部分留下,還可以付這個新房的房款,如果計劃得當,還能勉強夠裝修這個房子的費用。這真是意外驚喜。她不敢想,不相信。生活中,早就沒有什么大喜事可言,這叫人怎么相信?
空蕩蕩的房子又彌漫起那股騷味,牛肉、驢肉、羊肉混合的,像尿液一樣的味道。這味道越來越強烈,她忍不住想嘔吐,在他貌似關切地靠近她時,她把他往遠處推了推。她拿出一張紙巾捂住嘴,把惡心猛烈地咽下去。什么不可以忍受呢?她抬頭,仔細打量著這個很適合自己的房子。
他們很快賣掉房子。他去銀行,給一個賬號付了全款。接下來裝修,她包攬下來。裝修是件麻煩的事。第一件是砸墻,工程交工時,都是敷衍,用最差的材料。墻皮必須砸掉重新灰一遍。她去市場找工人。沒想到工人這么緊俏,好容易找到一個,對方說半個月后才能開工,等到半個月后,工人帶了一個徒弟來,拿著錘子一通亂錘,墻皮轟然片片落地,里面露出一個個大石頭,透出可怖的縫隙,從這邊能看到那邊。到電視墻那里,墻體變得牢固,這是最牢固的一塊,工人說,要是全屋都像這里一樣,就不必砸墻。可是只有這里牢固,不砸掉,也不行。單剩這里的話,重新灰墻時怕留下不平整的痕跡。于是用電鉆和錘子再突擊,用了兩天時間,才把墻皮砸完,她灰頭土臉回家,在房子里站得腿都僵了,他熬了米湯,拌了黃瓜,她知足地吃了半個饅頭,一倒頭就睡著了。
接下來,墻體整體灰了一遍,找的另外一個工人,加上之前砸墻,她已經花了一萬塊。每一分錢她都花得心驚肉跳,沒想到會這么貴。同事梅姐跟她很要好,剛裝修完房,把給自己裝修過的工頭介紹給她,說活干得好,價錢也不胡要。這樣,她就省卻了找散工的麻煩,很快,房間里的電走好了。工頭姓周,大家都叫他周老板,是一個四十多歲的瘦子,話不多,看上去很靠譜。她把自己的設計方案告訴周老板,又把自己的經濟狀況說了一下。為了讓周老板能夠盡心,她還叫梅姐和周老板一起吃了個飯。基本都是她在說,她叫上自己的老公,可是他說,裝修的事,都交給她,一來家里錢大都是她賺,都是她掌,二來這樣不起沖突,不吵架。周老板和梅姐相視一笑,她的臉熱辣辣的,她覺得人家看不起她,也看不起她老公。她硬著頭皮,把那頓飯堅持下去。
每天他都會做好飯等她。她從工地上回來,吃完飯,盡量把兼職的活再趕一些,就倒頭睡。第二天,再早早去工地。房子漸漸按照設想完成著。按照花最少錢出最好效果的初衷,勉強成形。壁紙是特價,木地板是特價,家具家電是特價,她在每一家店里都據理力爭很久,并且要多要一個鍋,一個體重計,一套餐具等,才肯付款。她的嘴巴上每天都起著皮,眼睛里布滿紅血絲,頭發好幾天不洗,她瘦下來,同時更老,像一個六十歲的老太太。
快要裝修完時,出了一件事。那天,她正在指揮工人裝一臺空調。舊房子里沒有空調,她想在新房安裝一個,立式的,格力的。好空調,格力造,這廣告詞蠱惑了她。她要奢侈一下,還有個私心,女兒女婿在上海住慣了,每天在單位吹空調,如果他們回來住,沒有空調哪能行,如果他們有了孩子,把孩子熱著,又怎么得了。
就在這時,門外進來一個人,門沒鎖,那人徑直進來,問誰是主人,她點頭后,那人又問,多少錢買的房?
她以為是個鄰居,或者,是個同樣看房的人。那人瘦,臉色疲憊。身上穿著一件污濁的半袖,并且,散發著一種調料的味道,是一股類似孜然的味道。
這味道竟然讓她立刻警覺起來。她含含糊糊地說了句,很貴。
那人不罷休,說,很貴,是多少。他的語氣有點不禮貌,有點沖。她往后退了一步。
空調工人完成最后的安裝,打開電閘,試驗成果,涼意直吹到毛孔里去,她認識到自己需要冷靜。
房子是我老婆賣出去的,我并不知道。所以我來問問,是不是你在她手里買的。
她忽然明白了他是誰。空調師傅告辭要走,她沉著地付余款給他們。那人仍然站在門口等,等她回答。
送工人到門口,她腦子里飛快轉著各種念頭,想著該怎么回答。她知道不能說那個價格。她早就知道那個價格意味著什么。這個時候,她選擇和她老公,和她老公的情人,達成默契,達成共謀,達成共識。
她反問他,你老婆沒跟你說多少錢嗎?
他回答,說了。
他又說,不過,我還想來問問,你的分期要多久。
她立刻明白了一些,他老婆跟他說的數目,絕對要高。一定跟市價一樣。她繼續保持冷靜,想著怎樣說才能滴水不漏。她迅速整理語言,她要成功入駐這套房子,成功打發走這個可憐的,滿腹狐疑的男人。
她說,這樣吧,我讓你看看轉賬記錄。
她這么說完,立刻佩服起自己的智慧。她當著男人的面給自己老公撥通電話,對他說,房主找來,請他把轉賬記錄給她發來,她讓他看看。
他會明白。他知道怎么處理。他和他的情人,肯定有著某種約定。
他讓她把電話給那個男人,他在電話里告訴那個男人,轉賬記錄原本在,不過在家,如果需要,他可以下班后回家拍照片給他。
他又告訴那男人房子買的時候付了多少錢,是市場價。男人聽后,剛才繃緊的身體完全舒展,疑云消除,男人客氣地在電話里說,不用不用,我就是問問你們分期的事,你們剛裝修,一次付清是有些難,原本我是反對分期的,不過我老婆已經跟你們說好了,我就沒意見了。
他掛斷電話,跟她客氣幾句,走了。
她靠在門口,空調把她吹得睜不開眼睛。這個夏天,不斷冒出絲絲冷氣。
他倆誰都沒再提起這件事。
最后的工作完成后,她叫上他,把新房里全部打掃了一遍,把自己買來的十五元兩盆的幾盆小吊蘭擺在客廳和臥室,打開窗戶往外看,風徐徐地吹進來,簡直和她小時候在山里吹過的風一樣充滿青草香味。他從背后走過來,抱住她的腰,和泰坦尼克號里面那個經典動作一樣,接著,他把她的身體扭轉過來,拉著她跳起慢悠悠舞步。她身體很軟,熱淚滾滾落下,周身再沒有什么力氣。力氣順著窗戶跑出去,身體變得空蕩蕩,一所房子對她的身體和心靈的損耗比她想象的要多。她微笑著停下舞步,示意自己要坐到沙發上去,他有點調皮地做了個請的動作。
她坐下,無力地閉上眼睛。太累了。這個時候她需要一點依靠。可他還在獨自一個人跳舞,嘴巴里哼著過時的舞曲。她想,隨便誰都行,她只想找個人,靠一靠,如果可以的話,再睡上那么一小會。
這時,她的手機響了。包在沙發上放著,就在手邊。她睜開眼睛去拿手機,是女兒打來的。女兒問她,房子怎么樣了。
她掩飾不住欣喜,說,今天全部竣工。
女兒很少打電話回來。裝修期間,她也沒有回來過,她想給女兒說一下自己的興奮,讓女兒回來看一眼她精心裝修的房子。
可是女兒打斷了她。女兒的聲音很委屈,說,媽媽,你們都換房子了,我們都還沒有自己的房子住。
女兒說,她現在又懷孕了,這個孩子不敢再打掉,醫生說高齡產婦,再流產怕懷不上。
女兒說,他們看好了一套特價房,不過還差些錢。限定半個月之內交錢。如果不交,就交給其他人了。
“為什么是特價房呢?”她愣愣問了句。她想自己裝修都是用特價的東西,特價的東西,并不十分好。
特價也好。女兒說,特價是因為這是二手房,里面死過人的,當地人忌諱,可外地人,哪有資格忌諱?很多人都想買。他們搶先交了定金。
哦。她明白了。他也走過來,湊在她面前聽電話。
媽,我公婆家給了一些,我們又貸了款,不過還缺錢,你和我爸千萬給我們湊來,要不,房子讓別人搶走,定金也拿不回來。
差多少?她問道。
女兒報出數字。她驚呆了,而他已經撲通一聲跌坐在沙發上。她看一眼自己的新房,覺得這房子如此不真實,仿佛不是她的,可明明是她精心裝修過的。床,她還沒有睡過。淋浴,她還沒有用過。廚房里,她還沒有做過一頓可口的飯。仿佛再沒有機會。窗外風開始熱起來。已是中午時分,窗外是煙囪似的高樓,哪里有青草?她是糊涂了,高興糊涂了。
她的眼角還有淚痕,那是剛才包含興奮滋味的淚水。現在,這淚水滑落下來,在她臉上的溝壑里停留一下,就掉到地上。
賣房。她喃喃道。舊房子里的家具現在在租來的一個地下室放著,賣掉房,他們別無選擇,得和那些家具一起在地下室容身。她擦擦眼淚,挺起身體,已經做好一切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