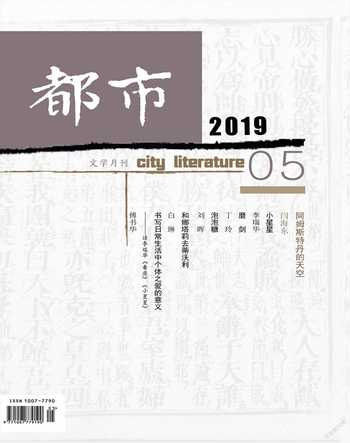和娜塔莉去蒂沃利
白琳
三月有水逆,大家都說要打起精神。
來羅馬的第一周,就生了病。從閑散的假期到緊迫的課程中,整個人仿佛再一次陷入絕境。
但是意大利的三月實在太漂亮了。娜塔說,一起去旅行怎么樣。
我第一次和娜塔單獨出去。
娜塔叫娜塔莉。如果昵稱的話是叫娜塔莎。我為了方便,每次都自作主張叫她娜塔。她說沒關系,因為她的一個小侄女也總是這樣叫她。可是娜塔是數老鼠的娜塔。有一天她在地鐵上問我,Lin,我究竟是個老鼠還是豬。我說ok,按照中國人的算法,其實你是豬。從去年開始,我一直和瑪麗娜待在一起,有時候瑪麗娜會叫娜塔,大部分時候不會。她們身上,都流著一半的俄羅斯血液。瑪麗娜講五國語言。娜塔說三種。現在加上意大利文,是四種。和我在一起,大家都說英文。她們兩個也很少講俄語。
但是瑪麗娜對羅馬周邊實在是太熟悉了,旅行對她而言并不公平。我常常會忘掉她現在是一個意大利人。但是需要出羅馬旅行的時候,我就不約她出門了。其實即便羅馬的天氣再好,我一個人也懶得出門,但是所有的人都在春天蠢蠢欲動,行程忽然就滿得排不開。接到娜塔的電話時,我還在上一段旅程里。
Lin,周末和我出去好不好?她說。
她還說,如果你覺得不方便,可以叫中國的朋友一起。
我說沒什么不方便,兩個人也許正合適。
三月第一周的周末,我們一起去蒂沃利。出行前一晚才想起來,這一周是意大利的第一個博物館免費開放周。今年意大利文化遺產部推出一項新規定,根據這個規定,意大利各大博物館的免費開放日天數會增加至20天。每個月的第一個周日,從十月到第二年的三月,共六天,免費;每年有一個博物館周,周二至周日,共六天;八天的免費開放日。這個隨機,有可能是分開的,可以由各博物館自行決定。新規定2月28號生效。2019年的免費博物館周時間確定,是3月5日至10日。
在意大利,藝術和考古的學生進入古遺跡以及各種博物館都是免費的,所以這樣的規定是針對大眾的優惠。也就是說,無論去哪里,我們都可以橫行無忌,但是恰好出行日選擇了一個大眾優惠日,又是周六,所以我想象了一下人群爆滿的場景———這是中國思維。
大概是之前總也一起出去過幾次,這次兩人旅行一開始倒也不感到尷尬。羅馬周邊的小鎮蒂沃利是意大利拉齊奧的一個古鎮,離羅馬30公里。出產葡萄、石灰華,鎮上的工業以造紙業為主。蒂沃利的哈德良別墅在1999年被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我們上課講它。因為石灰華,還有哈德良別墅。
所以娜塔說,Lin,不要想著這是去玩,我們不是才剛剛學了這方面的內容嗎,我們這就是戶外考察去。
戶外考察課還沒有上夠么?我說。上個學期每次十公里,這學期變本加厲到十四公里。
娜塔說,親愛的,拿出點中國人的架勢。
所謂中國人的架勢,就是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所以我把課堂內容和第二天的游玩內容結合起來做作業,一直做到半夜。有時候我覺得真是一個悖論。我在這邊念了考古專業,可以很明白地知道我看了什么東西,而不是被導游哄來騙去,但是卻好像從來沒有享受過樂趣。每次當我做完功課之后,我對那個地方就失去了敬仰之心。它們從來沒有變的更偉大,而是逐漸趨于平庸。就好比我剛到羅馬,看到米開朗基羅或者拉斐爾的作品,還會覺得哇,真的是精彩壯觀!可是羅馬遍地都是這樣的杰作,所以,現在我們從拉斐爾和米開朗基羅的作品中走過去,都變得心不在焉。就像是公元一世紀的磚踩在腳下,踩成了習慣。羅馬遍地廢墟,人間煙火幾千年浸染,城都被燒毀好幾次,它卻好像集精致與不羈與一身,是個邋里邋遢的somebody。
好在和娜塔很合拍,這是意外。我們一起坐小火車去,沿途是田園風光。娜塔說想要一棟小屋子,住在郊區,我說我在國內也常常這么想,只不過沒這么大一片綠油油風光好的地。城邊上這樣的地都是奢侈品。火車開的慢,三十公里開了差不多一個小時,正好夠吃完點心,喝完咖啡。
蒂沃利有埃斯特莊園,中文譯得俗,但也形象,叫百泉宮,里面盡是大大小小的噴泉。是個十六世紀的別墅,紅衣主教某某某把自己的一輩子都獻給了這個別墅。說是某某某,不是因為記不住名字,而是覺得在這個說明中,如果細節很多,就也成了不好看的有點古怪的文章。就好像我每次去上課,見著好看的壯觀的,也不能由衷的放心的去喜歡。從來,正色和正經,都讓我覺得無味,而且我討厭按部就班的游記,說不上是畫地圖還是搬導游詞,總之有一種大眾生產的塑料味道。
主教某某某那輩子想當教皇沒當上,為別墅的不斷修飾花費了畢生精血,最有樂趣的是叫朋友來做客,就像很多人搞了個農家小院,也喜歡請朋友來坐坐。因為花費不菲,所以陪得傾家蕩產。別墅華麗,但總叫我有一種憂傷感。我指著最大的噴泉,對娜塔說,那后面有洞。娜塔過去,果然有。她說哇,后面能過人。我說我們中國有一個猴子,就住在類似的洞里面。然后就是一陣胡吹,就像所有在羅馬的無良黑導游一樣,講出各種不負責任的語言。我受夠了課堂上凡事必點出處的教條規矩,開始信口開河。
我們去蒂沃利,主要是看villa Adriana,這是羅馬帝國皇帝的別墅中最為廣闊和富麗的一座。課堂上講villa的時候好好講過。頭一天晚上做功課做到想要吐血,偏偏沒有查路線怎么走。娜塔說,我們不搭車,我們走過去,地圖上一看,沒有幾公里,走路一小時。娜塔和我都覺得是個小意思,當然是小意思,哪次上課我們不得走個七小時?然后我們就很不科學地跟著谷歌走。
我得說我們教授說谷歌是個“stupid”的玩意兒真的沒有對不起它。這絕對是一個不值得推薦的行為方式,乖乖買公交票過去就好了,只要十分鐘,一張票一塊三。
我和娜塔沿著路走,很快就走到了荒郊野外。走了二十分鐘之后,路上已經沒有人行道了,只有兩條山道,都通車。一條靠著溝,看得見小鎮全景,一條靠著山,雜草叢生。我們不敢沿溝走,因為視覺死角更多,只能貼山而行。一路逆行。覺得身邊呼嘯而過的每一輛車都會罵我們一句SB。
你害怕嗎?Lin?娜塔一邊走一邊回頭問我。
不怕。我朝她吼。
我覺得我的喉嚨在冒煙,尾音打著彎不知道拐到哪里去。我穿了短袖還是熱。胳膊被路邊枝條劃了好多口子。
你呢?我又吼了一聲。
一切都ok,感謝上帝,我還沒被撞死,好好地活著哪!
她的回答被呼嘯而過的汽車蓋住了百分之八十的分貝。
說實話我幾乎聽不見你說什么。我再次大吼。
我說,我們都是超級大傻瓜。你,谷歌,還有我。娜塔氣極反笑紅色的頭發在陽光之下燃燒。
你說,我們如果從這里再走回去,是不是更蠢。
好容易遇到一個比較大的拐彎,我們終于可以并肩站在一起休息一下。娜塔掏出來水瓶,灌了好大一口。我一邊查地圖一邊問。地圖上顯示我們已經走了一半了。這時候再走回去搭車,是在是蠢得夠嗆的行為。往前往后,都是驚險。有時候我們堅持一條道走到黑,倒也不是太過古板,實在是沒有什么可選擇的余地。
半小時后,從快速車道上的盡頭終于有了一條分支,我們拐了上去,之后我們走過了一片葡萄園,然后又走過了一片果園,然后是一個莊園。我們還經過了一條滿是塵土的小路。剛走上去的時候我們幸福極了,腳底是松軟的草葉和塵土,四周還有花香。娜塔和我一樣,都不是香水的嗜好者,所以那一刻自然的味道充斥了我們的鼻腔。但是還沒有等我們享受夠,遠處就開來了一輛車。塵土像是鼓風機前面的面粉一樣飛了起來,一直飛到路的盡頭,我們被嗆得趕快掩住口鼻,世界忽然從綠色變成了灰白色。是一種淡淡的霧霧的磨砂的白。
等塵土落下去一點之后,娜塔才沖著車尾吼:你毀了我們的路!
是的,他毀了我們的路。這條路還挺長的。我們慢慢走著,等所有被揚起的塵土重新落定。就在它們紛紛下落的途中,也許正落到我們的腳踝位置的途中,又有一輛車開過來了。
我去,這么偏的路,竟然能在十分鐘內過兩輛車!娜塔和我一起拿外套掩住口鼻。我們現在都有了經驗。
但是車沒有開很快,而是在靠近我們的時候慢慢停了下來。一個女生搖下車窗,問我們:要去哈德良別墅嗎?
是。
那上車吧。我也去。
不了,謝謝,我們想要享受一下三月,還有“我們”的路。
Ok。Enjoy。
她開走了,開得很慢。土這一次只揚到我們的膝蓋。
你喜歡這樣的旅行嗎?
什么?
就是走啊走。比起坐車,我更喜歡徒步。
我也是。
但是我們回火車站的時候還是老老實實買了公交車的票。不是因為不能夠再堅持走路了,而是因為害怕被車撞死。走路一個半小時的距離,公交車只要十分鐘就開到了目的地,我們都有點索然無味。
這么快,真沒有意思。雖然來的時候有點蠢,但是還好我們走了一趟,享受了那么多的美景。
———還差點被撞死。
Whatever。反正我們現在還活著。
去吃冰淇淋吧。我們還有時間。我們回來太早了
我們在小鎮了走了一陣子。早上的時候看到一個小集市,賣花賣蔬菜水果,這時候已經什么都沒有了,只有一些咖啡廳的帳篷搭在外面。Tivoli小鎮本身就很古老精美,上坡地方還有個較大的古堡,小巷里轉出來轉進去,就是在和陽光捉迷藏,臨近傍晚,光線仍然美的讓人心醉。我很少用心醉這樣的詞。可是我愿意把它用在意大利的每一個美景中。我常常感受到一種心醉。常常恐懼,自己陷在一個美夢里,不敢翻身,深怕醒來。
我們在一家冰淇淋店里坐下來。一人拿著一只冰淇淋。
Lin,我來意大利的原因是因為陽光。還有聲音。幾年前,我第一次來的時候,住在羅馬的隨便一個什么地方,早晨醒來的時候,所有的陽光都灑在我的身上。我聽到了鳥叫,還有人們的聲音。奇怪的是,我一點都不覺得吵,感到很安心。
那是因為你不會意大利語,你不知道他們在講什么所以也就不關心內容,只享受了他們的熱情的聲音。
不管怎么說,意大利給我一種熱烈的活著的感受,我愛極了這里的天氣。
那是因為你在挪威待了太久的時間。不抑郁才怪呢。
我身邊坐了個男人,面前放著一個杯狀的冰激凌,提拉米蘇和開心果的混合。他身邊的椅子上擺著一只手提箱。我從來沒見過那么不尋常的手提箱。豬皮漂白后做的,新的時候該是淺奶油色,配件是黃金的。就算這邊買得到,看上去也不便宜。
冰淇淋快要化掉了,他碰都沒碰過,跟我一點也不一樣,我忙著吃我手上的那一大桶。吃的又累又滿足。他正在抽煙,但看起來也并不怎么想抽。
我喜歡他那個皮箱。我對娜塔說。
她眉毛抬了抬,看上去并不贊同我的說法。
我在心中勾勒那種有十八個房間的石頭屋子。她說。如果有一天我有那樣的屋子,也會叫朋友一起住。不然太凄涼。
但是朋友不會一直來。而且你還沒有噴泉和泳池。你至少得弄個噴泉讓我們一邊吃飯一邊享受水流的聲音。
我們都在說D’este別墅的故事。那里面各種各樣的噴泉,功能還有所劃分,其中一種就是制造水流的聲音,讓朋友聽。十六世紀的別墅,當然放在這時候,在娜塔的想象里大概就變成了另外一種模樣。恐怕是還充斥我們上個學期學習到的很多藝術作品的新裝潢,用無線電話吩咐管家把香檳冰一冰,松雞烤一烤的樣子。
他看上去有點心事啊。我又有一點八卦了。
人人都是氣球,里面充滿思考的空氣。
我有一天在我家看到一只蟑螂淹死在一只裝了豬油但是沒有蓋蓋子的瓶子里,你說它是開心開始不開心。還是樂極生悲。
也許還蠻開心的吧,畢竟好多人都還挺想被錢砸死的。
我不是。
哈哈哈哈,我也不是。
我們走吧。我有一點冷了。
我們站起來,把椅子推到一邊,是三月蒂沃利的傍晚五點鐘。走之前我看了看那個箱子的主人。他看來變了很多———比較老,比較清醒、嚴肅,而且一片祥和。他像那種學會了閃避拳頭的人,穿著一件牡蠣白的風衣,戴著手套,沒戴帽子,白發像鳥的胸脯一樣平滑。
我們算好了時間,離下一趟回羅馬的車還有大概半個小時。我們在路上花了十五分鐘,到達火車站的時候還有十七分鐘。但是我們沒有買票。沒有人工售票點,一臺自動售票機前面排滿了人。全部都是外國人。看上去好像沒有人會用那個機子。有個男人甚至還想用拳頭砸出來一張票。排了十分鐘之后,娜塔說,好了,我們坐下一趟回去。
幾點?
七點。
Ok。沒有問題。但是也許我們就趕上了這一趟了呢?
看上去不可能。
娜塔說對了。輪到我們的時候已經過了出發時間三分鐘了。我們買完票,出門撞見排在我們前面好幾位的男人。他穿著一條阿迪達斯的運動褲,黑色。白色T恤,一頭汗,沮喪地回來。
哦,你沒趕上車嗎?娜塔問。
然后我們就承受了一堆吐槽和咒罵。
坐在火車站戶外的長椅上候車。我和娜塔都想要喝一杯咖啡。那大概是我們在意大利最愛的味道,過很久都會想起來的味道。關于我們在這里活過的味道。我說我買了比樂蒂咖啡壺,可以每一天享受那樣的味道。早上匆匆在浴室洗漱一番,回來的時候計時器的鈴聲正好響起。關了火,把咖啡壺放在桌面的一塊草墊上。我為什么要說得這么詳細呢?因為回憶會使得每一件小事都像表演,像一個明顯又重要的動作。那是極為敏感的一刻,你所有不自覺的動作無論多么熟悉,多么習慣,都成為意志之下彼此分離的舉止。
我們以后,就這樣常常來旅行吧。
好。我說。這是聚集記憶的時間———Time Walking On Memo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