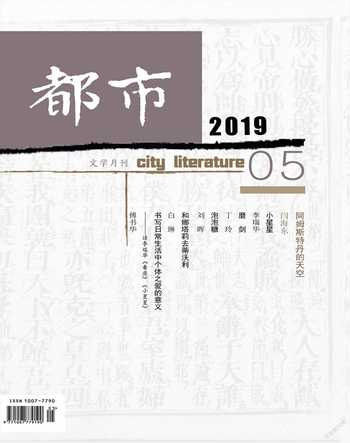她就是山神凹的女兒
許瑋
羅羅山下,山神廟旁,耐受河穿村而過。
四季的悄然輪回里,一個叫“山神凹”的晉東南村莊,突然間就被廣大讀者熟知。這個曾經貧瘠而荒涼的村子,生養了一位叫“葛水平”的作家,是她的書寫,讓這片土地有了文學的色彩。
多年的寫作,一系列文學榮譽的捧得,葛水平始終沒有忘記自己的故鄉———太行山下的山神凹。2011年,她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裸地》(刊于2011年第3期、第4期《中國作家》),遙遠年代里的人和事,被她寫得沉重而揪心,讀者記住了生養她的那個叫“山神凹”的小村。時隔七年,2018年秋天,葛水平又捧出了一部長篇小說《活水》(刊于2018年第9期《人民文學》),同樣是寫山神凹,讓她放不下的依然是對故土的惦念和牽掛。
黃土厚重,河水奔流,從《裸地》到《活水》,葛水平進行了一場深入而持久的文學跋涉。山神凹走出來的作家,讓那片土地呈現了文學的光澤。
山神凹是葛水平的故鄉,無可置疑地是她文學創作的素材庫。身為作家,葛水平希望自己的故鄉變好,希望鄉鄰們能在大時代的變革里富起來,活得堂堂正正、殷殷實實,所以,才會一次次把目光投向太行山下的那片土地,并矢志不渝地用文字書寫。迄今為止,葛水平所有鄉村題材的小說,幾乎都有山神凹的影子。她用文字打開了一扇窗,山外的人看到了山里的景象,山里人也望見了山外的不同。
然而,因為窮,故鄉的人一度產生了鄙薄故鄉的心理。《活水》這部小說,有人感言,“山神凹真他媽的是全中國最不被人關注的地方。”又說,“山神凹是一個鬼地方,不適合人居住。”而且,老一輩山神凹人更是勸自己的兒女,“就算在城里活得不像樣子,山神凹人也會高看你,祖宗也會高看你。”人往高處走,貧窮留不住人吶!縱然愛戀自己的故鄉,可是,看著鄉民們為了生活,一個個背井離鄉,進到城里,土地變得荒蕪,村莊日漸頹敗,葛水平感到了焦急、焦慮,甚至憂心忡忡。
《活水》有名有姓的人物達58個,葛水平并沒有刻意把某個角色拔高成中心人物,而是讓所有的人都成為“中心”,組成了《活水》這部小說的“群體形象”。這些人物,在山神凹一定都能找到原型。他們有的曾與葛水平朝夕相處,有的在她的人生記憶里也許只是流星一閃,但因為是山神凹的鄉民,是葛水平深愛的土地上的生命,故而每一個人物寫起來都沒有陌生感。
一個村莊養育了幾大姓,卻輩輩守著大山,守著干枯的歲月,在山神凹的土地上苦熬,窮了一代又一代,所以,每個人都想著有朝一日能走出山神凹。不管是申廣建、申老七、申斗庫這樣的山神凹“農一代”,還是申白露、申寒露、宋栓好這樣的“農二代”,甚至申芒種、申小滿、申小暑這樣的“農三代”,都希望能走出去,到城里看看五光十色的生活。在山神凹人看來,山外才有“活水”,山外才有希望,山外的月明似乎也比凹里的亮。
小說中的申寒露,因為跟一個叫“李夏花”的留守婦女偷情,被全村人看作是申家的敗類,受到恥笑和排斥。申寒露聽到了村人的議論,甚至接受了大家的恥笑,但他想挺直胸膛往前走,想活出個人樣來。然而,有時候,人還是左右不了自己的命,到頭來,終究走不出人生的困局。日子需要“活水”滋養,愛情需要“活水”滋養,人一生的事業和奔忙又何嘗不需要“活水”呢!
申寒露的前半生在出走與回歸之間糾結不定。當他真的敢為自己的愛情做主,并決定和李夏花走到一起,組成一個新的家庭的時候,生他養他的山神凹才真正有了“家”的意義。
李夏花無疑是小說中女性人物的核心角色。她的一生不斷地糾纏著愛恨情仇,也不停地在離鄉和回鄉之間輾轉。作為女人,她最大的不幸,就是沒有給申家生一個健全的孩子。后來,“她和山神凹漢子茍且,目的很明確,她需要錢,她要錢就是想給大嘎看病。”然而,母愛的偉大還是屈從于生活所迫。李夏花無奈離開了山神凹,到城里的劇團謀生,就為了一口飯,而且,山神凹的風言風語已經容不得她再棲身。人活一輩子,有時候是活給別人看的,一輩子要活出個樣兒來,實在不容易。李夏花就是最好的一個例子。所以,她一生都渴望有個安定的家,有個疼愛自己的丈夫。后來,她與申寒露組成了新的家庭,要開始新的歲月,人生才算有了一個不再漂泊的安放。
故鄉不會拒絕自己的兒女,離開或者歸來,故鄉永遠都是那片熟悉的土地。不管失意還是落魄,在故鄉的土地上都能找到人生的安慰。
申寒露的奮起、李夏花的抗爭,讓人更加明白了一個道理:你怎么對待生活,生活就會怎么對待你。到了山神凹第四代,命運依然如此。走出大山、走進城里的申小滿,潦草輕浮地對待生活,生活最終給了她一個沒有結果的人生。相較于申小滿,同樣進到城里的申小暑,用一顆真誠善良之心對待生活、對待周圍的人,因此,生活給了她豐厚的回報:不但收獲了事業,也收獲了純真而幸福的愛情。
閱讀《活水》,我清晰地讀到了一個詞———掙扎,每個人都在土地上掙扎:有的人掙扎了一輩子,有的人轉瞬即逝。山神凹雖然只是一個小村,但因為每個人的掙扎,村莊猶如一個大舞臺,人人都在這個舞臺上演繹著自己的悲歡離合。每個人掙扎的方式不同,但目的都是希望走出貧困,到城里讓人高看一等。然而,當山神凹人真正進到城里的時候,卻發現城里的生活并非完全適合他們,縱然好日子不會招手即來,得使勁兒,得蹚對路子,但城市的五光十色,很多時候讓他們無所適從。
小說結尾,山神凹的第三代、第四代回來了。他們是在山外打拼過的年輕人,山外的生活拓寬了他們的眼界,有想法,有魄力,敢闖敢干,他們將給山神凹注入“活水”,也該是給生養自己的土地注入“活水”的時候了。窮是窮一時,還能窮一世!而且,任何一片土地,只有注入“活水”,才不會荒蕪,也才會有希望。年輕人的回歸,讓山神凹有了“活水”,凹里的日子要變了,人的心也要變了。葛水平借放羊人韓谷雨的口說,“我告訴你們吧,我有預感,山里人借山居住,賺城里人錢,是莊稼人活著的正理。”這是作為山神凹女兒的葛水平發自內心的期待,正如年輕的主人公申小暑說的那樣,“擁有土地的人才能理解生活的美好。”這就是小說的主旨。
群體掙飯吃的征途上,山神凹的故事代代接力,耐受河見證了這樣的接力。
葛水平善于寫鄉村生活,塵世煙火在她筆下騰起了俗常的美學。比起一些宏大題材的寫作,葛水平執著于民間書寫,善于從民間取材,一支筆娓娓道來,切近生活的原汁原味。所以,葛水平的小說深深地打著民間的烙印。驢、窯洞、二胡、戲班、八音會、一丈紅……這些太行山腹地獨特的生活場景和生活元素,被葛水平在小說中賦予了“文學地理學”的意義。而且,劇團生活經歷,讓她寫起戲來游刃有余,不經意間的一落筆,就把舞臺情景寫得活色生香。當代作家里,少有人能把戲寫得如葛水平那般唯美。從她獨特的語言風格里,讀者能感受到小說字里行間交織和暈染著的濃濃鄉愁。
葛水平發表的文學作品,幾乎都是鄉村體裁。值得注意的是,她的不少鄉村題材小說都與當下有一定距離,寫的是舊時代的故事,可《活水》寫到了當下,觸及到當下的鄉村變革。土地和人的變革,在群體的掙扎中極具現實意義。由葛水平的《活水》,我想到了作家江子先生的散文集《田園將蕪》。全書借描繪贛江邊一個叫“下隴洲”的村莊的地理經緯、歷史記憶、身體疼痛及現實境遇,表達了對五千年鄉土中國的眺望和思考。“當鄉村被逼到坍塌邊緣,中國精神昔日賴以維系的鄉土已瓦解時,我們的家園是否有重建的可能?有著數千年文明歷史的鄉土中國,將會走向何方?”作者的這些發問,切中了當下中國鄉村出現的癥結,而這些發問,也正是葛水平在《活水》中提及并思考的。她的小說對當下鄉村的描摹,相信所有從鄉村走出來的讀者都有同感。
一個作家,文字所能筑起的最高功德,恐怕就是對生養自己的土地施以跪拜之禮。在《活水》創作談中,葛水平寫過一句話,“我堅信,重返故鄉是未來人的必然選擇。”這是她的自信,也是故鄉對每一個游子的深情呼喚。葛水平是山神凹的女兒,提筆書寫自己的故鄉,是她對故土的虔誠回饋。
葛水平曾說,“只有貧窮和荒涼可以帶給我靈動的故事。”但我想,循著她筆下的這道“活水”,山神凹一定會摘掉窮帽。而且,作為山神凹的女兒,葛水平用《活水》這樣一部長篇小說的書寫,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游子還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