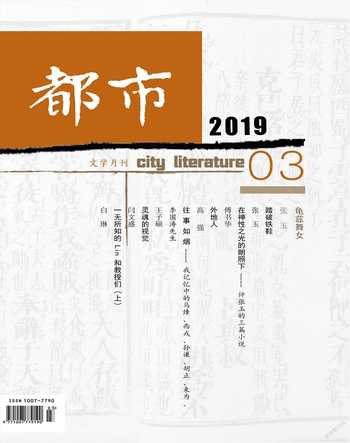舞女之鞋
人之所以有這么多的喜好,歸根結(jié)底是因為理想。我們還是要做點自己擅長的事,不論是為了尋找存在感,還是為了自己對世界的傾訴———我從來不掩飾自己對文學(xué)、對生活、對自己和他人的欲望,我喜歡在文字中顯露出真實的張玉。開始寫作有很多年了,從詩歌到散文到小說,我一直期待這些記錄下我的快樂和痛苦、光明和黑暗的故事被愛我的人珍重閱讀。我會穿越時間和空間向他們微笑:縱使相逢應(yīng)不識?莫愁前路無知己?我堅信確有這樣的人和物在我身旁。
近年以來我寫得最多的是散文,而最近開始學(xué)著寫小說,我感覺這個轉(zhuǎn)型很費力。如何寫小說?直接復(fù)制生活是肯定不行的,而過分的虛構(gòu)也還是不行。小說有比散文更苛刻的選材取向和結(jié)構(gòu)層次。我喜歡“小說”這兩個字,它給人一種家常的、親切的感覺:小小地說一段,說話、說事、說書……說著說著,小說可以動筆了。
這個小輯中選的兩個短篇都是我的新作,它們屬于從散文到小說的過渡作品,散文體敘述痕跡在《龜茲舞女》中尤為明顯。這篇小說的創(chuàng)作靈感來自于一幅壁畫,我在新疆阿克蘇的一個無名廢墟中看到一面墻上有殘存的壁畫,一個面目模糊的女子在殘損的墻壁上作飛天舞,那些當年曾華艷無比的顏料都已經(jīng)斑駁脫落,這女子衣履凋零、肢體殘缺,但她依然起舞不息。由此我想到理想和信仰,這種思考令我有一種對宗教的敬畏。故事的最后,魚兒通過支教完成了自己的救贖,成為一名美麗的舞女,她在月光下為文明的傳承而舞。
然后的《踏破鐵鞋》,其實它延續(xù)了上一篇小說中舞女的理想,但是這種理想雖然更深刻,卻十分迷茫,也許這更切入我們當下的生活,它表達了我對近年以來生存和夢想之沖突的舉棋不定。我把故事的鏡頭拉回來,我讓楊經(jīng)緯走在我熟悉的太原街頭,但是他仍然找不到方向。“踏破鐵鞋無覓處”的下一句是“得來全不費工夫”,但是楊經(jīng)緯真的得到了什么嗎?我認為沒有。因為他并不知道他是誰,他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楊經(jīng)緯做的鞋子之寓意性質(zhì),是對理想的深刻追問,這種追問是永恒的。草原聽不到鞋子的呼喊,一雙鞋的呼喊,無聲地穿透時間,在水泥森林里回響,故鄉(xiāng)消逝,大地龜裂,世界上的一切理想也許就這樣牛頭不對馬嘴,這也許是人類后工業(yè)時代最后的悲傷。
我最近的創(chuàng)作狀態(tài),可以說焦頭爛額。因為我想要表達的東西,比我目前所能表達的東西要多、要復(fù)雜,所以,我在尋找一種更好的敘述,從現(xiàn)實主義內(nèi)部突破出來。當我遇到抽象問題的時候,寫實總是無能為力。比如道德問題,是整個社會的問題;比如信仰問題,是形而上的問題;散文又沒有那么大的容量。所以要表達宏觀問題,我只能選擇小說。過了這個坎之后,出現(xiàn)了一個新的視野:當你和自己創(chuàng)作的虛擬人物生活、呼吸在一起,文檔在手指的敲擊下葳蕤成長,世界上少有事物能與這種快樂相比。
魚兒是不幸的,但是她快樂、堅韌,楊經(jīng)緯的生活平穩(wěn)舒適,但他是痛苦的、迷茫的,而我卻因為寫了這兩個人而得到釋放和滿足。好吧我承認我把自己的快樂建立在了他人的痛苦之上。這就是我的舞女之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