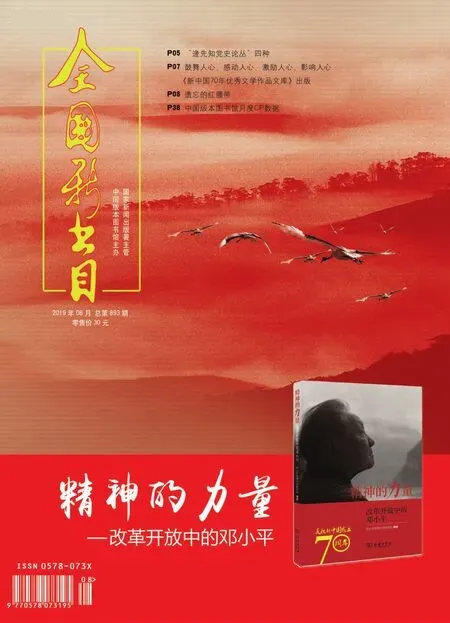遏制戰(zhàn)略是美國政府一直遵循的國家安全戰(zhàn)略
《遏制戰(zhàn)略:冷戰(zhàn)時期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評析(增訂版)》
[美] 約翰·劉易斯·加迪斯 著
時殷弘 譯
商務(wù)印書館
118.00元
2019.06
自喬治·凱南首次締造了遏制戰(zhàn)略以來,該戰(zhàn)略被冷戰(zhàn)期間歷屆美國政府所繼承,但每屆政府都賦予其新的內(nèi)涵和手段,這一嬗變過程在本書中得到了全面透徹且視角獨到的分析。遏制戰(zhàn)略是冷戰(zhàn)中美國歷屆政府一直遵循的國家安全戰(zhàn)略。本書是美國著名冷戰(zhàn)史學(xué)家約翰·劉易斯·加迪斯的代表作之一,全面透徹地分析了遏制戰(zhàn)略的演變歷史,是一部經(jīng)典的國際關(guān)系史和戰(zhàn)略史杰作,并且在大戰(zhàn)略理論方面做出了重要建樹。加迪斯從戰(zhàn)略的目標(biāo)、對威脅的認(rèn)識以及實現(xiàn)戰(zhàn)略的手段三個方面,對整個冷戰(zhàn)期間的不同版本的遏制戰(zhàn)略進(jìn)行了分析,通過歷史研究揭示了每種遏制戰(zhàn)略的實施效果及優(yōu)劣。1982年,本書第一版問世。2005年該書出版增訂版,補(bǔ)充了第一版中缺失的遏制戰(zhàn)略在冷戰(zhàn)末期的重要發(fā)展。約翰·劉易斯·加迪斯在冷戰(zhàn)史研究領(lǐng)域的地位已無須贅述,本書即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無論從國際關(guān)系史研究還是戰(zhàn)略研究層面而言,本書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佳作。

[文摘]
(一)
國際事務(wù)中國家利益的種種定義趨于了無新意且無懈可擊:它們?nèi)伎磥硪赃@一或那一形式,歸結(jié)為對于造就一種對一國國內(nèi)體制的生存和興旺有利的國際環(huán)境的需要。的確,凱南在1948年夏天寫下的定義也不背離這個模式。“我們的對外政策的基本目標(biāo),”他斷言,必須始終是:
1.捍衛(wèi)國家安全,這意味著我國始終有能力在不受外國嚴(yán)重干涉或干涉威脅的情況下追求自身內(nèi)部生活的發(fā)展;以及
2.推進(jìn)我國人民的福利,辦法是促進(jìn)這樣一種世界秩序:在其中,我國能對其他國家的和平和有序的發(fā)展做出最大程度的貢獻(xiàn),并且從它們的經(jīng)驗和能力中獲得最大程度的裨益。
凱南告誠說,“徹底安全和國際環(huán)境的完美永不會實現(xiàn)。”任何這樣的目標(biāo)表述充其量也只能“指示方向而非終點。”不過,這仍是凱南對美國在世界事務(wù)中不可減約的利益所曾作過的最直接的辨識,大概極少有人會對他的說法提出質(zhì)疑。比較困難的任務(wù),在于準(zhǔn)確地具體確定為加強(qiáng)國家安全、增進(jìn)國際環(huán)境的適意性(congeniality)需要什么。
凱南論辯說,美國人傳統(tǒng)上以兩種方式來回答這個問題。一種是他所稱的“普遍主義”(universalism)方式,設(shè)定“如果能促使所有國家都同意某些標(biāo)準(zhǔn)的行為規(guī)則,丑惡的現(xiàn)實——權(quán)勢渴望、民族偏見、非理性的仇恨和嫉妒——就將被迫退縮到一種保護(hù)性屏障之后,即被接受的法律制約。而且我們的對外政策問題就能由此簡化為熟悉的議會程序和多數(shù)決定方式。”普遍主義以國際事務(wù)中和諧的可能性為前提,力圖通過創(chuàng)設(shè)國際聯(lián)盟或聯(lián)合國之類人為的構(gòu)造來實現(xiàn)這一和諧,并且將其成功寄托在各國的一種意愿上,那就是使它們自身的安全需要從屬于國際社會的安全需要。
凱南將另一種稱作“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方式。它“懷疑任何將國際事務(wù)壓縮到法理概念中去的方案。它主張內(nèi)容比形式更重要,內(nèi)容將強(qiáng)行穿透加諸它的任何外表構(gòu)造。它認(rèn)為權(quán)勢渴望仍然在如此眾多的國家中間起主導(dǎo)作用,以致不可能被反制力量以外的任何東西減緩或控制。特殊主義不會拒絕與別國政府合作以維持世界秩序的觀念,但要有效的話,這樣的聯(lián)盟就須“基于只在有限的政府群體之間才會見到的利益和觀念的真正共同體,而非基于普遍國際法或普遍國際組織的抽象的形式主義。”
凱南認(rèn)為,對美國的利益來說,普遍主義是個不適當(dāng)?shù)目蚣埽驗樗俣ā懊總€地方的人們都基本上如同我們自己,他們由實質(zhì)上相同的希望和靈感激勵,他們在既定的環(huán)境中以實質(zhì)上相同的方式做出反應(yīng)。”對他來說國際環(huán)境的最顯著特征是其多樣性,而非其一致性。將國家安全寄托于在全世界范圍內(nèi)擴(kuò)散美國體制將超出美國的能力,從而危及這些體制。“我們是偉大和強(qiáng)大的。但我們沒有偉大和強(qiáng)大到如此地步,以致僅憑我們自己就足以征服、改變或經(jīng)久地使所有……敵對的或不負(fù)責(zé)任的勢力服從。試圖這么做將意味著要求我們自己的人民做出如此的犧牲,其本身就將徹底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和我們的政治體制,而且會在試圖捍衛(wèi)它們的時候失掉我們政策的真正目的。”
普遍主義還涉及使美國立意追求一種在凱南看來既不可能、也不可取的目的,那就是從國際生活中消除武裝沖突。他認(rèn)為,只有靠凍結(jié)現(xiàn)狀才能做到這一點——“在維持現(xiàn)狀符合其利益的時候,人們不會和平地離棄現(xiàn)狀”,而這轉(zhuǎn)過來意味著使國家陷入“如此令人迷惑和受限的義務(wù)承諾,以致我們無法在世界事務(wù)中以有利于世界安全和世界穩(wěn)定的方式運用我們的影響。”事實是,戰(zhàn)爭可以并非總是惡,和平也可以并非總是善:“如果你喜歡的話,監(jiān)獄高墻后面就有‘和平’。在今天的捷克斯洛伐克就有和平。”
雖然可能令人不快,我們或許仍不得不直面這樣的事實:可能在某些場合,世界某些地方的規(guī)模有限的暴力可能比相反的情況更可取,因為這些相反的情況將是我們會被卷入的全球性戰(zhàn)爭,在其中沒有任何人會贏,整個文明都會被拖進(jìn)去。我認(rèn)為,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事實,即對我國的安全來說,會有一種與暴力的單獨復(fù)發(fā)相比不那么可接受的和平安排。
“或許世界和平這整個觀念一向是個不成熟、不可行的堂皇的白日夢”,凱南在1947年6月爭辯道,“我們本應(yīng)提出如下說法作為我們的目標(biāo):‘和平——如果可能,且在它實現(xiàn)我們的利益的限度內(nèi)。’”
最后,普遍主義有可能使美國陷入“毫無結(jié)果和麻煩不堪的國際議會制度的混亂之中”,這種制度可能阻絕捍衛(wèi)國家利益所必需的行動。凱南非常輕視聯(lián)合國。他堅持認(rèn)為,設(shè)想在那里采取的各種立場對世界事務(wù)有大的實際影響乃是幻想。相反,它們猶如“戲劇場面的競演:有一段比較暗淡的、冗長的準(zhǔn)備時間,然后大幕升起,燈火通明一時。為了子孫后代,代表團(tuán)的姿態(tài)被關(guān)于表決的一組照片記錄下來。誰看來處于最優(yōu)美最動人的位置,誰就贏了。”如果出于什么原因,這種“議會表演”能被予以實際的承認(rèn),“這就將確實是解決國際歧異的一種精致、優(yōu)越的方式。”然而,因為這不可能,所以唯一的效果是使美國人民偏離真正的問題,并且使國際組織本身從長期來說變得滑稽可笑。
因此,促進(jìn)國家利益的最好辦法不是試圖重建國際秩序——“普遍主義”的解決辦法,而是通過“特殊主義”方式,即試圖維持國際秩序內(nèi)部的平衡,這樣就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國家集團(tuán)能夠主宰它。“我們的安全依靠,”凱南在1948年12月告訴國家戰(zhàn)爭學(xué)院的聽眾,
我們有能力在世界的敵對或不可依靠的勢力中間確立一種均勢:在任何必要的地方使它們彼此爭斗,確保它們在彼此沖突中消耗——如果它們必須消耗的話——在相反情況下可能指向我們的褊狹、暴力和狂熱,確保它們由此被迫相互抵消,在兩敗俱傷的沖突中耗盡自身,以便促進(jìn)世界穩(wěn)定的建設(shè)性力量可以繼續(xù)享有生活的可能性。
和諧或許是不大可能的(鑒于凱南對人性的悲觀看法,這很難說是個令人驚奇的結(jié)論),然而可以通過仔細(xì)地平衡權(quán)勢、利益和敵意來獲得安全。
(摘自第二章第一節(jié))
(二)
2004年2月16日,喬治·F.凱南慶賀了他的100歲生日。比蘇聯(lián)早13年誕生,現(xiàn)今在它解體后13年,他仍健在。身體衰弱,但依然心智靈敏,這位國務(wù)家在其普林斯頓家中的樓上臥室內(nèi)會見一連串的訪者,包括家人、朋友、他的傳記作者,甚至美國國務(wù)卿科林·鮑威爾。
58年前,差不多也是同一天,凱南在另一間臥室里患病臥床,躲避莫斯科的凜冽寒冬,并且一如既往地對國務(wù)院感到氣憤。他叫來他的秘書多蘿西·海絲曼,口授了一份超長的電報。這項文件比任何其他文件更有理由宣稱鋪平了一條道路,據(jù)此國際體系從它在20世紀(jì)前半葉的自毀軌道轉(zhuǎn)到了另一軌道,那到20世紀(jì)后半葉結(jié)束時,已經(jīng)消除了大國間戰(zhàn)爭的危險。
言過其實?也許是,但在1946年2月22日,有誰會認(rèn)為世界能安然免于大國間戰(zhàn)爭的浩劫? 這怎么可能?彼時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剛結(jié)束——與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過后相反——各國甚至無望召開全面和會。免于威權(quán)主義危險?這怎么可能?彼時西方民主國家不得不依靠一個威權(quán)主義國家去擊敗另一個。無虞再度發(fā)生經(jīng)濟(jì)崩潰?這怎么可能?彼時無法保證全球性衰退不會重演。無虞人權(quán)遭難?這怎么可能?彼時歐洲最發(fā)達(dá)的國家之一剛犯下史無前例的種族滅絕滔天罪行。無虞這樣一種恐懼,即在任何未來戰(zhàn)爭中任何人都不會安全?這怎么可能?彼時原子武器已被開發(fā)出來,而且它們幾乎不可能繼續(xù)僅由美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