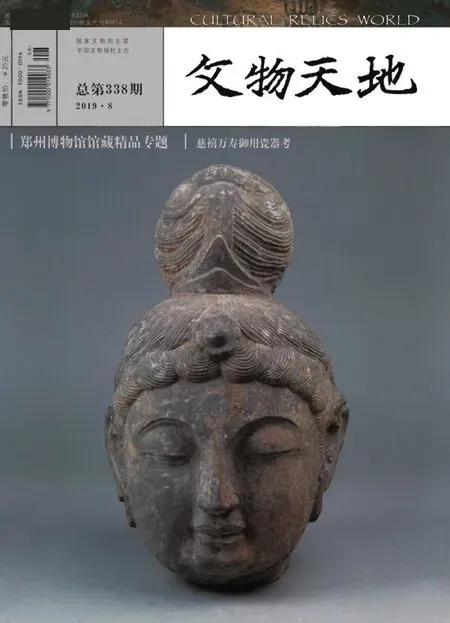辨?zhèn)未嬲鎴D通文史美術史論自立他山
——“鑒定與中國美術史研究”研討會綜述(下)
文/戴曉云
邵彥:近期所見書畫鑒定個案兩例
邵彥就個案中呈現(xiàn)在繪畫、書法中的風格進行研究,而后得出自己的結論。她對東京國立博物館舉辦的“顏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筆”、上海博物館舉辦的“丹青寶筏——董其昌書畫藝術”的展品做了兩個個案研究。
邵彥首先分析董其昌的《山居圖》(圖八),指出程嘉燧認為這是董其昌早年作品的觀點值得再思考。為了證明這個觀點,邵彥幾乎用了董其昌所有時段的作品,包括書法和繪畫。從《行書論書卷》《紀游圖冊》《燕吳八景圖冊》《煙江疊嶂圖卷》到《行書羅漢贊》,49歲的《羅漢贊》表明此時董其昌大字狂草成熟,對于從42歲的《燕吳八景圖·西山秋色》(圖九)到50歲的《煙江疊嶂圖》發(fā)展成熟的長線皴,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從狂草快速奔跑的中鋒線條,到山水畫舒緩的長線皴,難度降低。
邵彥認為,《山居圖》的時代應該重新歸屬,應為董其昌中期作品,不屬于早期。董其昌早期的兩件作品,一件是38歲作品、一件42歲作品,體現(xiàn)的主要不是遍學傳統(tǒng),而是從科舉書法脫化的過程。
董其昌個人風格的形成足跡,主要體現(xiàn)在《羅漢贊》的成熟草書面貌、《煙江疊嶂圖》的中鋒長皴線。《山居圖》皴法較《煙江》長皴線柔和,年代更晚些。
對于傳為李公麟的《五馬圖》(圖一〇),邵彥以《臨韋偃放牧圖》(圖一一)和《孝經圖》(圖一二)為李公麟作品的標準器,綜合黃庭堅的作品,對《五馬圖》進行了分析考證。
她認為《五馬圖》有明顯裁割痕跡,原來可能不止五馬。馬旁“黃書”系偽添,筆力纖弱似明中期以后人書,書寫位置古怪。后跋黃庭堅、曾紆書法皆真,黃庭堅書法為盛年佳作。黃庭堅跋紙張質地與本幅相同,但中間有裁割,年代相同,是否原配不得而知。人馬畫法精妙純熟,屬于畫史孤品,無法置入現(xiàn)有線索。這些與她認可的李公麟《臨韋偃牧放圖》和《孝經圖》畫法有明顯差異。
邵彥認為,《五馬圖》是北宋畫,后添黃庭堅題,后紙黃跋有可能是移配。無法證明本幅是李公麟畫,更傾向于是專業(yè)畫家作品。亦無法證明是皇家馬政檔案,疑為屏風小樣。
戴曉云:佛畫鑒定個案和中國美術史研究
近年來,佛教美術(宗教美術)成為研究熱點,由于這些文物的鑒定沒有納入傳統(tǒng)書畫鑒定的范圍,因此與傳統(tǒng)書畫鑒定相比,佛教(宗教)文物鑒定問題更顯重要。戴曉云圍繞宗教畫鑒定個案探討中國宗教繪畫的研究。首先以一幅明代嘉靖年間的道場畫(圖一三)展開,進而分析明代宗教繪畫的時代風格特點,地區(qū)風格特點,比較了水陸畫(傳統(tǒng))和民間宗教畫(民間道場畫)(新興)的區(qū)別。
雖然此畫的嘉靖年款畫面漫漶,但經過分析,不存在改年款的可能性。題記上有年號“嘉靖”(圖一四)。有些模糊不清,是不是后代的涂改和作偽呢?本幅是明代的還是清代的呢?這個問題可以從年號本身來考慮。“嘉”字上半部分的“吉”字沒有漫漶,因此嘉字沒有問題,清代有嘉字的年號就是“嘉慶”,而慶字的繁體是“慶”字,筆畫比較多,作偽者想要把“慶”字完全刮干凈也不太可能,因此嘉靖二字作偽的可能性不大。這幅畫應該就是明代嘉靖年間的繪畫。
戴曉云指出,明代的宗教繪畫(包括卷軸和壁畫)、金銅佛造像中人物的眉眼、造型、服飾和清代的相比,明代作品都相對生動,面色柔和,帶有笑容,有的造像或雍容華貴,或莊嚴肅穆,但均較為自然,不刻板。嘉靖款的道場畫人物自然生動,面帶笑容。
古浪博物館藏明代的水陸畫共有42軸,根據(jù)題記,這些圖是明代萬歷三十一年重修過,到清代雍正再重修。那么萬歷三十一年之前就繪制了。上述畫作是明代的作品,具有上述描繪的明代時代風格。例如韋陀像中韋陀菩薩面帶笑容(圖一五),臉型豐腴圓長,造像生動,神采飛揚。
青海西來寺藏水陸畫24軸,是明萬歷年間的畫作,畫風和人物造像也具有明代的時代風格(圖一六),首都博物館藏有萬歷年間慈圣皇太后造的水陸畫40余軸(圖一七),其繪制風格和青海西來寺的繪制風格完全一致。雖水陸畫存在粉本的問題,但時代風格無疑是兩館所藏畫風十分接近的根本原因,首都博物館藏水陸畫和青海西來寺水陸畫具有相同的時代風格:西來寺藏水陸畫的水陸緣起圖和古浪博物館藏的水陸畫的水陸緣起圖不僅人物繪制風格相似,而且人物形象也完全相同。

圖八明 萬歷董 其昌山 居圖上 海博物館藏

圖九董 其昌吳 燕八景圖冊之一 上海博物館藏
公主寺位于山西繁峙,大雄寶殿有一堂明弘治十六年的水陸畫(圖一八)。其風格和嘉靖款道場畫、古浪博物館藏水陸畫、青海西來寺所藏水陸畫和首都博物館所藏水陸畫完全相同。由于公主寺繪制年代較其他幾堂水陸畫早,因此畫藝更加精妙。
這些明代的水陸壁畫和卷軸畫,體現(xiàn)了明代的時代風格,畫風端莊典雅,神態(tài)生動。共同點為人物臉型圓長,較為豐腴,眉毛彎彎;部分女仙臉上有三白臉色;所有人物柔和帶笑,形象生動;均采取工筆重彩的畫法;繪畫形式類同,一般使用立軸的形式,神像旁有榜題,或還有功德主的姓名及所捐款項等具體內容。
但是,嘉靖款宗教畫和其他的明代水陸畫又有明顯不同:嘉靖款道場畫藝術性比同時期的水陸畫差,人物造型和線條不如同期的水陸畫,人物莊重典雅不足,同期水陸畫的設色、線條和人物造型遠勝于嘉靖款畫作。比如弘治十六年的壁畫采用了瀝粉貼金的做法,顯得富麗堂皇,色彩絢麗、古樸典雅。而嘉靖款畫作則隨意很多,甚至不講究構圖和對稱關系。但嘉靖款道場畫也有其優(yōu)點,那就雖不夠莊重典雅,但是比同期水陸畫畫得更野更活。
如上分析,這幅畫和同時代的明代人物畫有共同點,但又有明顯區(qū)別。藝術風格和同時代的中原地區(qū)、北京地區(qū)的繪畫藝術風格相差極遠,具有明顯的差異,那么為何和同時代的水陸畫差異這么大呢?
戴曉云指出這是兩種繪畫系統(tǒng),一種是水陸畫的繪畫系統(tǒng),稱之為傳統(tǒng)繪畫形式,承襲了傳統(tǒng)的道釋繪畫形式;一種是民間宗教儀式上使用的圖像系統(tǒng),是民間形成的一種新的繪畫,是配合民間宗教的一些儀式,在道場上使用的,其藝術具有民間性,不少具有年畫的特點。這些新興的繪畫雖然和水陸畫同時期,但藝術風格有差異,是由于宗教文化的形成和傳承、繪畫的傳承和創(chuàng)新、粉本和畫工不同。這些宗教畫,大多分布在南方地區(qū)、長江中下游地區(qū)。這些繪畫和一定的宗教文化和宗教儀式配合使用,是民間教派的有機組成部分之一,研究清楚這批宗教畫的性質和題材,對民間宗教畫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只有弄清這批宗教畫的性質,相關研究者使用圖像作材料時,才不會用錯。
道釋畫可以用藝術風格來判別,但鑒別有時候和藝術風格無關。戴曉云以《十王圖》為例說明,由于“十王”在中國喪葬文化中特殊的地位,《十王圖》的使用范圍相當廣泛。《十王圖》既可能是佛教水陸的“十王”,也可能是道教黃箓的“十王”,還可能是民間宗教度亡儀式上的“十王”,也可能人們?yōu)榱俗屚鋈税残纳下罚选笆酢睊煸谀怪校澜掏綉覓斓澜绦再|的“十王”,佛教徒懸掛佛教性質的“十王”。這些《十王圖》,可能出自一個粉本,但性質卻完全不同。這種情況,在很多道釋畫中都存在,這是研究時尤其需要注意的問題。
盡管傳統(tǒng)宗教繪畫和新興宗教有相似之處,同樣具有明代宗教畫的特點,繪畫形式類同,一般使用立軸的形式,神像旁有榜題,或還有功德主的姓名及所捐款項等具體內容。但如前所述,它們在藝術風格上有很大的差異。由于道場畫是配合一些宗教儀式用的,因此從繪畫風格的差異,可以窺探其背后代表的宗教文化。這是讀圖分析其藝術風格和來源,從而為探尋宗教文化的類型提供歷史證據(jù)的一個例子,也就是鑒定在佛教美術史研究上的作用。

圖一〇 李公麟(傳) 五馬圖 日本私人藏

圖一一 李公麟 臨韋偃牧放圖(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一二 李公麟 孝經圖(局部) 大都會博物館藏
朱萬章:宋畫鑒定的幾個誤區(qū)
朱萬章談了自己對宋畫研究的幾點心得。
首先,書畫鑒定的基本問題是斷代。一般說來,對于一幅古畫的鑒定,首先確定其時代氣息。畫面透露出的“氣韻”,是鑒定宋畫的先決條件。這種“氣韻”的獲得是建立在對存世宋畫的飽游飫看之上的。劉勰《文心雕龍》:“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運用到鑒定宋畫可以衍變?yōu)椤坝^千畫而后識氣”。宋畫有一種共同的時代氣息,即畫面透露出的“氣韻”,啟功將其稱之為“望氣”。這種時代氣息包括畫面本身所蘊含的新舊程度、包漿、筆法、墨韻、賦色、材質、傷況、裝裱等,甚至包括很多不可或很難言說的成分,因而在鑒定起來的時候,會出現(xiàn)一些不可確定性或模糊性,但只要對同時期的畫作的共通性有所認知,找到一些規(guī)律性的信息,就不會妨礙對畫作本身時代的判定。
雖然所謂的“氣韻”有一定的主觀性,甚至有很大空間的不可捉摸性,但由于這是建立在對同時期作品共性的認知上,因而對于傳統(tǒng)書畫鑒定來說,目前仍是顛撲不破的不二之選。現(xiàn)在的不少書畫鑒定實踐,缺少這個環(huán)節(jié)的認知和積淀,輕言真?zhèn)危髡f各理,因而有南轅北轍之虞。鑒定的關鍵一步最必須看原跡,任何精美的畫冊和高像素的電子圖版都無法替代對畫作本身的考察(圖一九、圖二〇)。
對于孤本作品的鑒定與比對,按照約定俗成的慣例,遇到沒有同一人的作品作為比較參照的孤本,如果到代,且又無法拿出鐵證證偽的前提下,一般便認定為真跡。輔助依據(jù)不可盡信。
畫作本身以外的信息,如收藏印鑒、題跋、文獻著錄、材料、裝裱及其他輔助依據(jù),只能增加作品的文化附加值,也可以作為書畫真?zhèn)蔚淖C據(jù)鏈之一,但不能作為判斷書畫真?zhèn)蔚闹苯右罁?jù)。科技鑒定只能證偽。預設結論的證據(jù)鏈不可信。
對前人鑒定結論提出質疑的精神固然可貴,但須建立在論據(jù)充分的前提下。預設結論的證據(jù)搜索與推論不能作為書畫真?zhèn)蔚囊罁?jù),所有可能性都不能成為“證真”和“辨?zhèn)巍钡淖C據(jù)。宋畫的鑒定存在作品優(yōu)劣與真?zhèn)螁栴}。一般情況下,一件有定論的宋畫真跡其藝術價值是高的。但有時候并不盡然,有部分作品雖然是真跡,但不乏懈筆。也有的作品雖然畫得很好,但卻不是畫家真跡。
朱萬章認為,鑒定的先決條件是回到作品本身,但現(xiàn)在很多書畫鑒定文章,并非建立在對作品原件的研究之上,而是抓住一點,加上各種推測,對已有明確鑒定結論的作品在沒有鐵證的前提下,輕易否定,對初入美術史研究之門的后學者造成困擾。朱萬章建議,對待美術史上的名作,如果該作品前人已有結論,且這種結論已經被學界所廣泛采納,在確實拿不出令人信服的鐵證證偽的前提下,理論上仍然遵循約定俗成的原則。

圖一〇 李公麟(傳) 五馬圖(局部) 日本私人藏

圖一三 明嘉靖款 民間宗教道場畫 私人藏
赫俊紅:歷史文獻中的書畫鑒定
歷史文獻可作為書畫鑒定的輔助佐證。歷史文獻中有關書畫家及書畫作品的記載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純文字的,如以集中記人為主的畫史類著作,以及散見于筆記、雜記、詩文集和地方志等的有關記述;以記載作品的為主的書畫著錄書,如記錄宮廷藏品的宋代《宣和書譜》《宣和畫譜》,清代《石渠寶笈 秘殿珠林》初、續(xù)、三編,記錄私家藏品的明清著錄書約有六七十種。
另一種是圖像的,以照相和珂羅版印制等技術,影印成書畫作品的單幅或集冊。這種圖像記載方式出現(xiàn)在清末,民國時被集中在上海、北京的各大出版機構廣泛采用。如上海神州國光社由鄧實和黃賓虹主編的《神州國光集》21集、續(xù)集20集,文明書局刊印廉泉(小萬柳居士)收藏而成的《名人書畫扇集》60集,商務印書館的《名人書畫集》30集;而北京延光室、北平古物陳列所、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則依托清宮舊藏來影印,如《故宮書畫集》47期、《故宮》44期。20世紀40年代末鄭振鐸編刊的《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8集。
面對如此龐雜的書畫文獻資料,首先要有辨析和質疑的鑒定意識。具體到某一書畫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在梳理文獻記載時,要注意兩點:文獻譜系查檢,判斷記述文獻的承襲與變異;文獻原真性,對最本源記述的追溯與采信。從此角度重新審視舊藏著錄書畫或現(xiàn)存書畫作品,會發(fā)現(xiàn)諸多以往被忽視的問題,從而去偽存真,以正視聽。

圖一四 明嘉靖款民間宗教道場畫(局部) 私人藏

圖一五 明萬歷 韋陀像 古浪博物館藏
以晚明畫家馬守真為例。1981年版《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俞劍華編,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第767頁)記其小傳曰:“馬守真(1548-1604),(明)女。一作守貞,小字玄兒,又號月嬌,一署馬湘,有小印曰獻庭;善畫蘭,故湘蘭之名獨著。金陵(今南京)妓,居秦淮勝處。輕才任俠,與王穉登友善。以詩、畫擅名一時。……”詞條所附參引書目有《明畫錄》《無聲詩史》《圖繪寶鑒續(xù)纂》《列朝詩集小傳》《書林紀事》。

圖一六 明萬歷 水陸緣起圖 西來寺博物館藏

圖一七 明萬歷 水陸緣起圖 首都博物館藏

圖一八 明弘治十六年 觀音和大勢至菩薩圖 山西繁峙公主寺壁畫
詞條編者參閱的上述5種書,前4種均成書于清初,后1種晚至1935年,寫作者皆非傳主馬守真的當時代人,因此,這些記載又源自何人何處?與馬守真相友善的吳門才子王穉登是否有過對馬氏的記述?與馬氏同時代的、后世的記載有哪些?歷史文獻中著錄的馬氏畫作有哪些?對這些問題的追蹤查檢,便形成了關于馬氏其人和其作品的兩個文獻查檢表,即《晚明清初各種文本對馬守真的記載》《明清鑒藏家對馬守真畫作的著錄統(tǒng)計表》[1]。前者從王穉登于1577年的記述到卞永譽清初的記載共34項,后者從明末汪珂玉《珊瑚網畫錄》到民國關冕鈞《三秋閣書畫錄》共著錄作品26幅。
對上述文獻的辨析對勘可知,王穉登寫于1605年、馬氏去世不久的《馬姬傳》,是對馬守真其人其事的最早且可靠的記載,王穉登是以第一人稱“余”來記述馬氏身世才情及兩人間的交往,此傳1612年被潘之恒輯錄于《亙史》卷十八“外紀?艷部”,明天啟間刻本。
傳中確切地記載了馬氏的姓名字號:“馬氏同母姊妹四人,姬齒居四,故呼四娘,小字玄兒,列行曰守真,又字月嬌,以善畫蘭,號湘蘭子。”傳中還記載了馬氏的年齡,即甲辰(1604)秋日馬氏買樓船載嬋娟從南京到吳門王氏客飛絮園,為王氏祝70壽時,馬姬57歲,歸未幾便病故。如果按公元紀年,馬守真的生卒年是1548-1604年。也就是說,王穉登《馬姬傳》中對馬氏生卒、姓名字號等傳略的記載,在歷史文獻譜系中是最早的、最可靠的、原真性記述,是應予以采信的。

圖一九 宋 范寬 溪山行旅圖 絹本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〇 宋 王希孟 千里江山圖(局部) 絹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以此對勘上述《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中的馬守真詞條,顯然“一作守貞”“又號月嬌”有訛誤。晚明清初其他人對馬氏的片段記述基本源于王氏寫作。而縱觀馬氏其人和其作品的兩個歷史文獻查檢表,分析發(fā)現(xiàn)類似“守貞”的訛誤多出現(xiàn)在清乾隆及以后時期的馬守真畫作著錄的題名或印章中。
歸而言之,基于對馬守真其人其作品的歷史文獻譜系的查檢對勘,通過對其人生平傳略記述(如生卒年、“守真”非“守貞”)的原真性追溯和采信,再從真?zhèn)舞b定的角度來重新審視這些被舊藏家視為馬守真的畫作,便會發(fā)現(xiàn)其中存在著不少的偽作。1.通過馬守真的生卒年(1548-1604)便可判為偽作的作品,包括金瑗記錄的《女史馬湘蘭竹石積賞》《馬守真蘭竹》,張大鏞記載的《馬湘蘭蘭竹》。2.偽款印“馬守貞”在清乾隆時及以后藏品上的使用,其中有《石渠寶笈》記載的《明馬守貞畫蘭一卷》,陸時化記載的《明妓馬守貞白描大士軸》《明馬守貞水墨梅蘭冊》,葛嗣浵記載的《明馬守貞飛白竹軸》,杜瑞聯(lián)記載的《馬湘蘭白描蘭花卷》(圖二一)。
同樣,類似的偽作也存在于現(xiàn)存作品中,如故宮博物院藏《蘭竹圖軸》,題款:“甲寅七月既望寫于桃葉渡舟中 湘蘭馬守真”,甲寅當為1554年,馬氏7歲,顯然是偽作。再如故宮藏《馬守貞竹石扇面》,題款:“天啟癸亥夏五月……湘蘭馬守貞”;遼寧省博物館藏《花卉圖冊》(圖二二),其中一頁的款識為“天啟甲子秋日 湘蘭女史馬守真”。我們知道,天啟癸亥是1623年,天啟甲子是1624年,此時馬氏已去世20年,故系偽作。

圖二一 馬守真 畫蘭卷(偽)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二 馬守真 花卉圖冊(偽) 遼寧省博物館藏

美術史研究應回歸到本體研究
書法和繪畫是古代人們經常使用和創(chuàng)作的,留存量非常大,書畫鑒定是鑒定中最常見的鑒定類別。書畫鑒定的研究開展較早,體系較為成熟,其經驗是其他鑒定門類可資借鑒的。此次研討會以書畫鑒定為中心議題,旨在借鑒書畫鑒定成熟的理論和方法,為課題的順利開展打下堅實的基礎。宗教畫的鑒定屬于書畫鑒定的范圍,傳世書畫的鑒定理論和方法完全適用于此。
另外,我們必須明確,書畫史和宗教美術史是中國古代美術史的有機組成部分,近年來其他學科對圖像研究的關注,大多數(shù)集中在對宗教畫、石窟造像和壁畫、寺觀造像和壁畫等宗教美術作品上。這些研究美術史的理論和方法,應該和書畫史一樣。無論是傳世書畫還是宗教美術史(宗教圖像)的研究,同樣有本末問題,有基礎研究和本體研究,本次會議的目的就是讓學界的目光集中在宗教美術研究的本體研究上。目前,許多研究舍本追末,在尚未清楚神祇定名、題材的性質、壁畫本身和臨摹復制品的區(qū)別,就把這些圖像當作史料用于研究中,去證明自己的結論,這樣會犯使用材料的錯誤。有的學者使用錯誤的學術史,對錯誤的學術史不加辨別,發(fā)表自己的議論,把研究建立在錯誤的學術上,最后得出錯誤的結論;有的在基礎研究尚未完成的情況下,借鑒西方的研究方法,從社會學、民俗學、人類學或物質文化和視覺文化等角度去看問題。雖然使用西方的理論和方法無可責備,但在基礎研究尚未完成的情況下,就使用西方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屬于舍本逐末,美術史研究中過度闡釋的問題也會凸顯。薛永年先生在《美術史的自立與他山》一文中指出,“我不贊成用中西文化二元對立的思維看待當下的美術史論研究中的問題。藝術史論研究,既有跨文化的一面,又有民族價值觀和民族特色的一面。不過,需要明確的是,他者眼光,雖對我們有啟發(fā),但不能代替我們以自己的眼睛看世界,被動效仿搬來的鞋子,未必適合自己的腳。”“對此,我們更應該加強文化交流中的文化自覺,并且以卓然自立的精神在美術理論的建設中發(fā)揮他山之石的積極作用而避免外國專家也不欣賞的盲目追隨。”[2]這是我們在中國美術史研究中應該持有的態(tài)度,也是宗教美術史研究中特別需要引起注意的問題。
美術研究應立足于傳統(tǒng)理論和方法,如果把立足于本土傳統(tǒng)的研究理論和方法稱為本,那么西方理論和方法則可稱為末,研究中不可本末倒置。中國美術史研究的現(xiàn)狀告訴我們,目前美術史研究更多應該在于自立,而不是他山之石。如果美術史研究的本體研究已經完成,那么借鑒他人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則不失為一種好的方法。他山之石只有建立在扎實的基礎研究上,才會結出碩果。
[1]赫俊紅:《丹青奇葩——晚明清初的女性繪畫》,第118、130頁,2008年。
[2]薛永年:《自立和他山——美術史論的交流和借鑒》,《美術觀察》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