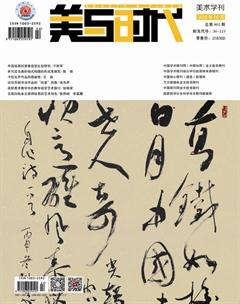略談主流文化對美術創作的影響
李立婷
摘 要:美術作為整體文化中一部分,直接承載著國家利益。在由國家直接發起的系列宣傳活動中,美術被視為主要載體,這些美術創作不僅是藝術家陶冶情操、傳達本身思想的有效方式,也可以成為執政者宣傳自己、達到本身執政意圖和理念的有效工具。這些美術創作由于受到執政者的干預,成為了最能體現當時社會走向的主流文化。
關鍵詞:主流文化;美術創作;戰爭題材;油畫創作;“英雄塑造”
一、主流文化
文化是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的。19世紀的人類學家泰勒對于文化作出了如下定義:文化是一個“復雜的整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作為一個社會成員的人所獲得的任何其他能力或習慣”。① 這一定義意在說明文化在社會生活中的滲透性,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主流文化則是由執政者領導的、在總文化中占統治地位、能代表時代思想并決定文化走向的一種主要文化。其特征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由執政者主導,并以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為核心;第二,是總文化中絕對重要的部分,直接承載國家利益,與國家利益一脈相承;第三,以是否符合社會進步和歷史發展來判斷正確與否。文化涉及社會的各個方面,美術作便是文化的一種典型的代表。
美術作為整體文化中一部分,承載著國家利益。在由國家直接發起的系列宣傳活動中,美術被視為主要載體,這些美術創作不僅是藝術家陶冶情操、傳達本身思想的有效方式,也可以成為執政者宣傳自己、達到本身執政意圖和理念的有效工具。由于執政者對美術領域的干預,美術成為了最能代表當時社會走向的“主流文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成立時期起著鞏固政權作用,發揮著政治功效。
二、蘇聯美術的影響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正處于內憂外患的窘迫境地:一方面在國際中處境尷尬,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企圖通過國際力量來扼殺剛剛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另一方面國內的國民黨反動派殘余勢力尚未完全肅清,尤其美國對朝鮮悍然發動的侵略戰爭,迫使剛剛結束了解放戰爭的中國人民陷入了長達三年的抗美援朝戰爭中,剛剛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危機四伏。迫于解決國際、國內種種威脅的中國人民政府,實行了“一邊倒”政策,多領域學習蘇聯。作為鞏固國家政權、鼓舞廣大人民群眾建設新社會的主流文化,美術創作領域的戰爭題材油畫也不例外。
這一方面,蘇聯時期的俄羅斯美術主流的本質是現實主義,充滿生氣和現實理想,與中國政府期待通過“再現歷史、歌頌英雄”的美術創作來鞏固政權的要求相吻合;另一方面,為了美術事業自身的發展,中國政府實行了“走出去,請進來”的方針政策,在派遣了大量優秀畫家往蘇聯學習繪畫技藝的同時,也引進蘇聯優秀的繪畫專家來華授課并開辦了以蘇聯為代表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美術展覽。蘇聯戰爭題材油畫創作中的愛國主義思想、勇敢犧牲精神、宏大敘事的構圖、英勇陽剛的英雄塑造美學原則,對中國美術的戰爭題材油畫創作具有極大的借鑒意義,促使后者塑造出了戰爭中無數經典的“英雄”形象。
曾在蘇聯在華舉辦的馬克西莫夫油畫班訓練過的中國油畫家馮法祀于1957年完成的作品《劉胡蘭就義》就是借鑒了蘇聯畫家庫克雷尼克塞的戰爭題材油畫作品《丹娘》。《丹娘》是庫克雷尼克塞歷經五年創作完成,于1954年北京舉辦的蘇聯經濟及文化建設成就展覽會的展覽作品之一,畫面上精心布置了兩個敵對的陣營:一邊是滿膛憤懣、仇視敵人的蘇維埃村民,另一邊是惡貫滿盈、滅絕人性的希特勒匪軍,人物的外形和表情的刻畫形成了鮮明對比。而馮法祀的《劉胡蘭就義》無論在場面安排、取景設置還是人物刻畫方面,都借鑒了庫克雷尼克塞的《丹娘》,兩幅作品都以正反兩派人物的對比來塑造就義前不怕犧牲、英勇無畏的女英雄形象。
三、“紀念碑”式的崇高形象
(一)革命的理想人格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大部分的美術工作者被國家有計劃地組織起來,按照國家分派下來的任務進行“統一”創作。國家博物館先后組織了幾次征收戰爭題材油畫創作的美術展覽,“展覽”的形式也是由國家組織并統一進行。這些由國家政府直接發起的系列美術創作活動,其作品被用來宣揚共產黨功績、鞏固政權、鼓勵人民建設祖國。戰爭中壯烈犧牲的英雄更是被創造成一種“紀念碑”式的崇高形象。這些“紀念碑”式的崇高形象的英雄塑造,主要有兩個功用:一是用以昭彰我黨在戰爭中的歷史功績,著重展示革命的理想人格;二是用以鞏固新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設,為廣大人民群眾提供道德樣式的榜樣,提供“見賢思齊”的標準。由此兩點作為主流美術中戰爭題材油畫創作的出發點,借助繪畫語言來表現我黨及人民群眾在戰爭中保家衛國、英勇無畏的民族精神,以此鼓舞和激勵廣大人民群眾建設國家的熱情。“為了在統治時帶有一定程度的贊同基礎,一個憲政國家的政府必須在被統治者的心目中建立它的合法性。文化在保證統治的合法性上面是一個關鍵因素。”②由此,這個時期主流文化之一的主流美術中的戰爭題材油畫作品不僅彰顯了共產黨卓越的功績,樹立起作為執政黨的共產黨在人民群眾心中的威望,還鼓舞和激勵了廣大人民群眾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的熱情。
1957年董希文所作《百萬雄師下江南》(圖1)的大型戰爭題材油畫,就是為了歌頌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在戰爭中立下的豐功偉績。畫家在創作過程中與不少親身參加過此次戰役的同志們做了詳細研究,采用宏大的敘事構圖,將我軍不畏犧牲、英勇作戰的英雄形象描繪得極為生動,主要是用以歌頌我黨帶領百萬雄師過長江解放全中國的偉大勝利。胡一川的《開鐐》主要描繪最初的共產黨被國民黨關押、被釘鐐四十天的真實歷史。畫面人物造型樸實概括而鮮明,特別是畫面上對光的處理,使主要人物十分鮮明、突出。畫面上巨大的鐵鐐代表著殘酷的反動勢力,預示著我黨在獄中所受到的磨難,使觀者油然而生一種沉重、肅然起敬的感覺。這無疑使得廣大人民群眾產生對作為執政黨的共產黨的無限崇敬之情、仰望之心,樹立起我黨在人們心中佇立不倒“紀念碑”般的崇高英雄形象。李宗津的《強奪瀘定橋》、任夢璋和楊為銘的《平型關大捷》、趙以雄的《長征路上的宣傳員》、吳作人的《過雪山》、任夢璋的《攻克錦州》、張漾兮的《巧渡金沙江》、董希文的《紅軍不怕遠征難》、鮑加和張法根的《淮海大捷》等諸多戰爭題材油畫作品都使得我黨在廣大人民群眾心中樹起立起佇立不倒的“紀念碑”式崇高英雄形象。
(二)道德的規范形象
1959年詹建俊所作的戰爭題材油畫作品《狼牙山五壯士》(圖2)采用“紀念碑”式構圖,描繪我軍戰士將日本侵略者引入狼牙山,最后跳崖也決不投降的英雄事跡,表現了戰士們寧死不屈、不畏犧牲的英雄氣概,這無疑給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中的中國人民群眾帶來了巨大的精神鼓舞與不竭動力。羅工柳的《地道戰》、聞立鵬的《國際歌》、全山石的《英勇不屈》、王德威的《英雄小姐妹》等都是以人民在戰爭中保家衛國、英勇無畏的民族精神來鼓舞和激勵廣大人民群眾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熱情的戰爭題材油畫作品。1957年馮法祀創作的《劉胡蘭就義》,雖以精湛的表現技巧受到美術界的一致認可,但由于當時正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時期,畫面上寥寥幾個敵人就可以使大片群眾“妥協”,被認為“暗含著人民群眾的懦弱、愚昧,打擊人民群眾建國熱情”,在當時受到美術批評家的批判。可見這些作為主流文化的美術作品在承載國家利益的同時,不但要表達藝術家本身的思想,更要體現國家政治所要求的發展走向,不能脫離、違背國家的意愿。
四、結語
作為被國家直接控制的主流文化對美術創作領域的影響,可以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戰爭題材油畫作品中的英雄形象塑造體現出來。其英雄形象作為新中國為鞏固政權、歌頌英雄為不朽“紀念碑”的政治工具,是國家主流文化對美術創作的影響的有力證明。由于主流文化由執政者主導,主流文化必定與國家利益緊密關聯。與此同時,在文化中存在的領導權不會隨著歷史的改變而消失,而是會伴隨著人類的整個發展歷程。
注釋:
①②陶東風.文化研究導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6,228.
參考文獻:
[1]陶東風.文化研究導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趙箋.主流文化與美術創作的思考[J].南京藝術學院學報,2011(2).
作者單位:
山東師范大學(美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