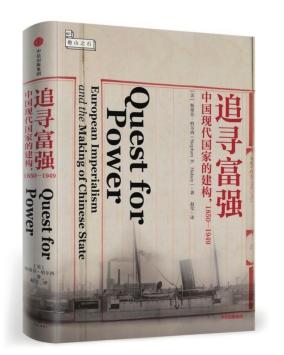理解中國的“國家獨特性”
雷墨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理解當下中國必須重回歷史。無論從文明傳承還是民族復興的視角,都能從紛繁復雜的歷史影像中看出中國的“國家獨特性”。
為何在西方殖民主義浪潮沖擊下,中國能作為一個政治實體屹立不倒?因為與同時代很多有類似歷史遭遇的國家不同,無論是晚清、民國還是新中國,都在致力于現代國家的構建,而且取得了相當的成功。
這是中國“國家獨特性”最為顯性的特征,也是理解當下中國、思考未來中國的邏輯基點。
獨特的背景
“到1914年為止,歐洲國家的殖民地范圍已占全世界陸地面積的84.4%以上,但直到近代,中國都一直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這個國家的發展軌跡為何與歐洲掌控的全球格局大相徑庭?”美國學者斯蒂芬·哈爾西在其《追尋富強:中國現代國家的建構》的開篇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忽略它就無法理解當下的中國,也難以理解中國與世界的互動。某種程度上說,這個問題是中國“獨特”之源。哈爾西通過分析第一次鴉片戰爭直到新中國成立前的歷史,把中國的現代國家建構放在世界歷史語境下,解釋中國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為何能屹立不倒,并走上了一條獨特的道路。
但在探討中國如何較為成功地構建現代國家前,有必要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在被動地卷入西方殖民主義浪潮前,中國處于一種什么樣的狀態?與后來有類似歷史遭遇的國家相比有何獨特之處?
我們不妨從最直觀的歷史事實入手,即從清朝到民國再到新中國,中國的疆域大體保持完整,中央政權從未完全失去對疆域的控制。相比來說,在領土和人口上曾一度與清朝中國接近的奧斯曼帝國,最終“萎縮”到安納托利亞半島(土耳其),而莫臥兒王朝的印度則徹底淪為了西方的殖民地。
“大一統”思維在中國歷史進程中的作用無需贅言,但在清朝可以說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體現在清朝政府對包括西藏、新疆、蒙古在內的邊疆的實際控制力,但更為關鍵的是,就治理手段來說清朝政府已經帶有某些“現代”特征。
相比于明朝,清朝對邊疆的控制,帶有更明顯的事實管轄特征。比如,清朝在擊敗準噶爾勢力后即在拉薩駐有常備軍,并設立噶倫與西藏地方精英共同處理地方政務,后來又設立了常駐拉薩的駐藏大臣。
從當時的歷史情況來說,清朝政府對邊疆的軍事控制,主要考慮是為了穩定作為統治核心的內地。也就是說,把穩定邊疆作為統治內地的外圍屏障。但以現在的標準來看,“軍事存在”至今仍是一國中央政府彰顯事實管轄的重要手段。清朝政府在邊疆的軍事存在,與舊式、傳統的帝國以及歐洲殖民列強有著本質的不同,在政治意義上已帶有現代特征。
美國學者簡·伯班克和弗雷德里克·庫珀,在《世界帝國史:權力與差異政治》一書中,以羅馬帝國、蒙古帝國、奧斯曼帝國等舊式帝國為例,詳述了對外擴張與帝國存在之間的密切聯系。簡單地說,這些帝國的擴張與財富掠奪直接相關,一旦停止擴張,帝國存續危機就接踵而至。而清朝則完全不一樣,它對邊疆的控制與財富沒有任何直接關系,與帶有現代性的主權管轄更為接近。
中國歷史上在官僚體制的“非人格化”,以及權力運作的世俗化方面,遠比歷史上那些歐亞帝國要成功和有效。
另一個差異是治理手段。無論是羅馬帝國還是奧斯曼帝國,其對外擴張都帶有強烈的宗教動機。清朝政府重視宗教在穩定西藏、蒙古、新疆中的作用,但它也一直在政策上防止宗教權力化,底線是不能使宗教影響轉化為與朝廷分庭抗禮的力量。
清朝乾隆年間在平定新疆大小和卓叛亂后,對“伯克”(地方首領)制度進行改革,廢除其世襲制,并禁止阿訇介入行政性事務管理。在官僚體制上,這種做法已經在向更具現代特征的“非人格化”靠攏。
政治原則上實行政教分離,權力運作上推行世俗化,這都與羅馬帝國、奧斯曼帝國不一樣,更帶有現代民族國家政治的特征。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書中也指出了這個不同點:中國歷史上在官僚體制的“非人格化”,以及權力運作的世俗化方面,遠比歷史上那些歐亞帝國要成功和有效。
當然,清朝統治者不可能具備主動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的意識,形成這種局面主要是“無意識”的。但在當時清朝中國獨特的內外環境因素作用下,客觀上促成了其不同于舊式帝國的特征。
18世紀中期,中國的人口總量已突破2億。這樣的超大型人口規模,在當時的世界上絕無僅有。這意味著,即便清政府維持極低的稅率,也能產生龐大的、足以確保國家正常運轉的財政收入。
漢族人口占絕大多數比例的現實,事實上形成了人口高度同質化的局面。這一方面為內部分歧、矛盾乃至動蕩的低頻率提供了可能,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延續、塑造身份“認同”。
秦漢以來形成的以中原為腹地的文明核心地帶,對中國歷史進程所產生的向心力已反復被證明,這種影響在清朝達到了新的高度。比如,即便在與沙俄和清朝都對峙、戰爭時,準噶爾依然能清晰地將兩者區別開來。他曾致信康熙,“中華與我一道同軌”,“我并無自外于中華皇帝、達賴喇嘛禮法之意”。
但在奧斯曼帝國和莫臥兒王朝的印度歷史中,國家“認同”可以說從未真正產生過。無論是統治階層還是地方精英,他們對“認同”的感知,從未超越過對利益的盤算。
如果把19世紀中期視為中國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的起點,那么在這個轉型開啟之前,清朝中國已帶有較為明顯的“二元”特征。一方面,中國的經濟結構、經濟運作方式以及皇權統治,依然是傳統、舊式的。但另一方面,清朝中國的治理手段和國家形態,已經具備了某些現代特征。
獨特的路徑
與廣大非西方國家一樣,中國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也是被動的。但中國最大的不同,就是沒有一味地陷入被動,而是在諸多不利條件下尋找主動。
在民族國家轉型方面,學術界較為主流的概念是“財政-軍事國家”。其基本邏輯是,軍事開支的攀升給國家財政造成壓力,從而倒逼財政體系的改革,進而引發整個行政體系乃至權力結構的變化,最終導向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
這個邏輯對歐洲民族國家的形成很有解釋力。1490年歐洲獨立的政治實體數量約為200個,但到1890年降為30個。這段歷史正值歐洲戰亂頻仍時期,也與歐洲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基本吻合。
有屹立不倒,也有轟然倒塌。非西方世界亦然,只不過更多地是以被殖民化的形式表現出來。客觀地說,在西方殖民主義浪潮的沖擊下,某些非西方的國家尤其是大國,不是沒有進行過抗爭或救亡圖存式改革,有些也嘗試過打造“財政-軍事國家”,但它們的共同點是都失敗了。
而且,失敗的原因都存在某些相似性。用哈爾西的話說,那就是“軟弱無力的中央政府(國家)與千瘡百孔的經濟”。他在講述奧斯曼帝國和莫臥兒王朝的印度時寫道,“歐洲人遇到的不是強盛的中央集權的帝國,而是繼這些帝國后出現的一系列地方性國家。”
同樣是遭遇外部沖擊,中國歷史的演進路徑完全不一樣。在某些學者看來,中國邁入現代國家門檻遵循的依然是“財政-軍事國家”邏輯。經濟上的土崩瓦解與政治上的分崩離析,是奧斯曼帝國和莫臥兒王朝晚期的共同特征。這兩個特征,在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11年清朝滅亡的中國歷史中并不明顯。
內憂外患造成的政治危機,很大程度上源于國家經濟實力以及政府對經濟的抽取能力,不足以轉化為應對安全威脅的能力。在這一點上,晚清的中國在應對方式和成效上與上述非西方國家存在明顯不同。
歐洲殖民帝國在印度建一個工廠,就能輕易地將其政治經濟模式復制一次。但這種情況在晚清的中國從未發生過。
根據斯蒂芬·哈爾西的研究,去除通脹因素,清朝政府的稅收收入,從1842年的白銀4200萬兩,增加到1911年的1.2億兩,總共翻了3倍。雖然清廷在趨勢上行將就木,但從國家轉型的角度看,危機下中國的國家建構卻表現出極強的韌性。
在應對內外危機的過程中,清朝政府不是在正常的國家權力體系之外“疊加”一個包稅人制度(莫臥兒王朝印度的做法),而是依托已有的官僚體系實施財政體制改革(比如推行帶有地方稅特征的厘金制度),從而“內生”出新的國家制度。
19世紀50年代前,田賦在清政府財政收入中的比例一直占七成以上,但到19世紀末這個比例已經下降到30%以下,新興工業、國內商業、對外貿易等稅收比例大幅上升到60%以上。這樣的財政收入結構,已經接近19世紀初的英國。
財政收入結構的變化,反映的是經濟結構的變化。變化的主要動力來自19世紀60年代開始的洋務運動。洋務運動的初衷是強軍,后來延伸到近代工業、教育乃至治理體系(比如建立警察制度)。這種政府層面的現代國家建構的成功,離不開當時中國經濟和社會的“韌性”,即強大的對抗外部壓力的能力。
哈爾西寫道,“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在加爾各答建立了一個工廠,到18世紀中期,它的貿易已經開始改變孟加拉已有的政治經濟模式。”也就是說,歐洲殖民帝國在印度建一個工廠,就能輕易地將其政治經濟模式復制一次。但這種情況在晚清的中國從未發生過。
經濟上的韌性與政治上的韌性相輔相成。政治上的韌性,得益于清朝政府在權力的集中與下放問題上的務實(或者說被迫)調整。清朝早期的權臣是多爾袞、鰲拜、索爾圖、索尼等,但晚清活躍在權力場的卻是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等漢官。
從滿族統治精英的角度看,這是與漢人“分權”的問題。但從現代國家建構的角度看,這是一個權力體系“開放”的問題。也就是說,出于應對王朝危機的需要,晚清政府的分權客觀上導致了權力體系的開放。而權力體系的開放性,是衡量現代國家建構的指標之一。
更為關鍵的是,這種權力結構的變化并未導致中國政治上解體。晚清漢族權臣,尤其是曾國藩和李鴻章,沒有取清廷而代之,不能不說是一種“愚忠”。但也應該看到他們“國家意識”的一面。
在某些學者看來,國家意識的萌發和提升,是中國向現代國家轉型過程中,得以維持政治上大一統和疆域上大體完整的重要原因。清帝退位后,中國陷入軍閥混戰的黑暗時期,各路軍閥完全掌握地方的財政、行政和軍事大權,但中國并沒有分裂為多個獨立國家。
獨特的國家
清朝轟然倒塌時,帶有現代國家特征的中國已經形成,雖然孱弱但極具韌性。這種特征是當時其他非西方大國所不具備的。《清帝遜位詔書》宣稱總期“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有學者認為,這份詔書很大程度上賦予了“大一統中國”理念的政治合法性。
如果說源于《清帝遜位詔書》的政治合法性只是“表”,那么當時中國政治精英和實權人物的“國家意識”可謂“里”。“表里合一”共同構成了中國作為政治實體的韌性。比如,掌握新疆軍政大權近20年的漢官楊增新,把新疆經營成了儼然獨立于中央政府的政治實體,但同時他也一直捍衛中國對新疆的主權,從未有過脫離中央政府宣布獨立的打算。
事實上,在軍閥割據混戰的高潮期,“獨立建國”不僅不是選項,而且是政治禁忌。雖然各路軍閥的權力來源于槍桿子,但他們權力的合法性卻依賴于“國家統一”。這就造成了一種奇特現象:一方面中國在政治上處于分裂狀態,但現代國家建構的進程卻還在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