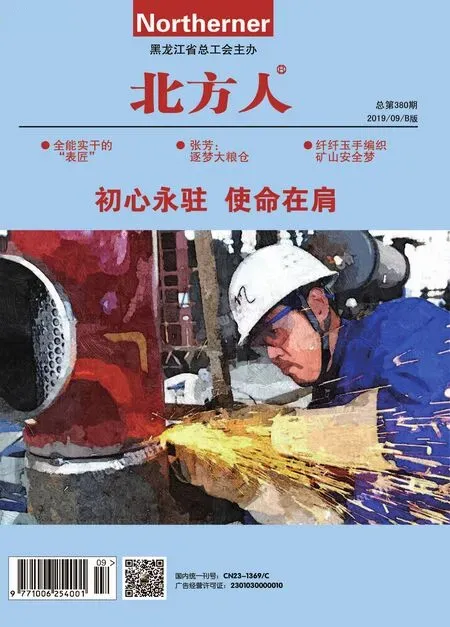偏見無處不在
文/八九不過百

黑或者白,每個人都有對顏色的偏好;社會是一個大的人,也有對顏色的偏好,但顏色本身并沒有對錯之分。無論是代表還是象征,人賦予其含義,令其有了不同。烏云和下雨,白云和晴天,綠色和植物,藍色和海洋,紅色和暴力,眼睛看到的,耳朵聽到的通過大腦聯系在一起。
《渺小的偉大》通過不同的視角展開這場由于新生兒意外死亡引發的案件敘述。魯斯代表有色人種,特克代表白人,而律師肯尼迪則是以第三者的角度來旁觀和反思,而心聲與話語權卻總是相悖。
故事中有一個小細節設置地很巧妙,洛雷法官在最后判決中根本沒有宣布無效審判,而是授予了“真實無罪釋放”,這與肯尼迪一開始對洛雷法官的刻板看法是截然相反的,這種對法官行為的錯誤判斷正是源于已有觀念形成的偏見。偏見是會放大的。當某個人的一個行為觸犯了禁地,我們就會將她列入正常接觸距離之外重新來審視她,她其余的行為便開始放大,進而懷疑她、討厭她,為她的行為找標簽。
每個人心里都有一桿秤,A或是B,但人并沒有高下之分。
我們總是在不知覺當中忽略很多東西,忘記了對方也是存活的個體,忘記對方也是某方面的受害者,忘記世界的一體從來不浮在表面。
我們,同而為人。
一開始看這本書是有些困難的,因為沉重,因為害怕面對,我將自己鎖在中國的一隅之地,以為躲著就能不去面對這些偏見。其實不然,沒有人是一座孤島,偏見無處不在。傳播學領域有一個概念叫作“沉默的螺旋”,當人們在表達自己想法和觀點的時候,如果看到自己贊同的觀點受到廣泛歡迎,就會積極參與進來,這類觀點就會越發大膽地發表和擴散;而發覺某一觀點無人或很少有人理會(有時會有群起而攻之的遭遇),即使自己贊同它,也會保持沉默。
書中以特克放下激進的偏見為結尾,是一種溫暖,更是一種對未來的期待。沉默與逃避是懦弱的表現,我們應該為自己的同胞發聲,應該為自己發聲。打破種族歧視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很多時候我們甚至沒有意識到那就是種族歧視。與之相對的是中國的“崇洋媚外”。來者為客的熱情本性、受慣打壓的奴性心理、強烈的民族不自信都讓我們在走出國門時更弱了一些。腰板硬才有話語權,唯唯諾諾只會讓別人看不起,被指著脊梁骨說不是。唯有更強,才能不受欺負,這一切,我們仍要負重前行。